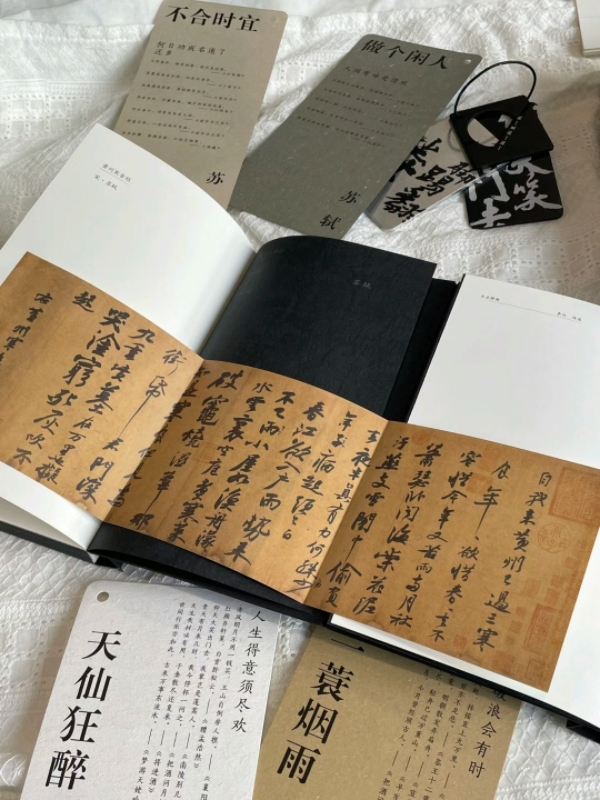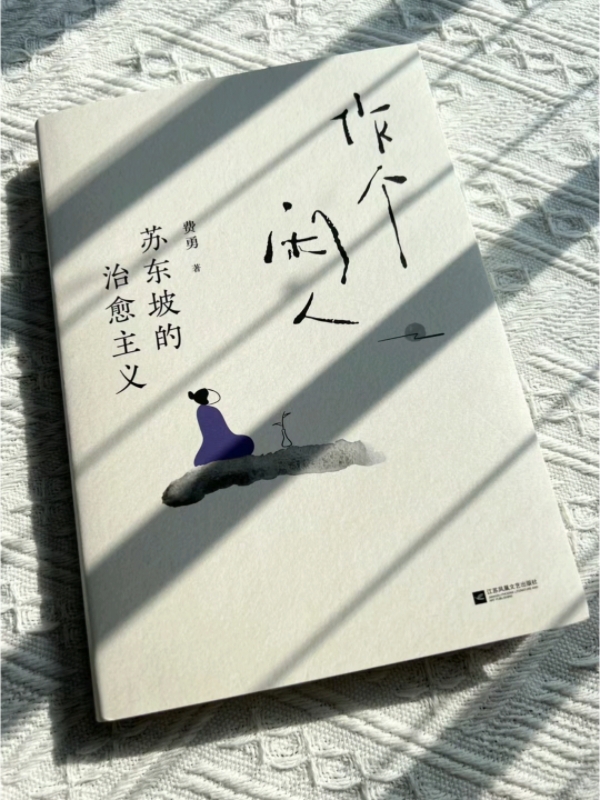
18
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
1.
1085年和1086年是苏东坡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1085年5月,他被任命为登州知州,上任五天,就有新的任命,回到朝廷担任礼部郎中,半个月后,又被提拔为起居舍人。1086年3月,又被提拔为中书舍人,9月又高升为翰林学士,负责皇帝的文书工作。一年多的时间,苏东坡的政治地位直线上升,很快从一个沦落在黄州的戴罪之人,成为权力中心的核心人物。就在这个高光时刻,苏东坡听说杨君素要去担任黄州太守,就写了《如梦令》二首送给他:如梦令·寄黄州杨使君二首
其一
为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
其二
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帘外百舌儿,惊起五更春睡。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
2.
春风得意的时候,苏东坡却怀念起黄州的日子。玉堂,指的是翰林院。翰林院这个机构,是从唐代开始出现的,最初是用来安置各类特别的行当,比如文学艺术、医学工艺、宗教方术、棋琴书画等方面的人才,并不是正式的官署。说得通俗一点,这些人是陪皇帝玩的。到了晚唐,翰林院成了专门起草机密诏书的机构。到了北宋,翰林院已经是一个正式的政府机构,而且是精英最集中的机构。能够进入翰林院,是一种荣誉,代表着最受尊重的士大夫精英群体。在翰林院的苏东坡,想念起黄州的东坡。那一块东边的山坡,留下了他一生里一段痛苦的岁月,现在却成了有点甜蜜的回忆。苏东坡说,我离开之后有谁去过那里呢?那里应该已经荒凉了,雪压着小桥,因为没有足迹,看不到路。
3.
然后,他连用了两个“归去”,让人想到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陶渊明是归去田园,回到自己的家。苏东坡是要回到黄州的东坡,而不是眉州。春天的时候回去吧,那时候下着雨,落在江面上,正好是春耕的时候啊!“一犁”,这个犁,本来是耕田的工具,是名词,这里用作量词,和“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一蓑”是一样的用法,把名词量词化。这句话呈现出这样的意境:下雨和耕田的情景交融在一起。第二首词描述了当年东坡雪堂的春天生活,自己亲手种下的桃李,绿叶成荫,果实累累,窗外的鸟鸣惊醒了春睡中的苏东坡。现在身处翰林院的苏东坡提醒自己,“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在黄州时,苏东坡开始信佛,并称自己为“东坡居士”。在京城身处高位的苏东坡,怀念起当年黄州春天小桥流水的景象,还是称呼自己为居士。
4.
为什么春风得意的时候,苏东坡怀念起黄州那一段苦日子?为什么春风得意的时候,回忆起那段苦日子却有了甜蜜的感觉?为什么又提醒自己是一个居士呢?比较明显的理由,是苏东坡在春风得意的时候,都遇到激烈的权斗。第一次在朝廷工作,正好遇到王安石实行新法,士大夫分裂为新党和旧党,苏东坡作为旧党的核心人物,受到攻击、排挤。第二次回到朝廷工作,旧党领袖司马光担任宰相,苏东坡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但很快,苏东坡和他发生了意见分歧。苏东坡到地方历练了一圈,又经历“乌台诗案”沦落到黄州,对于民间的真实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不再像当初那样一概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觉得新法里的免役法还是很有实效的一项政策。
5.
但司马光比较极端,凡是王安石赞成的,他都反对。这让苏东坡非常苦恼,他在给杨绘的信里袒露了自己的心声,内容大意是说:我近来连续请辞,请求外派地方,但还没有得到允许。这些日子一直在闭门等待。反正我一定要离开翰林院了,想必你已经有所闻了,原因是台谏容不得我。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致此烦言,盖始于此。然进退得失,齐之久矣,皆不足道。在这段话里,苏东坡讲出了一个重点,就是当时的士大夫,一开始是政治见解不同,到后来就演变成派别之争。王安石当政时,不管什么原则,只看是不是跟随他。司马光当政,也不管什么原则,只看是不是跟随自己。
6.
苏东坡说,虽然跟随的人不一样,但性质是一样的,就是只讲立场,不讲原则,只讲站队,不讲大局。这是苏东坡对于政治失望的一个根本原因,这样的争斗毫无意义。苏东坡说自己虽然和司马光私交很深,但不会只是“跟随”,而是讲原则,不赞成的不会盲从。王安石和司马光、王安石和苏东坡、司马光和苏东坡之间,还是属于“君子之争”,不会意气用事,不会穿小鞋、使绊子。但其他同僚就不大一样了,有时候仅仅因为嫉妒就会发动攻击。苏东坡提拔太快,加上他弟弟苏辙也同时得到重用,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因此就受到了一些人的嫉妒。
7.
当时的孙升对司马光说:“苏轼这个人,翰林学士应该是极限了,不能再做更大的职位了。假如以文章写得好坏作为当官的标准,那么本朝的赵普、王旦、韩琦,都不是以文章出名。”孙升还上奏说:“辅弼经纶之业,不在乎文章学问。今苏轼之学,中外所服,然德业器识,有所不足。为翰林学士,可谓极其任矣,若或辅弼经纶,则愿陛下以王安石为戒。”孙升的看法,应该是代表了当时朝廷里大部分官员的一种普遍看法。一个人太红了,当然就会受到嫉妒。受到嫉妒,就容易被人找碴儿。苏东坡为进士候选任职的人出题目,出了这么一道题:“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媮tōu。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
8.
大意是,如今朝廷想效法仁宗皇帝的忠厚,但可能会引起各级官员因为皇帝忠厚而不尽心尽职的弊端;想效法神宗皇帝奋发有为,但可能会引起各级官员不能团结一致甚至苛求百姓的弊端。谏官朱光庭和苏东坡是进士同年,是理学家程颐的弟子。他上书告状,认为苏东坡的题目是在讥讽仁宗和神宗。他从苏东坡的题目里读出了这样的意思:“臣以为仁宗深仁厚德,如天下之为大,汉文不足以为也。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测,宣帝不足以为也,今学士院考试不识大体,反以媮tōu刻为议论,乞正考试官之罪。”苏东坡为自己辩护,他讲的媮刻,不是说仁宗和神宗,而是讲大臣不能很好地奉行,就会犯这样的毛病。最后他用了撒手锏,说这道题是经过御笔亲点的,假如有讥讽的意思,怎么可能逃过圣鉴呢?最后经皇太后裁定,苏东坡的题目没有问题。
9.
接着,右司谏吕陶,上疏弹劾朱光庭,认为他是报私仇。报什么私仇呢?这个上疏里讲了一件事,是关于苏东坡和程颐的。1086年10月11日司马光去世,那天正好有一个祀典,安放神宗的灵位到太庙。10月17日典礼结束,大家赶往司马光家吊唁。程颐却觉得这个时候不应该去吊唁,为什么呢?因为论语上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刚刚参加了热闹的典礼,不能马上就去参加丧礼,这样做不符合古礼。有人不以为然,说孔夫子只说“哭则不歌”,并没有说“歌则不哭”。一时间大家各说不一。这个时候,苏东坡说了一句:“此乃鏖áo糟陂bēi里叔孙通所制礼也。”
10.
叔孙通是汉朝立国之初规章和礼仪的制定者,据说他制定的这些规章礼仪都是有依据的。鏖糟陂是一个地名,是开封西南附近的一块烂泥地。鏖糟陂里的叔孙通,带有嘲笑的意思,是说程颐不过是学到了叔孙通的皮毛,并不懂真正的古礼。苏东坡自己认为这句话不过是一句调侃,因为他也说自己是“鏖糟陂里的陶渊明”,但程颐显然不太高兴。吕陶认为苏东坡和程颐因此结下私怨。程颐和他的哥哥程颢,都是理学大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很高,和周敦颐一起奠定了理学的基础,也是“天理”概念的创立者。苏东坡在文学史上地位很高。这两个人都很有建树,也很有才华,而且都是君子,但彼此因为性格不同,就是相互看着不顺眼。
11.
苏东坡给哲宗皇帝的奏状中说:“臣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色词,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他认为程颐这个人虚伪,而程颐则认为苏东坡很轻浮,思想根基很浅薄。司马光在世时,这些人还能勉强维持表面的团结。但在司马光去世后,程颐代表的洛党和苏东坡代表的蜀党,还有势力最大的刘挚、刘安世等人代表的朔党,形成了很激烈的派别斗争。苏东坡先是和洛党交锋,洛党被排斥之后,朔党和蜀党之间又是没完没了地相互攻击。从一件很小的事上就可以看出当时权斗的风格:挖历史。礼部郎中叶祖洽在十八年前考进士的时候,为了讨好王安石,说了一通“祖宗以来因循守旧”的话,鼓吹改革。十八年后给事中赵君锡把这件事翻了出来,予以举报。
12.
这让苏东坡感到非常厌倦,怀念起黄州的岁月,很想回归到那种清贫但是单纯的生活。从前苏东坡在密州,他在写给好友的诗歌里感叹密州的生活很艰苦,也很无趣。但是,京城虽然繁华好玩,却处处是党争的陷阱。所以,他宁愿在地方上,虽然处于边缘,却更逍遥一些,心不累。没有想到的是,多年后他再次回到朝廷,飞黄腾达,却怀念起被贬谪的居住地黄州。那一段艰苦的岁月,相比于权力斗争,也显得如此美好。所以,人的一生,有得必有失,你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却陷入复杂的人事纠纷;你遭遇了不幸的打击,远离了中心,却得到了清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