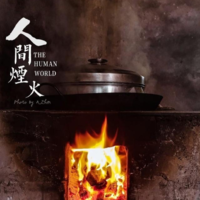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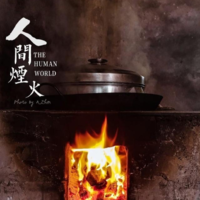
【1】果蔬秋浓
汪曾祺
1
中国人吃东西讲究色香味。关于色味,我已经写过一些话,今只说香。
水果店
江阴有几家水果店,最大的是正街正对寿山公园的一家,水果多,个儿大,饱满,新鲜。一进门,扑鼻而来的是浓浓的水果香。最突出的是香蕉的甜香。这香味不是时有时无,时浓时淡,一阵一阵的,而是从早到晚都是这么香,一种长在的、永恒的香。香透肺腑,令人欲醉。
我后来到过很多地方,走进过很多水果店,都没有这家水果店的浓厚的果香。
这家水果店的香味使我常常想起,永远不忘。那年我正在恋爱,初恋。
2
果蔬秋浓
今天的活是收萝卜。收萝卜是可以随便吃的——有些果品不能随便吃,顶多尝两个,如二十世纪明月(梨)、柔丁香(葡萄),因为产量太少了,很金贵。萝卜起出来,堆成小山似的。农业工人很有经验,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一般的,过了磅卖出去;这几个好,留下来自己吃。不用刀,用棒子打它一家伙,"棒打萝卜"嘛。咔嚓一声,萝卜就裂开了。萝卜香气四溢,吃起来甜、酥、脆。我们种的是心里美。张家口这地方的水土好像特别宜于萝卜之类的作物生长,苯蓝有篮球大,疙瘩白(圆白菜)像一个小铜盆。萝卜多汁,不艮,不辣。
红皮小水萝卜,生吃也很好,(有萝卜我不吃水果,)在我的家乡叫作"杨花萝卜",因为在杨树开花时卖。过了那几天就老了。小红萝卜气味清香。
南方的黄瓜不如北方的黄瓜,,水唧唧的,吃起来没有黄瓜香。
都爱吃夏初出的顶花带刺的嫩黄瓜,那是很好吃,一咬满口香,嫩黄瓜最好攥在手里整根咬,不必拍,更不宜切成细丝。但也有人爱吃二茬黄瓜——秋黄瓜。
3
呼和浩特有一位老八路,官称"老李森"。此人有一些不好的习惯,说起话来满嘴粗话。
我们请他到宾馆里来介绍情况,他脱下一只袜子来,一边摇着这只袜子,一边谈,嘴里隔三句就要加一个"我操你妈"。他到一个老朋友曹文玉家来看我们。曹家院里有几架自种的黄瓜,他进门就摘了两条嚼起来。曹文玉说;"你洗一洗!"—"洗它做啥!"
我老是想起这两句话∶"宁吃一斗葱,莫逢屈突通。"这两句话大概出自杨升庵的《古谣谚》。我为什么老是要想起这两句话呢?因为我每天都要吃葱,爱吃葱。
"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每年小葱下来时我都要吃几次小葱拌豆腐,盐,香油,少量味精。
羊角葱蘸酱卷煎饼。
再过几天,新葱——新鲜的大葱就下来了。
4
我在1958年被定为右派,尚未下放,曾在西山八大处干了一阵活,为大葱装箱。是山东大葱,出口的,可能是出口到东南亚的。这样好的大葱我真没有见过,葱白够一尺长,粗如擀面杖。我们的任务是把大葱在大箱里码整齐,钉上木板。闻得出来,这大葱味甜不辣,很香。
新山药(土豆,马铃薯)快下来了,新山药入大笼蒸熟,一揭屉盖,喷香!山药说不上有什么味道,可是就是有那么一种新山药气。羊肉卤蘸莜面卷,新山药,塞外美食。
苯蓝、茄子,都可以生吃。
5
逐 臭
"臭豆腐、酱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过去卖臭豆腐、酱豆腐是由小贩挑着担子沿街串巷吆喝着卖的。王致和据说是有这么个人的。皖南屯溪人,到北京来赶考,不中,穷困落魄,流落在北京,百无聊赖,想起家乡的臭豆腐,遂依法炮制,沿街叫卖,生意很好,干脆放弃功名,以此为生。这个传说恐怕不可靠,一个皖南人跑到北京来赶考,考的是什么功名?无此道理。王致和臭豆腐家喻户晓,世代相传,现在成了什么"集团",厂房很大,但是商标仍是"王致和"。王致和臭豆腐过去卖得很便宜,是北京最便宜的一种贫民食品,都是用筷子夹了卖,现在改用方瓶码装,卖得很贵,成了奢侈品。有一个侨居美国的老人,晚年不断地想北京的臭豆腐,再来一碗热汤面,此生足矣。这个愿望本不难达到,但是臭豆腐很臭,上飞机前检查,绝对通不过,老华人恐怕将带着他的怀乡病,抱恨以终。
6
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有一位女同志,南京人。爱人到南京出差,问她要带什么东西。
——"臭豆腐。"她爱人买了一些,带到火车上。一车厢都大叫∶"这是什么味道?什么味道!"我们在长沙,想尝尝毛泽东在火宫殿吃过的臭豆腐,循味跟踪,臭味渐浓,"快了,快到了,闻到臭味了嘛!"到了眼前,是一个公共厕所!
其实油炸臭豆腐干不只长沙有,我在武汉、上海和南京都吃过。昆明的是烤臭豆腐,把臭油豆干放在下置炭火的铁算子上烤。南京夫子庙卖的油炸臭豆腐干用竹签子串起来,十个一串,像北京的冰糖葫芦似的,穿了薄纱的旗袍或连衣裙的女郎,描眉画眼,一人手里拿了两三串臭豆腐,边走边吃,也是一种景观,他处所无。
吃臭,不只中国有,外国也有,我曾在美国吃过北欧的臭起司。招待我们的诗人保罗·安格尔,以为我吃不来这种东西。我连王致和臭豆腐都能整块整块地吃,还在乎什么臭起司!待老夫吃一个样儿叫你们见识见识!
不臭不好吃,越臭越好吃,口之于味并不都是"有同嗜焉"。
【2】拒绝乏味
谢冕
7
吃饭喝酒,是味觉上的享受,讲究的是味道。关于吃食,我说过一些话,被误传为谢某"不咸不吃"。其实不是,原意是∶该咸不咸,不吃。旅行在外,吃宾馆里的菜肴,往往苦于乏味,每道菜几乎都缺盐。记得那年,在南方某学校吃食堂,菜品繁多,目不暇接,缺点就是,太淡,寡味!因为是无所选择,于是每餐都自带食盐,免得每次都呼人送盐。
由此得出结论∶平庸的厨师不会也不敢用盐。他们宁肯寡淡,寡淡不担风险。而精明的厨师却是勇者,敢于用盐,往往一锤定音,而境界全出。
五味之中,盐是霸主,盐定位,糖提鲜,此理主厨者皆知。不会用盐,犹如医师开方,犹豫而不敢在主药下足分量,庸医于是就出现了。些大的、老字号的饭店,菜端上来,不用怀疑,就是这个味,因为厨师下手有数。其实,好饭店不一定要上高端珍品,能把普通菜做成精品才是名厨。没有窍门,其道理很简单,火候食材等因素除外,适量用盐最为关键。
8
我的一位朋友,吃饭很老到,他专拣大饭店点普通菜,便宜,到位。我说过的北大畅春园超市的饺子,每次吃,每次都满意,酱油、醋等不用外加,不假思索,张口就吃,也是因为到位,够味,"信得过"。
吃饭就是求味觉的满足,盐不到位,便乏味。这是就一道菜而言的,推而广之,就一次宴席而言,其理亦同。一桌人围坐,主人出于礼节,请客人各点一道菜。众人欣然曰∶"好好,还是点清淡些的。"结果八九人点出十几道菜——不是白菜豆腐,就是豆腐白菜。这场面我经历不止一次了,每次都很扫兴,也很尴尬。碍于情面,只能把不悦憋在心里∶这是吃饭还是比赛风雅?这里的潜台词,"清淡"是高雅而时尚的,要是点"清淡"以外的,就俗气了。于是,就满桌的白菜豆腐,豆腐白菜!
9
上面说的是集体会餐,一桌的寡淡让人郁闷。其实,所谓每人点一道菜,乃是西方的规矩,因为西餐是"各吃各的",每人点自己爱吃的一道主菜就行,无须考虑众人口味。中餐则不同,中餐是围桌而坐,讲究的是综合和协调。一桌人围坐,菜单一般是由主人预订的,有时也由主人临场发挥,当场点。除了宴请熟人朋友,我本人是轻易不敢临场发挥的,这不啻是一场"冒险",因为此时往往七嘴八舌,各主其是,结果则是莫衷一是。
我的经验是不轻易"发扬民主"而主张"独断",即由一人说了算。因为我深知众口难调。
10
点菜是一门高超的艺术,首先要考虑菜系,中国菜系繁多,各自特点突出,若在粤菜馆点水煮牛肉,就会贻笑大方,有人在川菜馆要求"不辣",也近于无知。中国菜南甜北咸,差别在天地之间。在无锡,犹如吴侬软语,往往甜得柔情万种;而在燕赵大地,则是重油重盐,犹如易水风寒,慷慨悲歌!晋人嗜酸,无醋不欢,霸气冲天;蜀地喜辣,红油火锅,挥汗如雨!所以,宴客点菜首先要考虑菜系,特别是这个菜系的名菜和招牌菜,这才"近于专业"。一桌成功的宴席,主事者除了了解菜系和菜馆,还要兼顾客人的组成,他们口味不一。荤菜素菜,软菜硬菜,爆、炒、汤、蒸,拼盘宜淡,主菜宜重,先轻后重,次第顺进,直抵高潮。高潮而后,这才甜食和果类登场,是甜蜜的余绪,宴会于是在暖意浓浓的"皆大欢喜"中圆满结束。
11
点菜难,因为这是一道调和众口的艺术。记得早年家里灶间,有祖传剪字,乃是先人手书的一副对联∶"此间大有盐梅手,以外从无鼎鼐(nai4)人"。此语有魏晋遗风,似是出自钟鸣鼎食之家。盐梅手,鼎第人,原指厨师,但此处却有题外之音。古人常把宰相比厨师,因为厨师知百味,大厨师更能协调众人之口味。能调百味者,相国之才也。因而"鼎鼐万家"说的不是厨师,而是大相国。
话扯远了,还是回到主人点菜上面来,此时环顾列座众人,想着各人的口味,南北西东,咸甜酸辣,理应兼顾而容人。主人首先重视的是"各悦其悦",再进一步,则是试图扩展他们的味觉,进而共享众人之悦。正是此时,厨师就跃身而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师"了。我知道"治大国若烹小鲜"这话的原旨,但更愿意借此以形容,我此时此刻的感受。点一桌菜,让大家开心,这里难道不包含更丰富的意义吗?常言道∶众口难调,此刻经高超的"厨艺"的调理,这古来的难题,却是迎刃而解!
12
食物缺盐是乏味,人生寡淡是乏味,我本南方人,家乡饮食偏甜,习性并不重盐。我的口味很宽,咸甜酸辣从不忌口,且常常奚落那些口味偏执而自诩为"美食家"者。
但即使如此,我仍对"缺那么一点盐"耿耿于怀!这说的是咸,甜也一样,不到位,也是败笔。几年前吃粤产萨其马,包装精致,一吃,就差一句国骂出口。这道京城名吃,既缺油,又不甜,又不酥软,全变味了。
在汉语中,"五味杂陈"是贬义,犹如"五色乱目""五音乱耳"一样。《老子》第十二章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指欲望多了易成反面,"口爽"者,诸味杂陈,反而伤败纯正的味道。这是道家的一种审美准则。而我斗胆不持此议,我认为饮食之道在于多样,"五味杂陈"方是正道。一桌酒席,甜酸苦辣咸,五味杂陈,让众口尝百味,从而改变人们的口味偏见和积习,乃是饮食应有之道,是为常态。
13
我始终我行我素,坚持我的主张∶有味,够味,恰到好处的足味,而断然拒绝的则是∶乏味。啤酒要冰而爽,咖啡要热且浓,杜绝温暾水。冷也好,热也好,甜也好,咸也好,都要各在其位,都要各显其能。愚生也钝,生性也许平和,处事也许雍容,但内心却是一团熊熊烈焰—热情,坚决,甚而激烈,这是品味饮食吗?不,也许是在追寻人生的一种境界。
【3】城市的幸事
蒋 韵
去年秋天到我的老师尤敏先生家做客,她请我喝西湖藕粉,吃黄桥小烧饼。因为她刚从苏杭和南京回来,又因为她本是苏州人,向来喜欢江南点心。西湖藕粉端上来,扑鼻一股桂花香。先生说∶"是新鲜的桂花糖,从杭州带来的。刚买来时,香得不得了,这一路走回来,香味已经淡多了。"
我听得出话中怀乡的那点惆怅。至于桂花糖,久居北方黄土高原的我实在没有多少资格说三道四去品评。我又曾见过几棵桂花树呢?但我知道在我老师的家乡,在江南,或者说是在昔日的江南,做桂花糖也算是三秋的盛事胜景之一吧。
14
我很喜欢到老师家做客,这怕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在老师这里,常有某种意外之喜。比如这样一小碗西湖藕粉,比如这应时应景的新鲜桂花糖,东西也许并不值钱,难得的是"应时应景"这四个字。在暮秋的北地,想起斜阳中的满觉陇,想起《迟桂花》想起"十里荷花,三秋桂子"的前人词章,喜悦或感慨,是这一小碗点心盛不下的。
冬天去老师家,若赶上吃饭,也不须客气,坐下来,喝的是老师刚刚暖好的黄酒,绍兴加饭或花雕,里面加几粒话梅,那纯粹是为了迎合我这个北方学生的口味。
有一次说起张爱玲,我说她在《半生缘》里写到一种南京的小菜,叫莴笋圆子,是把莴笋腌了盘起来,中间塞一朵干玫瑰花。春节老师招饮留饭,一大桌盛馔里面,有一小白瓷碟,碟中赫然摆了几只绿莹莹的莴笋,只只中心开一小朵紫玫瑰。老师笑道∶"特为你准备的,张爱玲的小菜,是亲戚从南京带来的。"
15
老师的丈夫梁先生是南京人,有亲戚从南京来,带只板鸭、盐水鸭或鸭胗之类是可以想到的,带来家制的腌菜——莴笋圆子,若不是老师特意托付了,谁会想到带这种东西来呢?这是整个春节期间,我吃到的最有味道的东西。
如今有一句话,叫"吃气氛"。为此,有人不惜一掷千金。水晶吊灯、进口墙布、红木餐桌都打在菜价里了,当然还包括玫瑰花、
KTV 以及小姐的微笑等。路易十三是"气氛",波尔多干红、轩尼诗XO是"气氛",龙虾船是"气氛",玉米棒子和老南瓜也是"气氛",只要你肯花钱。花钱买来的气氛,或辉煌,或高贵,或典雅,或怀旧,但它总缺少一点什么。
就像精彩绝伦的假花。
还有另外的气氛,大约已被我们遗忘了。比如,"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再比如,"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还比如,"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这样的气氛和情致,可是买不到的。
16
所以,在今天,在我们日益进步和喧哗的城市,能有这样一处地方,为我们安静而从容地保留一小碗应时应景的西湖藕粉和新鲜桂花糖,保留几只故事性的玫瑰莴笋圆子,应该说是我们城市的幸事。
上面这段小文,写于1996年6月,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如今的尤敏老师,早已移居海滨城市大连,和女儿一家生活,而她的丈夫梁先生,则因罹患癌症去世多年。梁先生生病,住院,手术,化疗,这期间,我们几个学生,和尤老师一起,共同经历了那折磨人的一切。记得最后一次我和李锐去看梁先生,他已是骨瘦如柴,气息奄奄,却笑着,对我们说∶"等我出院了,我请你们去吃海鲜,去'海外海'。"
我也笑着,回答说∶"好,我们等您请客。"
其实,都知道,那已是永远不可能的事了。
自梁先生往生后,尤老师也曾回过几次我们的城市,我们去先生家里看望她,却再也没有吃过她亲手烹制的美味。往往,是就近找一处饭店或者咖啡屋,大家随便吃一餐便饭而已。没有人比我们更明白,在这个城市,我们的老师,只剩下了一座寥落的空屋,而没有了一个人间烟火的家。那些美好的日子,如大风吹落的花瓣,永别了。
【4】娃娃过年
叶梅
17
过年,是应当有年味的。
娃娃对年的味道比大人敏感,那些妙处,是童年最有趣的记忆。
儿时在三峡一带住着,小小的巴东县城,一条独街,多是板壁屋,天梯巷吊脚楼,从长江边曲里拐弯一直到金子山顶。房屋两侧多是橘树,每到晚秋初冬,小灯笼似的橘子就都红了,丛丛点点,好比娃娃的笑脸。
橘子红了的时候,大人们就会念叨,日子过得真快,转眼就又要过年了!听到的只言片语让娃娃们欣喜若狂,俗话说;大人盼种田,细娃盼过年。还有什么比过年更有趣,更好呢?
真正的过年是从腊月二十四开始的。
这一天要打扫"扬尘"。屋里屋外,把家具倒腾开,扫帚伸进去将一年的尘垢扒出来,墙角上方的蜘蛛见势不妙,急急慌慌赶紧逃开了,留下一面破碎的网,摇呀摇,娃娃叫嘎嘎(三峡人把外婆都叫"嘎嘎")∶"这里还有呢。"嘎嘎的扫帚像一支笔,伸到哪儿,哪儿就干净了。
18
家里打扫清爽之后,开始炒各种香嘴的吃食,
花生、瓜子、蚕豆、板票,还有三峡人爱吃的苞谷花、茗片、洋芋片。不讲究的人家花式不多,但一两样也总归是要炒的;而会过日子的人家都会有一包炒砂,年年炒得黑油油的,一颗颗砂子带着力道。
炒熟的花生摊在簸箕里,抓起来烫手,嘎嘎一边炒一边扭过脸来制止,说∶"凉一凉再吃啊,还没凉吃了要上火的啊!"娃娃不管什么上火,抓一把塞到嘴里,果然喷香喷香,便沉不住气地欢跳,抓上一把揣进荷包里,再抓一把,再抓一把,然后夺门而跑,去找隔壁的娃娃。
腊月间还要炸丸子、蒸扣肉。三峡的习俗是提前把过年的菜都准备好,等到正月里相互拜年请客人吃饭时,家里都有现成的硬菜,一蒸一煮就能上桌。做这些菜都是系列工程。娃娃对那些技术不感兴趣,关心的只是结果,看嘎嘎从蒸笼里取出一碗碗扣肉,整齐排放在橱柜里,却并不急着给娃娃吃,就知道真的是要过年了。说起来,三峡的土家族比汉人要提前一天团年,在腊月二十九这天,叫作过"赶年"。有说是因为祖先当年被人追杀,不得不提前一天过年;有说是因为明代时期,土家族士兵奉调东南沿海出征抗倭,军令紧急只好提前过年。无论哪种说法,团年都是件最重要的事。
19
这天,家人无论在何处都要赶回家里,先祭拜祖先,然后依次上桌。团年席上虽也说笑,但不像吃创汤那样随意,且是庄重的,娃娃的衣裳扣子被扣得规矩,大人们更是穿戴齐整,大家围着桌子正襟而坐。娃娃看满桌的菜肴热气飘拂,心里不免着急,但也得等大人把祝福的话说了才能动筷子,且有些菜是不能动或是不能吃完的,尤其是鱼,几乎只是摆放在那里一动不动。有吃有剩,年年有鱼(余)。
娃娃喜欢跟全家人坐在一起,二舅舅的心上人远道而来,笑起来眼睛弯弯的,一对乌黑的大辫子,给娃娃带来好多柿饼、核桃、苞谷糖,娃娃觉得她长得真好看,就愿意挨着她坐。团年的这天晚上要洗澡,这是娃娃从小懂得的规矩,嘎嘎一边给娃娃洗,一边特意在膝盖那里多抹几下,说三十晚上洗了髁膝包,走到哪里都会有肉吃。这话也不知旁人是否知晓,但娃娃铭记在心,后来的若干年里,团年那天都要安排全家人洗澡,哪怕电视台的春晚已经成了三十夜的唯一、也宁可牺牲那些节目,澡是要洗的。否则,要没有肉吃了怎么办?
20
团年之后要守岁,那时娃娃年年都下决心,要跟大人们一样,守着炉火说话,直到天明。嘎嘎有很多故事,都在这时候讲述,但听着听着,娃娃就不由自主地东倒西歪了。
等到醒来,却听窗外响着鞭炮,枕边放着新衣,娃娃心里好喜欢。又突然想起,枕头下会不会有压岁钱,果然一摸就摸到了,小小的一张钱币,有时是一毛,有时是两毛,娃娃心满意足。就在那一刻,感觉自己又长大了一岁,向着成年人的光景,那时候娃娃是多么希望快点长成一个大人啊。
过年是要穿新衣的,每年都不同,红底紫花,灯芯绒,带着暖暖的布香,娃娃穿上之后,觉得街上所有的人都在朝自己看,连路都有些不会走了。
21
正月里,大人领着娃娃走亲访友,去四处拜年,好吃好喝好玩的,都有。娃娃们在一起感慨,要是天天都过年,那该多好啊。俗话说,"正月忌头,腊月忌尾",不说不吉利的话,不做伤和气的事,娃娃们在这些日子里,就从来没有挨过骂。
过完上九日,接下来是大家最爱的元宵节,这一天娃娃所在的巴东县城会大张旗鼓地玩龙灯,上码头、下码头,金子山、河对岸,玩龙灯的各有一班,在街心打开了擂台,随着震天的锣鼓,全城都在沸腾。美女姐姐扮了蚌壳精,躲在彩灯闪闪的蚌壳里,壳一开一合,逗引得娃娃们只想往里钻。那姐姐红衣绿裤,粉团团的脸儿,
半天不出来,娃娃的脖子都伸疼了,却是神秘诱人得很。一旁伴着蚌壳精的少年,拿着一把扇子,搞过来舞过去,最后终于用一根红绸牵出了俊俏的蚌壳精,娃娃随着大家一起欢呼。
22
娃娃们最期待的龙灯在一阵紧似一阵的锣鼓声中飞奔而来,那龙的一双大眼,通常比娃娃的头还要大,它上下飞旋,时而一掠而过,时而紧盯着娃娃,似有无穷深藏的话语,只对娃娃说。娃娃深信无疑,但一切还没来得及,元宵节的夜晚就快过去了,娃娃的绣花新鞋在拥挤之中,差点被人踩掉,嘎嘎在鞋面上绣的一对小兔子,眼睛也都红了。嘎嘎说∶"快去睡吧。"娃娃说∶"不睡,年还没过完呢。"
"有心拜年,端午不晚",这也是三峡一带的俗话,那年岂不是会一直过到端午?娃娃一厢情愿,总拿这话问嘎嘎。一直问到端午时节,嘎嘎包粽子,将一束菖蒲挂在门前,然后带着娃娃去长江边看龙舟,只听那鼓声如雷,千船万船一时竞发,娃娃这时才把年给忘了。
【5】故乡的吃食
迟子建
23
北方人好吃,但吃得不像南方人那么讲究和精致,菜品味重色暗,所以真正能上得了席面的很少。不过寻常百姓家也是不需要什么席面的,所以那些家常菜一直是我们的最爱。
如果不年不节的,平素大家吃的都很简单。由于故乡地处苦寒之地,冬季漫长,寸草不生,所以吃不到新鲜的绿色蔬菜。我们食用的,都是晚秋时储藏在地窖里的菜∶土豆、萝卜、白菜、胡萝卜、大头菜、倭瓜,当然还有腌制的酸菜和夏季时晒的干菜,比如豆角干、西葫芦干、茄子干等。人们喜欢吃炖菜,冬天的菜尤其适合炖。将一大盆连汤带菜的热气腾腾的炖菜捧上桌,寒冷都被赶走了三分。人们喜欢把主食泡在炖菜中,比如玉米饼和高粱米饭,一经炖菜的浸润,有如酒经过了岁月的洗礼,滋味格外的醇厚。
24
而到了夏季,炖菜就被蘸酱菜和炒菜代替了。园田中有各色碧绿的新鲜蔬菜,菠菜呀,黄瓜呀,青葱呀,生菜呀,等等,都适宜生着蘸酱吃,而芹菜、辣椒等则可爆炒。这个季节的主食就不像冬天似的以干的为主了,这时候人们喜欢喝粥,芸豆大精子粥、高粱米粥以及小米绿豆粥是此时餐桌的主宰。
家常便饭到了节日时,就像毛手毛脚的短工,被打发了,节日自有节日的吃食。先从春天说起吧。立春的那一天,家家都得烙春饼。春饼不能油大,要擀得薄如纸片,用慢火在锅里轻轻翻转,烙到白色的面饼上飞出一片片晚霞般的金黄的印记,饼就熟了。烙过春饼,再炒上一盘切得细若游丝的土豆丝,用春饼卷了吃,真的觉得春天温暖地回来了。除了吃春饼,这一天还要"啃春",好像残冬是顽石一块,不动用牙齿啃噬它,春天的气息就飘不出来似的。我们啃春的对象就是萝卜,萝卜到了立春时,柴的比脆生的多,所以选啃春的萝卜就跟皇帝选妃子一样周折,既要看它的模样,又要看它是否丰腴,汁液是否饱满。很奇怪,啃过春后,嘴里就会荡漾着一股清香的气味,恰似春天草木复苏的气息。
25
立春一过,离清明就不远了。这一天人们会挎着篮子去山上给已故的亲人上坟。篮子里装着染成红色的熟鸡蛋,它们被上过供后,依然会被带回到生者的餐桌上,由大家分食,据说吃了这样的鸡蛋很吉利。而谁家要是生了孩子,主人也会煮了鸡蛋,把皮染红,送给亲戚和邻里分享。所以我觉得红皮鸡蛋走在两个极端上∶出生和死亡。它们像一双无形的大手,一手把新生婴儿托到尘世上,一手又把一个衰朽的生命送回尘土里。所以清明节的鸡蛋,吃起来总觉得有股土腥味。
清明过后,天气越来越暖了,野花开了,草也长高了,这时端午节来了。家家户户提前把风干的粽叶泡好,将糯米也泡好,包粽子的工作就开始了。粽子一般都包成菱形,若是用五彩线捆粽叶的话,粽子看上去就像花荷包了。粽子里通常要夹馅的,爱吃甜的就夹上红枣和豆沙,爱吃咸的就夹上一块腌肉。粽子蒸熟后,要放到凉水中浸着,这样放个两天三天都不会坏。父亲那时爱跟我们讲端午节的来历,讲屈原,讲他投水的那条汨罗江,讲人们包了粽子投到水里是为了喂鱼,鱼吃了粽子,就不会吃屈原了。我那时一根筋,心想∶你们凭什么认为鱼吃了粽子后就不会去吃人肉?我们一顿不是至少也得吃两道菜吗!吃粽子跟吃点心是一样的,完全可以拿着它们到门外去吃。门楣上插着拴着红葫芦的柳枝和艾蒿,一红一绿的,看上去分外明丽,站在那儿吃粽子真的是无限风光。我那时对屈原的诗一无所知,但我想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因为世上的诗人很多,只有他才会给我们带来节日。
26
端午节之后的大节日当属中秋节了。中秋节是一定要吃月饼的。那时商店卖的月饼只有一种,馅是用青红丝、花生仁、核桃仁以及白糖调和而成的,类似于现在的五仁月饼,非常甜腻。我小的时候虫牙多,所以记得有两次八月十五吃月饼时,吃得牙痛,大家赏月时,我却疼得呜呜直哭。爸爸会抱起我,让我从月亮里看那个偷吃了长生不老药而飞入月宫的嫦娥,可我那双朦胧的泪眼看到的只是一团白花花的东西。月光和我的泪花融合在一起了。在这一天,小孩子们爱唱一首歌谣∶蛤蟆蛤蟆气鼓,气到八月十五,杀猪,宰羊,气得蛤蟆直哭。蛤蟆的哭声我没听到,倒是听见了自己牙痛的哭声。所以我觉得自己就是歌谣中那只可怜的蛤蟆,因牙痛而不敢碰中秋餐桌上丰盛的菜肴。
中秋一过,天就凉了,秋风把黄叶吹得满天飞。雪来了。雪一来,腊月和春节也就跟着来了。都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所以到了腊八的时候,人们要煮腊八粥喝。腊八粥的内容非常丰富,粥中不仅有多种多样的米,如玉米、高粱米、小米、黑米、大米;还有一些豆类,如芸豆、绿豆、黑豆等,这些米和豆经过几个小时的慢火熬制,香软滑腻,喝上这样一碗香喷喷的粥,真的是不惧怕寒风和冰雪了。
27
一年中最大最隆重的节日莫过于春节了。我们那里一进腊月,女人们就开始忙年了。她们会每天发上一块大面团,花样翻新地蒸年干粮,什么馒头、豆包、糖三角、花卷、枣山,蒸好了就放到外面冻上,然后收到空面袋里,堆置在仓房,正月时随吃随取。除了蒸年干粮,腊月还要宰猪。宰猪就是男人们的事情了。谁家宰猪,那天就是谁家的节日。餐桌上少不了要有蒜泥血肠、大骨棒炖干豆角、酸菜白肉等令人胃口大开的菜。
人们一年的忙活,最终都聚集在除夕的那顿年夜饭了。除了必须要包饺子之外,家家都要做上一桌的荤菜,少则六个,多则十二、十八个,看到盘子挨着盘子,碗挨着碗,灯影下大人们脸上的表情就是平和的了。他们很知足地看着我们,就像一只羊喂饱了它的羊羔,满面温存。我们争着吃饺子,有时会被大人们悄悄包到饺子里的硬币给硌了牙,当我们"当啷"一声将硬币吐到桌子上时,我们就长了一岁。
【6】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
郭慕清
28
是夜。炖了一小锅萝卜牛腩,盛一碗,低头趴在碗上闻一闻,弥漫的热气扑到了眼镜上,摘下眼镜,用木质小勺舀一点,慢慢入口,有些烫,咂巴咂巴嘴,竟然是出奇的香。
汤里并没有放什么名贵的调味料和滋补药材,只有萝卜、牛腩、水和盐,简简单单,清清爽爽,味美大抵是因为熬久了一些。
熬得久,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词,于菜品,于人生,道理如一。有几年,日子过得比较艰苦,总是碰壁,也曾在深夜里痛哭。问父亲;"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却没有收获?不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吗?"父亲答∶"熬得久了总会收获。"
就像田野里一望无垠的麦子,虽然饱经三九腊月的凛凛寒风,虽然在春天里憋着劲儿蹿个子,但哪怕差一分一秒熬不到炎炎夏日,麦穗就不能在阳光下发出金色的光芒。
29
熬得不久,还差一点火候,麦穗便不会低头,牛腩汤就不会鲜美,事情也不会功成。大道至简,煮菜看似煮的是一粥一汤,却包含着万千世界,不是吗?
说到由美食悟人生之道,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汪曾祺。他的《谈吃》,文字明白如话,娓娓道来,将食材来历、食客品味和食宴氛围讲得头头是道。这酸甜苦辣的人生况味,在舌间萦绕,对生活的热爱也跃然纸上,世俗烟火和琴心雅韵相契相合,毫不违拗。
汪曾祺谈到昆明一处的炒菠菜甚是美味。为什么呢?油极大,火甚匀,味极美。他和蔡澜对吃的看法一致,推崇袁枚《随园食单》中所提的"素菜荤做"。
30
这讲的是用荤料来增添素菜的丰富性,挖掘简单食物的别样风致。就像是芦蒿炒腊肉,单炒野生芦蒿,会有些青涩,难以入口,但是在烹炒的时候,稍稍添一点点腊肉借味,就大为不同,更能尝出芦蒿的清和鲜。
真正的"素菜荤做"其实来自潮州菜。据说,清代康熙年间,潮州开元寺举办过厨师厨艺大比试,参加比试的皆为潮汕一带寺庙主理厨政的厨子,在比试项目中,便有烹制"八宝素菜"这一项内容。
"八宝素菜"是潮州素菜的传统名肴,是由莲子、香菇、草菇、冬笋、发菜、白菜、腐枝、栗子共八种纯素食材做成。有一位来自意溪别峰寺的厨师,十分聪明,也深谙素菜一定要荤做的食理,即这八种素食,一定要用肉类炊炖,荤素结合,味道才能浓郁。可是这次比试是在佛寺里举行的,绝不能携带排骨、老母鸡等肉类食材进寺。
31
怎么办呢?这位厨子久久苦思,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在比试的前一天,他在家先用排骨、老母鸡、赤肉熬制了一锅浓浓的汤,然后将一条洗干净的毛巾放在锅里煮,再把毛巾晾干。第二天比试的时候,他手提装满食材的篮子,将毛巾搭在肩上,把门的和尚没有发现肉类,便放他进去了。做菜时,他将毛巾放入锅中煮片刻,让毛巾中的肉味溶解到锅里,然后加在菜肴之中,从而夺得了比赛的头名。《红楼梦》第四十一回里,贾宝玉曾道∶"这些破荷叶可恨,怎么还不叫人来拔去?"倒是林黛玉想起残荷听雨的美,谈到李商隐那首诗∶"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残荷听雨声。"秋夜寂寥,由天瓢泼下一场急雨,雨滴敲打在残荷上,脆响如铃,宛如天籁,让人能在繁华褪尽的萧索里,心生坦然对枯荣、静观世事沉浮的成熟和豁达。
绘一幅画,觅一份爱,和做菜其实并无二致,少不得那些看似错落,实则有致、入味的搭配。菜一素一荤,够香。书画的一枯寂一丰富,入禅化境。爱人性情的一急一缓,一英雄豪迈一温柔如水,彼此搀扶,情投意合。
这世界万物,道理万千,其实也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
感谢大家的倾情共读,祝大家读文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