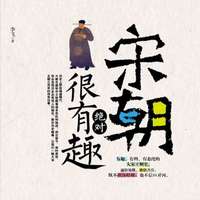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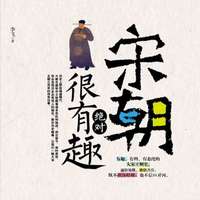
《宋朝绝对很有趣》作者:李飞
尊重知识产权,转载仅供读文练习,如侵联删
———————————————————————
1.
—— 来之不易的皇位 ——
赵昚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寿王赵德芳的六世孙,生于秀州(今嘉兴)。因为赵匡胤传位给弟弟赵光义,从此以后,当皇帝的从宋真宗赵恒直到南宋的高宗赵构,全都是太宗的子孙,太祖的子孙完全没有机会。
赵昚被赵构养在宫中二十多年,一直没有确立太子的身份。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赵构一直在尽力医治自己那个不育症,总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有个亲生儿子来继承帝位;二是秦桧和他手下的那批投降派始终从中作梗。秦桧自己的儿子秦熺是个无能之辈,他看赵昚聪明能干,唯恐将来秦熺对付不了赵昚,保持不住相位,就一再出坏主意,建议赵构对接班人一选再选,总想挤掉赵昚。君臣二人在选太子的问题上勾心斗角,各有各的打算。赵构希望选个聪明能干的,秦桧希望选个庸碌无能的。从幼童到成人,赵昚通过二十多年的多次挑选,终于突破重重难关,坐上了帝位。
2.
在幼童时代的竞争中,赵昚以他的沉静而不浮躁而引人注目,打败了那些逗猫惹狗的顽童,进入了皇宫。在少年时代的竞争中,赵昚以他读书的过目不忘与应对进退的彬彬有礼压倒了他的对手赵琢。虽然赵构自己荒淫无度,但是他却不愿自己的接班人也荒淫无度,所以才为已经成年的两个候选人出了一道很厉害的考题,那就是对赵昚、赵琢两人各赐十名美人作为侍女。赵昚的师傅史浩对赵昚敲响了警钟,他说:“这是对你的一次重要考验,你要经得起考验才行。这些美人都是伺候过皇上的,你也不用管她们和皇上有什么关系,对她们尽量尊重,以对庶母之礼对待,绝对不会有错。”果然,不久之后,赵构把这二十名美人召回,一一询问和检查,发现赵琢和那十名美人全都有了说不清的关系,而赵昚对这十名美人则是彬彬有礼,秋毫无犯。赵构十分高兴,随即拍板,决定立赵昚为太子。
3.
赵构把赵昚一直养在宫中,养到三十多岁还不肯立为太子。这时候为什么一下子就想通了,这中间还有个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当时的金兵一再南侵,虽然依靠许多忠勇将士抵挡了一阵,他总担心一旦抵挡不住,金兵打过江来,他就会像父兄一样,再当俘虏。他已造好了几百艘大船,准备在情况紧急时可以下海逃命。但是这个皇帝的名义是个包袱,有了这个名义他就不能先走。如果他丢下臣民不管自己先去逃命,别人就可能乘机推翻他。倒不如学一学他父亲赵佶的办法,早日禅位给太子,到时候自己可以逃命;以后形势好转,他还可以回来当太上皇,依然掌握实权,决定国家大事;如果形势恶化,他就可以驾着大船一直逃到海外去,而由新皇帝来为自己当替死鬼。
4.
赵构于1162年5月底册立了太子,6月就进行禅位,自己当了太上皇。他在退位之前,已经做好了屈膝和谈的一切准备,起用秦桧余党汤思退任宰相,并且下诏撤销专为抗金而设立的招讨司,从各方面捆住赵昚的手脚,不许他放手抗金。
赵昚即位后,当时著名史学家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中有意记录了赵光义谋杀太祖父子三人的蛛丝马迹,让其流传后世。赵昚知道自己是太祖后代,也理解民间一直有同情太祖子孙仇视赵光义的心理,亲自审阅书稿时就对李焘的记载抱支持与认可的态度,让赵光义的劣迹永远流传后世。赵构对此当然有所察觉,但是不便说明,因为他是赵光义的子孙,一旦明说,引起争论,会把赵光义的丑事揭得更多,反为不美。这样的事,只好打肚皮官司。 又如赵昚对岳飞非常推崇,在他未成年时,岳飞曾经来见过他,和他有过一次长谈,还引起过赵构的怀疑。岳飞被害时,他才十四五岁,心中非常不满。
5.
对于赵构,因为是义父,不便正面指责,对于秦桧,就少了一层顾虑,每每在议事时不客气地加以贬斥。秦桧也把他当作眼中钉,曾经多方活动,想把这个接班人拉下马来,只因为有很多正直的官员在力保他,赵构自己也以立了太祖之后能够顺应民情,有讨好臣民的作用,不能轻动,才没听秦桧的话。在给岳飞平反这件事情上,虽然是赵构所同意,但是赵构只是在金兵重新南侵的时候,迫于舆论的压力,不能不同意做有限度的平反,好给前线将士一个交代。但是赵昚在自己即位后,就大张旗鼓地给岳飞平反,完全超出了赵构所划定的范围,对岳飞评价之高,前所未有,对因受岳案所牵连的人员一一官复原职,慰勉有加。他的这些做法赢得了老百姓一片喝彩之声,给自己带来很高的威望。对岳飞评价很高,也就相对地贬低了谋害岳飞的赵构与秦桧,当然为赵构所不满,这是父子两人大打肚皮官司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6.
—— 隆兴北伐和隆兴和议 ——
孝宗是南宋最想有所作为的君主,也是南宋唯一志在复国的君主。他一即位,就召主战派代表张浚(非陷害岳飞之张俊)入京,共商复国大计,任命他为江淮宣抚使。高宗很不以为然,对孝宗说:“毋信张浚虚名,将来必误大计,他专把国家名器财物做人情!”对孝宗的恢复大计也大泼冷水道:“等我百年以后,你再筹划这事吧!”但孝宗起用张浚、准备抗金的决心已定,向朝臣公开说:“朕倚魏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隆兴元年(1163年)正月,他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史浩升为右相,当时左相是陈康伯。
7.
史浩是孝宗潜邸老师,他在孝宗走向皇位的途中起过不小的作用,号称智囊,因而颇受尊重。但在对金问题上,他却是个安于现状的主和派,对孝宗锐意北伐始终持反对态度。当时,西线吴璘在金主完颜亮南侵时不仅成功抵挡了金军的攻势,还攻占了原所属北宋的十六个州,收复失地之广前所未有。但史浩却以孤军深入为理由,让孝宗下诏命令吴璘退兵保蜀,不仅使十六州得而复失,而且使撤退的宋军在金军的反攻下伤亡两万余人。孝宗知道真相后大呼“史浩误我”,再授权吴璘得以自行决定进退,但已机会难再了。在东线,史浩也主张放弃两淮,固守江南,因张浚抵制,才未实行。
8.
大约到金大定二年(1162年)岁末,金世宗立足已稳,他做过与宋讲和的努力,但遭到了拒绝,便派仆散忠义为都元帅坐镇开封,统一指挥黄河以南的各路金军,对南宋实行以战迫和的政策。冬去春来,金军更加紧了南攻的准备,大将纥石烈志宁进兵灵壁(今属安徽),同时致书张浚,以战争相威胁。
在这种态势下,南宋朝廷中和战两派也不得不摊牌。张浚主张孝宗北上建康督战,下诏出师北伐。他指出:中原久陷,今不规复,其他豪杰必起而取之。史浩则针锋相对地反驳:若中原真有豪杰却不能亡金,正证明金人统治的稳固,未可贸然出兵。和战双方辩论多日,孝宗最终决定北伐。
9.
隆兴元年四月,为了防止主和派的反对,孝宗绕过三省与枢密院,直接向张浚和诸将下达北伐的诏令。高宗闻讯,急召孝宗企图迫使他收回成命,孝宗沉默不语表示拒绝。史浩因宰相不得与闻出兵大事愤而辞相,孝宗同意他出知绍兴府。史浩主张放弃陕西与两淮确是馊主意,但反对草率北伐仍有可取之处。
张浚接到北伐诏令后,星夜赶回建康,调兵八万,号称二十万,一路由李显忠率领取灵壁,一路由邵宏渊指挥攻虹县(今安徽泗县)。李显忠原是陕西骁将,一家二百余口遭金军杀害,后辗转至临安,因力主抗金而被秦桧贬官削职,金主完颜亮南侵时才被起用,被张浚视为干将。五月,李显忠顺利攻克灵壁,而邵宏渊久攻虹县不下,还是李显忠派灵壁降卒前去劝降,虹县守将才放弃抵抗。
10.
邵宏渊争强好胜,对虹县战功不出于己深以为耻,恰巧他的士兵抢了金朝降卒的佩刀,被李显忠斩首示众以儆效尤,因而对李显忠憋了一肚子气。李显忠建议邵宏渊乘胜进攻宿州(今安徽宿县),邵宏渊酸溜溜地说:“你可真是关西将军啊!”见对方不予呼应,李显忠只得独率己部发起进攻,城破,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这时,邵宏渊才投入战斗。攻下军事重镇宿州的消息,令孝宗与张浚大受鼓舞,指示他们扩大战果。
但前线两将的矛盾却趋于激化。孝宗升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他耻居李下,向张浚表示拒绝接受李显忠的节制。张浚迁就了他的无理要求,使他更有恃无恐。他提议将宿州府库中的钱帛全部拿来赏赐给士兵,李显忠只同意每三个士兵赏一千钱,却放纵自己亲信部曲恣意搬取。其时南宋军队都是吃饱拿足的骄兵悍将,一经挑唆,拒绝受赏,人心立时浮动。
11.
金将纥石烈志宁率先头部队万余人来攻宿州,被李显忠击败。但金军十万主力随即赶到,李显忠奋力苦战,邵宏渊不仅按兵不动,还对部众大讲风凉话:“这大热天的,摇着扇子还不凉快,何况在大日头下披甲苦战呢!”于是,军心溃散,无复斗志。
入夜,邵宏渊部中军统制周宏自为鼓噪,扬言金军来攻,宋军不战自溃。金军乘虚攻城,李显忠杀敌两千余,终于独力难支,浩叹道:“老天未欲平中原耶?何苦阻挠如此!”遂率师而退,行未多远,宋军就全线崩溃,军资器械丧失殆尽。所幸金军不知底细,不敢贸然追击,宋军才在淮河一线稳住了阵脚。宿州旧郡名符离,故史称这场溃败为“符离之溃”。
12.
符离之败使宋金交涉向不利于南宋一方的倾斜,也使南宋主和派有了发难的把柄。张浚不得不提出辞呈,好在孝宗还不想立即放弃北伐计划,他给张浚回信说:“今日边事,倚卿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怀犹豫,前日举事之初,朕与倾任之,今日亦须与卿终之。”张浚降为江淮宣抚使,部署两淮防线,抵挡金军南下。
符离之败对孝宗北伐雄心的打击是沉重的,他也发现恢复大业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开始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六月,孝宗让主和派代表汤思退复出,不到一月,就让他担任右相。与此同时,主战的张焘、辛次膺和王十朋等相继出朝。八月,孝宗恢复张浚都督江淮军马的职务,同时采纳汤思退的建议,派淮西安抚使干办公事卢仲贤前往金军大营议和。
13.
十一月,卢仲贤带来了金军统帅仆散忠义致南宋三省与枢密院的函件,议和条件为:宋帝与金帝改为叔侄关系,宋朝归还被占的海、泗、唐、邓四州,归还降宋的金人,补纳绍兴末年以来的岁币。
南宋朝廷的和战双方再次展开激烈辩论,最后太上皇高宗出面为主和派撑腰,孝宗才决定继续遣使议和。十二月,陈康伯因病辞去相位,向孝宗推荐张浚自代。但太上皇指令让汤思退升为左相,地位在右相张浚之上,以为牵制。尽管如此,主战派仍自觉实力大增。
隆兴二年正月,金帅仆散忠义再次来函,要价太高,口气忒硬。孝宗在主战派的鼓励下,将卢仲贤以擅许四州的罪名除职,编管郴州,改派胡昉出使金营,表明宋朝拒绝归还四州,否则将中止和议。和议陷入僵局。孝宗命张浚视师两淮,全力备战,准备与金军一决雌雄。
14.
张浚招徕山东淮北的忠义之士万余人,补充建康、镇江的正规军,增修两淮城堡工事,添置江淮战舰,随时奉命待发。汤思退及其同党百般攻击张浚,污蔑他“名曰备守,守未必备,名曰治兵,兵未必精”。孝宗最终屈从了主和派的压力,四月,召张浚还朝,罢去了他的相位。四个月后,张浚死在离京途中,遗嘱说:“我曾任宰相,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死后不配葬在祖宗墓侧,葬在衡山下足矣。”
张浚是南宋前期主战派重要代表,但从富平之战与隆兴北伐来看,他在军事上的全局决策是并不成功的,其中固然有当时宋军素质与双方力量对比等客观原因,但其志大才疏而急于求成的个人因素,也是无可讳言的。
15.
王夫之批评他“志大而量不弘,气盛而用不密”,可谓知人之论。他的遗言倒是真情实话,道出了自己的终生遗憾。总之,他一生坚持抗金,虽受秦桧迫害而不改初衷,终究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张浚罢相,汤思退独相达半年之久,孝宗已倒向了主和派。六月,孝宗命湖北京西制置使虞允文放弃唐、邓二州,虞允文拒绝执行,被撤职降知平江府。七月,海、泗二州宋军撤戍。九月,孝宗命汤思退都督江淮军马,杨存中以副都督协助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汤思退。
汤思退与金人暗通声气,要求金军重兵迫和。十月,仆散忠义挥师南下,由于主和派主动撤防,金军轻而易举地突破宋军的两淮防线。十一月,楚州、濠州和滁州相继失守,长江防线再度告急。汤思退主张干脆放弃两淮,退守长江,尽快与金议和。
16.
这时,孝宗听到使金回朝的魏杞报告说金人议和要价贪得无厌,便激愤地表示:有以国毙,也不屈从。抗金呼声再度高涨,太学生甚至准备伏阙进谏。十一月,孝宗罢免汤思退,将其流贬至永州居住。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二人上疏请斩汤思退及其同党王之望等,汤思退在流贬途中闻讯,忧悸而死。
在罢免汤思退的同时,孝宗重新召回因病出朝的陈康伯,任命他为左相,以主持大局。但宋朝在军事较量上一再处于劣势,孝宗不得不再派王抃为使者赴仆散忠义的大营,表示愿意议和以换取金人的退兵。金朝见以战迫和的目的基本达到,便停止进攻,重开和议。
经过使节尊俎折冲,岁末终于达成和议条款:宋金世为叔侄之国;“岁贡”改为“岁币”,银绢各为二十;南宋放弃所占的海、泗、唐、邓、商、秦六州,双方疆界恢复绍兴和议时原状;双方交换战俘,但叛逃者不在其内。
17.
与绍兴和议相比,南宋在隆兴和议中的地位有所改善。南宋皇帝不再向金朝称臣,岁贡改为岁币,数量也比绍兴和议减少五万,这是金朝最大的让步;而南宋在采石之战以后收复的海、泗等六州悉数还金,则是宋朝最大的让步。
双方的让步都是基于一种新的政治地缘的实力平衡,金朝的让步是出于内部的不够稳定,宋朝的让步是出于兵戍相见时太不争气。离开这点,空谈和议是否平等或屈辱是意义不大的。
隆兴和议以后,宋金关系再度恢复正常,直到开禧北伐才试图再次打破这种地缘政治的均衡状态。而隆兴和议到开禧北伐的四十年间,对宋金双方来说,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
18.
——宋朝出了个疯皇帝——
淳熙十四年,赵构病死于临安行在的德寿宫,时年八十一岁,谥号圣神武文宪孝皇帝,庙号高宗。
对高宗的死,孝宗表现出深切的悲痛。他一反君主守丧以日代月的旧规,坚持要为太上皇守三年之丧。其中虽有尽孝报恩的因素,但最关键的还是他对朝政已深感倦劳,不再是隆兴初政时那个雄心勃勃的宋孝宗。
淳熙十六年初,孝宗正式禅位给皇太子,此即宋光宗。据推测,孝宗之所以决意退位,另一原因是这年正月,金世宗的皇太孙完颜璟即位,此即金章宗,而按隆兴和议,年过花甲的孝宗得尊年仅二十来岁的金章宗为叔叔,这是其强烈自尊心所无法接受的。禅位以后,孝宗改高宗原先退居的德寿宫为重华宫,移住其中也当起了太上皇。他期望光宗也像自己对待高宗那样,让他颐养天年。
19.
光宗即位次年,改元绍熙。光宗皇后李凤娘,是庆远军节度使李道的次女,由术士皇甫坦推荐给高宗,聘为恭王妃。她生性嫉妒,容不得太子身边宫女的增多,一再到高宗与孝宗夫妇面前告状,孝宗让她学点后妃之德,同时警告她:“如果只管与太子争吵,宁可废掉你!”
光宗即位,李氏成为皇后,越发肆无忌惮。面对强悍的妻子,懦弱的光宗既惧怕又无可奈何。一次,光宗洗手时见端着盥盆的宫女双手细白,不禁喜形于色,不料被皇后看在眼里。几天后,李后派人送来一具食盒,光宗打开一看,里面装的竟是上次那个端盆宫女的双手。一个宫女因为手白而得到光宗的好感,李氏尚且不能容忍,对于光宗宠爱的妃嫔,她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
20.
光宗还在东宫时,高宗曾赐给他一名侍姬黄氏,光宗即位后晋为贵妃,备受光宗宠爱,李后自然妒火中烧,她趁光宗出宫祭祀之机,虐杀黄贵妃,然后派人告诉光宗说黄贵妃“暴死”。光宗明知是皇后下的毒手,但惊骇伤心之余,除了哭泣,连质问皇后的勇气都没有。事也凑巧,次晨祭天时猝不及防发生了火灾,转瞬间大雨冰雹劈头而下,虽没把光宗烧死,但突如其来的打击与祭祀时发生的一连串怪事,直接导致光宗的精神彻底崩溃。
光宗即位后病情时好时坏,无法正常处理朝政,这正中皇后李氏下怀。从绍熙三年开始,“政事多决于后”,大权旁落李氏之手。然而,她既无兴趣也无能力参决朝廷大政,权力对她而言,最大的作用就是可以为娘家大捞好处。她封娘家三代为王,侄子孝友、孝纯官拜节度使,一次归谒家庙就推恩亲属26人,172人授为使臣,下至李家门客,都奏补得官。
21.
李氏外戚恩荫之滥,是南宋建立以来所没有的。李氏家庙也明目张胆地僭越规制,守护的卫兵居然比太庙还多。李后一门获得的显赫权势、巨额财富,无疑都是其患病的丈夫光宗所赐。
李氏只生有嘉王赵扩一人,立为太子,本是顺理成章之事,但却受到孝宗的阻挠。可能是因为嘉王天性懦弱,孝宗认为其不适宜继承皇位,相比之下,魏王赵恺的儿子嘉国公赵抦生性聪慧,深得孝宗喜爱。当初光宗取代了二哥赵恺,成为太子,如今孝宗却宠爱赵恺之子,不同意将嘉王立为储君,无形中加深了光宗心中对孝宗本就存在的猜忌,让光宗时时感到恐惧和不安。在他看来,父亲似乎不仅对嘉王的太子地位,甚至对自己的皇位,都是潜在的巨大威胁。
22.
在别有用心的李后和宦官们不断离间挑拨下,这种恐惧感逐渐成为光宗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其心理和精神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导致了无端猜疑和极度偏执的症状。他视重华宫为畏途,不再定期前去问安,尽可能躲避着孝宗。天子孝行有亏,臣子劝谏责无旁贷,而臣僚们的这些言行更激起光宗的固执与疑惧,终于引发历时数年的过宫风波。
光宗病情不断加重,皇后李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生性妒悍,又有着强烈的权力欲。一方面,她独霸后宫,不允许任何女人与她争宠,光宗对此只能忍气吞声,抑郁不乐;另一方面,她视孝宗夫妇为她皇后地位的最大威胁,想方设法离间孝宗、光宗父子,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光宗的病态心理。
23.
绍熙五年初,太上皇逐渐病重,起居舍人彭龟年叩首苦谏光宗过宫探病,额血渍红了龙墀,也没能感动他。从太上皇犯病到去世,他竟一次都没有去过北内。个别得睹“天颜”的大臣不敢说出病相,无缘得睹“天颜”的士庶军民却被光宗的所作所为所激怒。叶适建议宰相留正将光宗病状遍告群臣,免得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轻议君父”,留正却以为人臣决没有对皇帝说“你有病”的道理,听任人心浮动,政局动荡。
六月,孝宗去世,光宗拒绝出面主丧。大丧无主,是前所未有的人伦大变,社会变乱随时可能发生。宰相留正与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率群臣拉住光宗泣谏,衣裾为裂也无济于事,朝臣们都手足无措。
24.
高宗皇后吴氏自高宗死后一直与太上皇孝宗同住重华宫,她年已八十岁,却能处变不惊,命宰执赴重华宫发丧。留正、赵汝愚请她以太皇太后之尊垂帘听政,她不愿背上女主干政的恶名,只同意代行祭奠礼,并向外宣布“皇帝有疾,可在南内服丧”,以保住朝廷体面,平息朝野义愤。
这种局面不能长久继续,留正便奏请立储,岂料光宗在这一问题上也出尔反尔,先是斥责留正“储位一建就会取代我”;继而御批“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却又不明确指示究竟立储还是禅位,让宰执无所适从。留正迷信自己流年不利,在一次上殿时扭伤了脚脖子,误以为不祥之兆,光宗给他的御批中又有语意含混的责备语,他便撇下了棘手的政局,乘上肩舆逃遁出城了。
25.
这一消息更令朝臣都民惊骇惶恐。工部尚书赵彦逾以山陵使来向赵汝愚辞行,建议他当机立断,根据“念欲退闲”的御笔,出来主持大计,成就上天赋予的一段事业。赵汝愚被说得忘情,脱口道:“是啊,几天前梦见孝宗授我汤鼎,背负白龙升天。”二赵计议已定,赵彦逾去做殿帅郭杲的工作,以取得宫禁卫队的支持,这是专制君主制下宫廷政变的关键。赵汝愚让知閤门事韩侂胄去打通太皇太后吴氏这一关,没有她的首肯就名不正言不顺,韩侂胄是名臣韩琦的曾孙,其母与吴氏是亲姊妹,其妻是吴氏的侄女。不过,韩侂胄平时也不能随便见吴氏,他托人传语,吴氏传语赵汝愚“要耐烦”。但局面不容一拖再拖,赵汝愚让他再去提议内禅。
26.
韩侂胄进退无路,走了原重华宫领班内侍关礼的路子。关礼声泪俱下地向吴氏哭诉局势的严重,吴氏终于传谕赵汝愚,决策内禅。
次日,是孝宗大丧除服的日子。嘉王赵扩由王府直讲彭龟年陪同,在军队护卫下来到北内。赵汝愚则先命殿帅郭杲率卫士赴大内请来传国玉玺,自己与其他执政率群臣也来到北内孝宗灵柩前,向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吴氏建议立储传位。
吴氏命赵汝愚宣布皇子嘉王即皇帝位,尊光宗为太上皇帝。嘉王听了,绕着殿柱逃避不止,连说“做不得”,吴氏大声喝令他站定,亲自取过黄袍给他穿上。
嘉王在韩侂胄、关礼的挟扶下侧坐在御座上,仍自言自语道:“我无罪。恐负不孝之名。”赵汝愚早率群臣跪拜了新君,他就是宋宁宗。次日,吴氏撤帘还政。在她的主持下,南宋王朝度过了一次皇位传承的危机。
27.
宋光宗此时对政权交接尚蒙在鼓里。当他知道后,长期拒绝接受宁宗的朝见,依然住在皇宫之中,不肯搬到为太上皇预备的寝宫里。他对于失去皇位的担心终于应验,病情因此又加重了。与他一同失势的李氏一反常态,对光宗不再像以前一样咄咄相逼,反而有同病相怜之心。她唯恐触动光宗脆弱的神经,常以杯中之物来宽解光宗心中的郁结,还反复叮嘱内侍、宫女,不要在光宗面前提起“太上皇”和“内禅”等敏感字眼。
庆元六年八月庚寅日(1200年9月16日),光宗患病,八月辛卯日(9月17日),光宗在寿康宫去世,享年五十四岁,后葬光宗于永崇陵。十一月丙寅日,上谥号宪仁圣哲慈孝皇帝,庙号光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