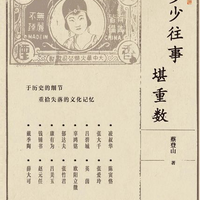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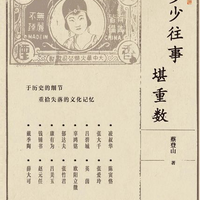
【民国事·往事堪重数】篇叁
冼玉清与陈寅恪
1. 在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提到陈寅恪人生最后岁月里的两位重要女性,一是跟了陈寅恪十三年的助手黄萱,一是同为广州岭南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的女教授冼玉清。
冼玉清生于一八九五年,小陈寅恪五岁。她原籍广东南海县,但出生于澳门。她十二岁入澳门灌根学塾(即子褒学校),跟从中国近代文化教育革新者的先驱陈子褒学习,并深受其影响。
冼玉清说:“我一生受他的影响最深,也立意救中国,也立意委身教育。自己又以为一有室家,则家庭儿女琐务,总不免分心。想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好教师,难免失良母贤妻之职;想做贤妻良母,就不免失人民教师之职,二者不可兼得。所以十六七岁我就决意独身不嫁。”尽管如此,年轻的她仍不乏追求者,听秦牧说当初有位相当有名的教授曾追求过她,但冼玉清曾赋诗笑谈其事,其中两句是“香饵自投鱼自远,笑他终日举竿忙”,话说得相当决绝。
2. 冼玉清二十一岁时,由其父送她到香港斯蒂芬斯女校(St. Stephen’s College for Women)读英文。两年后转入广州岭南大学附中读书,又两年毕业,升入岭南大学文学院,一九二四年毕业。次年起任教于岭南大学,直至一九五五年退休。
冼玉清除了是位著名学者之外,还是位杰出的女诗人、女画家。一九二九年在翰林学士江孔殷(霞公)、岭南大学国文系主任杨寿昌的引荐下拜见岭南诗宗黄节(晦闻),她回答黄氏作诗之法,颇为黄氏所赞许,更常读其《蒹葭楼诗集》,以学习诗法。
同年十月冼玉清复见黄晦闻于北京大羊宜宾胡同之“蒹葭楼”,并以其所作《碧琅玕馆诗集》呈览,黄氏批曰:“陈想未除,陈言未去,独喜其真”,其意要其“务去陈言”,追求“真切”。是月,冼玉清也拜谒诗人郑孝胥,并呈上诗稿,郑氏题曰:“古体时有隽笔胜于近体。”
3. 一九三七年夏,冼玉清以《碧琅玕馆诗集》呈给当时客居故都北平的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散原老人给予其很高的评价,称其“澹dàn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饰,自饶机趣,足以推见素抱矣”。并亲笔为冼玉清的书斋“碧琅玕馆”题写一匾。
不久,北平沦陷,陈三立日夜忧愤,拒药治病,后竟绝食五日,于同年九月十四日以死殉国。
一九四一年陈寅恪受香港大学中文系系主任许地山之邀,任职客座教授,年底日军占领香港,当时港大停课,陈寅恪生活极其困苦,正如他诗中所云:“乞米至今余断帖,埋名从古是奇才。劫灰满眼看愁绝,坐守寒灰更可哀。”当时客寓香港的冼玉清,托人给陈寅恪送去四十元港币,虽然陈寅恪没有接受,但雪中送炭之谊,铭感五内,无时忘怀。
4. 当一九六五年冼玉清逝世后,陈寅恪悲痛地写下一首挽诗。诗云:“香江烽火犹忆新,患难朋交廿五春(太平洋战起与君同旅居香港,承以港币四十元相赠,虽谢未受,然甚感高谊也)。此后年年思往事,碧琅玕馆吊诗人。”
一九四九年一月陈寅恪受陈序经校长之聘,来岭南大学任教,在北门码头上迎接陈寅恪一家的队伍中就有冼玉清的身影。同年九月冼玉清出版《流离百咏》诗集,并赠之陈寅恪。陈氏为题曰:“大作不独文字优美,且为最佳之史料。他日有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者,必有所资可无疑也。”一向“以诗证史”的陈寅恪,无疑地视冼玉清的诗作有“诗史”的另一种含义。
一九五〇年一月,陈寅恪夫妇与冼玉清结伴郊游,即游览清代名胜漱珠岗纯阳观,该地距离岭南大学仅四里,是当时许多诗人咏梅之处。
5. 陈寅恪写有《己丑仲冬纯阳探梅柬冼玉清教授》诗云:
我来只及见残梅,叹息今年特早开。
花事已随浮世改,苔根犹是旧时栽。
名山讲席无儒士,胜地仙家有劫灰。
游览总嫌天宇窄,更揩病眼上高台。
冼玉清以《漱珠岗探梅次陈寅恪韵(己丑仲冬)》和之:
骚怀惘惘对寒梅,劫罅xià凭谁讯落开。
铁干肯因春气暖,孤根犹倚岭云栽。
苔碑有字留残篆,药灶无烟剩冷灰。
谁信两周花甲后,有人思古又登台。
6. 一九五二年二月陈寅恪有《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三绝句,其一首云:
流辈争推续史功,文章羞与俗雷同。
若将女学方禅学,此是曹溪岭外宗。
冼玉清治学严谨,其研究侧重史学,又以考据、艺文、人物为主,毕生致力于岭南文化历史人物的发掘与系统研究,开一代之风气。陈寅恪以曹溪六祖慧能南派禅宗作喻,给予极高的评价。第二首云:
国魂消沉史亦亡,简编桀犬恣雌黄。
著书纵具阳秋笔,那有名山泪万行。
此诗陈寅恪用了他最擅用的“今典”,陆键东就指出:“其时,新编的中国历史‘简编’一类的书籍在文化界大行其道,并成一统天下之势。陈寅恪连用‘桀犬吠尧’‘信口雌黄’两典贬之,直见电闪雷鸣之色。”陈寅恪痛骂了当时修史的“应时”之作,也同时肯定了冼玉清的著作自有见地,“文章羞与俗雷同”。
7. 一九五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正逢旧历正月初一,陈寅恪赠予冼玉清一副由他撰写、唐筼yún手书的春联云:
春风桃李红争放,仙馆琅玕碧换新。
冼玉清何其有幸得到陈氏父子两代人先后题匾及写联。
一九六四年冼玉清到香港治病,留港约十个月,当时好事者却谣言满天飞,说她“逾期不归”,必定已经“逃港”了。殊不知冼玉清在香港立下遗嘱,将自己多年持有的香港股票全数捐给广东有关医院。同年十月她带着十万捐款返回广州,陈寅恪写了《病中喜闻玉清教授归国就医口占二绝赠之》,其一云:
海外东坡死复生,任他蜚语满羊城。
碧琅玕馆春长好,笑劝麻姑酒一觥。
给予冼玉清“同情的了解”,并褒扬她的一身正气。
8. 一九六五年十月二日冼玉清病逝广州,幸运的是她没有遇到“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而反观陈寅恪却在四年后,在目盲足膑之下,被红卫兵活活整死。一代史学大师晚年“涕泣对牛衣,卌xì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令人不胜唏嘘!
冼玉清宁守孤寂,不谈婚嫁,兀兀穷年,专心致志做着补史证史的工作,这和陈寅恪的研究何其相似,他们在剧变的时代中找到了最后的精神寄托,虽然这段患难之交只经短短的四分之一世纪,但却带给两人无限的暖意!

头白相逢亦惘然
9. 施蛰存先生有首诗,谈到一段如烟往事,四十二年后两位男女主角再度相逢,虽已是头发斑白,但仍是情不能自已。诗云:
儿女赓gēng词旧有缘,至今橐tuó笔藉余妍。
碧城长恨蓬山隔,头白相逢亦惘然。
一九六四年间施蛰存在读了陈小翠的《翠楼吟草》后写了十首绝句,又殿以赠陈小翠的书怀二绝,这是其中的一首。
话说一九六四年元月,当施蛰存从好友郑逸梅处得知了陈小翠的住址之后,即于同月二十日到陈小翠家中登门拜访,施蛰存在《闲寂日记》中写道:“访陈小翠于其上海新村寓所,适吴青霞亦在,因得并识之。坐谈片刻即出,陈以吟草三册为赠。”三天后的日记又云:“读《翠楼吟草》,竟得十绝句,又书怀二绝,合十二绝句,待写好后寄赠陈小翠。此十二诗甚自赏,谓不让钱牧斋赠王玉映十绝句也。”可见这诗还是他的得意之作,因为它里面还蕴藏了一段感人的故事。
10. 后来施蛰存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北山谈艺录》内中有一篇《交芦归梦图记》,谈到他与陈小翠这一段“并不如烟”的往事,云:“余少时尝与吾杭诗人陈媛小翠有赓咏联吟之雅,相知而未相见也,逾四十年,岁甲辰(1964),人日(农历正月初七)大雪,始得登元龙之楼,披道韫之帷,晤言一室。”这也就是他诗中所说“儿女赓词旧有缘”一事。其实早在一九八五年施蛰存就编有《翠楼诗梦录》,在集子中施蛰存述及这段往事,只可惜这集子一直未出版,故甚少人知。
施蛰存在年少时曾以“施青萍”或“青萍”的笔名,在所谓“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中发表文章,据黄转陶《卡党小传》文中说施蛰存曾译《生育女子须知》载于浙江民报《妇女周刊》中,另外还有小说《寂寞的街》刊登于《星期》杂志、小说《伯叔之间》刊登于《半月》杂志、小说《红禅记》刊登于《兰友》杂志,除此而外,他也写过不少旧诗词。他说施蛰存“撰稿好用钢笔,字迹细匀,不稍参差,墨水喜紫罗兰色。有瘦鹃风也”。
11. 一九二一年九月,周瘦鹃在上海创办《半月》杂志(共出4卷96期,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停刊),曾邀请当时以月份牌美人画而名噪一时的谢之光绘制每期的封面。谢之光所绘仕女图,其画笔法采中西之长,别具一格。当年施蛰存被这些封面所吸引,于是从第一期至第十五期,逐一以词题之,十五帧封面用十五个词牌,如《一斛珠》《蝶恋花》《行香子》《醉花阴》《巫山一段云》《喝火令》《极相思》《忆萝月》《好女儿》《步蟾宫》《锦帐春》《罗敷媚》《减字木兰花》《醉太平》和《步虚调》填词而咏之。
施蛰存说这十五阕词寄给周瘦鹃后,却一直杳无消息。其实周瘦鹃在收到词稿后马上找到鸳鸯蝴蝶派作家陈蝶仙之女陈小翠,以《洞仙歌》《卖花声》《浣溪沙》《一搦花》《如梦令》《菩萨蛮》《鹧鸪天》等词牌和之,写了九阕词,分别配以第十六期至第二十四期之封面。这“珠联璧合”的二十四阕词,后来在一九二二年的第二卷第一号(即第二十五期)以《〈半月〉儿女词》刊出,当时施蛰存年仅十七岁,而陈小翠也近双十年华,称得上是青春“儿女词”。
12. 施蛰存有位表叔沈晓孙当时在陈蝶仙创办的“家庭工业社”中任职,而陈小翠也在该社中兼任配料员之职。沈晓孙也读过《〈半月〉儿女词》,觉得这对小儿女颇有“文字因缘”,遂向老板陈蝶仙提亲,期望促成施、陈两人的姻缘。陈蝶仙对施蛰存的才华颇为欣赏,但女儿更是他至为钟爱的,故提出要施蛰存亲自登门拜访,或许他想要进一步再考察施蛰存的人品和学识。沈晓孙于是带上陈小翠的照片回松江见过施蛰存的父母。施父随即到杭州的之江大学与施蛰存商说小翠之事。
可惜施蛰存听罢此事,即以“自愧寒素,何敢仰托高门”为由,婉谢了这门婚事。原本一对“绝配”的才子、才女,就此错过了一段人世姻缘。
13. 郑逸梅谈及小翠的婚姻时说,最初南汇顾佛影追求她,佛影诗神似渔洋,和小翠很合得来,可是佛影一介书生,门第上是有差异的,终未能成佳偶。结果由父母之命,小翠嫁给了在辛亥革命时任浙江都督的汤寿潜的孙子汤彦耆qí。怎奈婚后两人意趣不相投,没多久,夫妇分食,后竟分居,但并没有离婚。
汤彦耆于鼎革之际渡海去台,陈小翠在一九五四年写的《咏汤氏园白藤花》一律,有“东风吹冷黄縢酒,翠羽明珠漫寂寥”之句,用陆游赠其前妻唐琬《钗头凤》词中语,言破镜已难重圆;此生只有寂寥独守了。
学者刘梦芙指出,陈小翠与汤彦耆分居时,正当盛年,才情艳发,诗画兼工;处杭州、上海金粉繁华之地,乃父事业兴旺,家境殷实,按今人观念,完全可以再觅一知音伴侣。但小翠却恪守“烈女不事二夫”的古训,忠于盟约,谢绝友人的追求,独立谋生,这正是贞介人格的表现。
14. 一九四六年秋,顾佛影返回上海,与小翠相见,重叙旧情。大概佛影流露了结为伉俪之意,但小翠却以诗明志:“梁鸿自有山中侣,珍重明珠莫再投”,她表明两人只能做好朋友,不能进一步发展关系。因此一九五五年顾佛影病重自知不起时,乃将小翠所写书、函、诗、词,亲付一炬,谓不愿小翠负此不好声名,这是对小翠的尊重和爱护。也因此在《翠楼吟草》只仅存几首她和顾氏唱和的诗词,其中有《南仙吕·寄答佛影学兄》一词,记述两人相识、相别又相逢,哀婉凄怨,令人不忍卒读。
历经四十二年,施蛰存、陈小翠两人才首次见面,当年曾是小儿女,如今都两鬓斑霜。陈小翠在后来为施蛰存写的《题画》一诗中,有句云:“少年才梦满东南,卅sà载沧桑驹过隙。”真是感慨万千。尤其在那“万马齐喑”的年代里,他们以诗词书画进行心灵的交流,感受到了那种人世间少有的真挚情义。只是好景不长,他们只再续了一段为时四年半左右的“文字因缘”。“文化大革命”祸起,小翠因兄陈定山在台湾、女汤翠雏在巴黎的亲属关系,饱受凌辱。
15. 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陈小翠甫及上海中国画院之门,即望见诸画师均罗列成行,为阶下囚,小翠反身逃回其寓,却被发觉,红小将追踵而来,小翠坚闭其门不纳,一时叩门如擂鼓,势将破门而入。小翠没有办法,乃引煤气自尽,终年六十七岁。
当有研究生问起陈小翠时,施蛰存爽直地说:“她是才女啊!能诗能画,才艺双全,可惜‘文革’时死得惨。”而二〇〇〇年五月,沈建中为施蛰存编《云间语小录》时,用心良苦,将陈小翠的一幅“落叶荒村急”作为封面,并故意问施老:“把您二人的名字排在一起,有何感想?”施蛰存说:“她要是还活着,不得骂死我啊!”脸上却笑成一朵花……

吕碧城和英敛之的凶终隙末
16. 吕碧城是一位奇女子,她是中国第一位女编辑,她曾提倡女权运动,办过女学,先后任过教习及校长。她也是清末著名的女词人,当时“文坛名宿”如樊樊山、易实甫等人对她的诗词甚为推崇,认为可以媲美易安居士(李清照)。袁氏当国时,她被聘为总统咨议,常出入新华宫;洪宪帝制时,她退而投身商界,与西商逐利于沪上,因深谙陶朱之术,年纪轻轻就拥有数不尽的财富,令人艳羡。
吕碧城姐妹四人都工诗文,有“旌德一门四才女”之称。词曲家卢冀野就曾赞之云:“旌德吕氏三姊妹(案:其幼妹早逝,故卢氏只言三姊妹),在中国妇女界总算是罕见的人物。碧城久居海外,死在异域,她这一生可谓不平凡的一生,才名洋溢,举世倾心,固然了不得。就是大姐惠如,办南京第一女子师范十几年,她的画,她的词,造诣深,境界高,和她那冰清玉洁,孤寂的身世是相称的。
17. 那自署‘齐州女布衣’的美荪,诗学鲍谢,终身西服,一嫁再嫁都是洋夫婿,侨寓青岛几十年,一手草书,不独工力厚,气魄之大直不类闺人手笔。
她只和遗老们有往还。她的生活与文学艺术极不调和,此其所以成为吕美荪的作风。然而两位姐姐终竟要让碧城一头地。”而在当时曾流传:“二十世纪头一二十年间,中国文坛、女界以至整个社交界,曾有过‘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的一大景观。”
尽管生于官宦之家,但吕碧城的少女时代却是甚为不幸的。学者秦燕春就说过吕碧城的一生,“不仅落难太早、成名太早、成功太早、富贵太早,且在智慧层面‘开化过早’了”。
18. 吕碧城的成名,无疑地要归功于《大公报》的创办人英敛之。英敛之对吕碧城的才华大为赏识,在她落难之际聘之为《大公报》编辑,这在当时无疑是空前创举,吕碧城不仅是《大公报》第一位女编辑,也是中国第一位报纸的女编辑。那年她虚龄才二十岁。之后英敛之还撰文赞许吕碧城的振兴女权的思想,同时又刊载吕碧城的诗词,“由是京、津间闻名来访者接踵相接,与督署诸幕僚诗词唱和无虚日”,吕碧城一夕爆红。
后来吕碧城欲办女学,英敛之除在《大公报》上为之鼓吹,还介绍她与袁世凯的重要谋士梁士诒、直隶提学史傅增湘等人结识。可见正是英敛之的提携扬揄,为吕碧城打通了进入天津文化界、教育界的道路。在此后一段时间内,吕碧城也一直对英敛之心存感念,两人保持了较好的关系。但到了女学堂筹办期间,两人竟渐生龃龉,隔阂日深。至一九〇八年九月十三日,英敛之日记云两人从此绝交。吕碧城与英敛之何以凶终隙末?这是令众人深感不解的。
19. 其实英敛之对吕碧城虽以兄长自居,但心中却有一种无限思慕之情,他曾在日记上写了一首词云:
稽首慈云,洗心法水,乞发慈悲一声。秋水伊人,春风香草,悱恻风情惯写,但无限悃款意,总托诗篇泻…
当是为碧城而作的。日记又说:“怨艾颠倒,心猿意马”,可见他也为吕碧城而倾倒,只是他终究理胜于情。其时外间对两人已经颇有流言,英夫人也难免误会。英敛之日记云:“内人连日作字、观书,颇欲发奋力学。……内人犹未眠,因种种感情,颇悲痛,慰之良久始好。”显然他们夫妻的感情,已因吕碧城而有裂痕。而后吕碧城的长姊、二姊相继到来,英氏夫妇对其照拂有加,甚至超过吕碧城,以吕碧城不能服人的个性,这对她也不能不有所影响。(吕氏姊妹才华不相上下,但都个性极强,吕碧城后来和两个姐姐感情极糟,亲姐妹几乎变成仇人。)
20. 而吕碧城才学虽高却涉世未深,性格过于孤高。讲到学问、思想或道德,常对老辈陈腐之见,表示不佩服并口无遮拦地抨击,有时也难免涉及英敛之,这自然会引起英敛之的不满。严复对此曾写道:“外间谣诼,皆因此女过于孤高,不放一人在眼里之故。英敛之、傅润沅(傅增湘)所以毁谤之者,亦是因渠不甚佩服此二人也。”严复与吕碧城也是因英敛之的介绍得以相识,并成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
严复一九〇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在给甥女何纫兰的信中说:“碧城心高气傲,举所见男女,无一当其意者。”又说:“此人年纪虽小,见解却高,一切陈腐之论不啻唾之,又多裂纲毁常之说,因而受谤不少,……自秋瑾被害之后,亦为惊弓之鸟矣。现在极有怀谗畏讥之心,而英敛之又往往加以评骘zhì,此其交之所以不终也。”
21. 可见知吕碧城者莫过于严复,严复在女学思想上深受吕碧城之影响,而严复的西学思想对吕碧城的思想及人生都有颇大的启发。严复对当时吕碧城处世之艰辛,所处之境遇,总能给予理解和同情,并给予师长般的关心和爱护。
平心而论,吕碧城才学见解固在英敛之之上,但对一位于自己有过帮助提携之功的前辈,就算不甚佩服,若更多保持一点尊重,善始善终也并非没有可能。然而,过分的孤高、直率和敏感,使她没有选择在人际关系上更有弹性一些的处理方式。吕碧城的性格有些急躁,略富进攻性,有时得理不饶人;而英敛之也是一位情感极丰富,但也很容易冲动的人,他当初对吕碧城是好到无以复加,但到后来却坏到痛心疾首。两人凶终隙末,最后的绝交就不可避免了。

郁达夫:从“名士”到“烈士”
22. 浙江富阳是富春江畔的一个小城,富春江发源安徽,贯流全浙,江形曲折,风景常新,唐朝诗人吴融形容为“一川如画”。一八九六年,郁达夫出生于此,故居原本是一栋木质旧房,因为隔壁豆腐店锅炉爆炸而倒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重新盖好。一九一一年冬到一九一三年秋,郁达夫曾在故居的小书斋苦读将近两年的时光。小书斋实际上是间狭长的朝南斗室,就在故居西楼,屋内原有的旧桌子、旧竹椅、旧书箱,再加上郁达夫长媳陆费澄女士特意翻检出的一盏美孚灯和一盏油灯,找来郁达夫的孙子郁俊峰演出少年郁达夫,那酷似的样貌,映照出当年苦读的身影。
23. 而在堂屋和小院,我们回想——“下着黑色长裙,上穿红色绸质大襟服的赵家少女,扎一根长长的发辫,坐在堂屋的桌边上,练习毛笔字,桌上有一盏点亮的煤油灯。少年郁达夫屏息敛声,蹑手蹑脚地走到她的背后,一口气吹灭了桌上的那盏灯。月光如水浸满了小院,在院内的石榴树下,郁达夫伸出两只手,捏住赵家少女的手臂。两人相对无言,在月光中沉默着度过了那一刻春宵”,我们拍下了少年郁达夫在《水样的春愁》中的初恋身影。
郁达夫的小说受到日本“私小说”的影响极深,那种深刻的自我分析和喜欢采用独白式的手法,充满了性的苦闷、死的诱惑,不管是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都带有强烈的“自叙传”性质。
24. 学者赵园指出郁达夫的特殊魅力,不只在于“表现自我”,更在于他实践自己主张的那种“彻底性”,在于他的惊人的坦白。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一九二七年年初郁达夫在友人家中初见王映霞,即苦苦追求,他因此与原配夫人孙荃离异,同年六月与王映霞成亲。
一九二八年出版《日记九种》,赤裸裸地公开他们的恋情,甚至还有床笫之私。这与后来他应聘到福州担任福建省主席陈仪的公报室主任,与王映霞聚少离多,两人感情不睦,到怀疑王映霞移情别恋,与浙江教育厅长许绍棣有染,最后发表轰动一时的《毁家诗纪》一样,都难免把自己文学化、公开化,有如小说家“由自传式的表现走向所谓演技的追求”,他把自己当作一个角色去处理,尽管是确有其事,却不免失之于夸张。
25.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郁达夫应聘担任《星洲日报》主编,他远离祖国来到新加坡。在新加坡他扮演的已不是一个小说家的角色,他提携后进,培养写作人才,甚至成了一个改革社会、提倡文化的文化人。当我们翻阅其侄女郁风所编的《郁达夫海外文集》一书,读着那写于新加坡的两百余篇政论、杂文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万里投荒”、孤军奋斗、没有任何依靠的笔耕者,在编报之余还三天一篇社论,两天一篇杂文,凭着他的爱国主义激情和横溢的文学才华,下笔千言,写下如此感人的政治诗篇。他也从一个被视为“颓废派”的文人、名士,成为一个抗日的革命战士,他以生命为代价,谱写最后的英雄诗篇!
26. 一九四二年的二月四日,就在新加坡沦陷的前夕,郁达夫在当地文人的协助下,从新加坡的红灯码头乘小船向印度尼西亚方向逃亡。新加坡学者王润华说,郁达夫从新加坡水域附近一个叫卡里曼(Kariman)的小岛,然后再到司拉班藏(Selat Panjang)就上苏门答腊本岛了,之后继续向西一直逃到武吉丁宜(Boekit Tenggi),最后他是住在巴爷公务(Payakumbuh)和武吉丁宜之间的小镇,可惜他一去就没有再回来了……
在南洋协助胡愈之开展华侨文化活动和统战工作的王任叔(巴人)在《记郁达夫》一文中说:“他有时实在像个土豪劣绅,他知道怎样来制服那些野兽似的宪兵朋友,他装作很豪奢,为他们花钱、弄女人、喝酒,而他自己则伺候在一边,力争抑制去接近酒和女人,他想借金钱的力量,去建立他们间虚伪的友谊。”这些都是发生在郁达夫化名为“赵廉”,为日本宪兵当翻译时的事,他要“中国人要爱护中国人,不许自相争夺、打闹和诬告、陷害”。他同样也依仗日本人的权势,去遏止那些印度尼西亚人对中国人不利的行动。
27. 郁达夫和鲁迅,可说在新文学家中,是旧体诗写得最好的两位。他在苏门答腊期间,据说每日一诗,无时不在怀念故国。他殷切地希望能回到祖国参加抗战,“镇日临流怀祖逖,中宵舞剑学专诸”;他多少回“草檄书生梦里功”,期待河山早日重光。一九四五年春,他在苏门答腊还写有“十年孤屿罗浮梦,每到春来辄忆家”的诗句,没想到同年秋他就被日本宪兵杀害了。
一九四五年的八月二十九日那天晚上,日本宪兵押走郁达夫,而且将他勒毙,至今我们找不到他埋骨之所。日本研究郁达夫的学者铃木正夫早在一九七二年前就开始调查郁达夫被害真相,他原先想对“凶手是日本宪兵”这一成说提出反证,但最后他却获得杀害郁达夫的班长下命令的纸片复印件,也找到这位班长,听他亲口说出真相。
28. 在富春江边的鹳山上有座“双烈亭”,是纪念郁华(字曼陀,画家郁风之父)、郁达夫兄弟的。郁华曾官费留学日本,一九三二年任上海公共租界内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上海沦陷后,他对进步爱国人士多方维护,严惩民族败类,一九三九年被日伪特务暗杀于上海常熟路家门口。同样地,郁达夫也死于日本宪兵之手,两人都在抗日战争中付出宝贵的生命。由一位新文学作家到抗战烈士,瞬间,笔者的脑海中浮现出各种不同的郁达夫身影,互相交错重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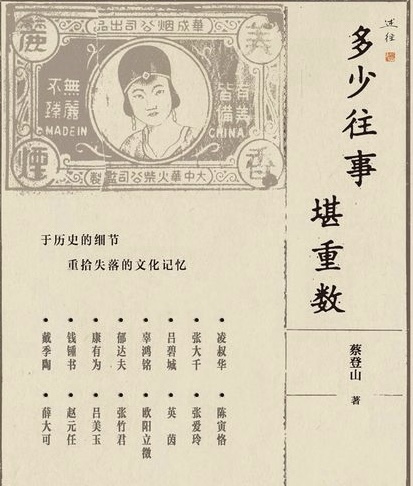
【民国事·往事堪重数】 系列1---6文本号:
①400021 ②520721 ③214309
④461871 ⑤870301 ⑥844707
民国时期《作家才子诗意生活】系列1---8文本号
①710141 ②824179 ③208301
④652791 ⑤464275 ⑥897745
⑦108175 ⑧187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