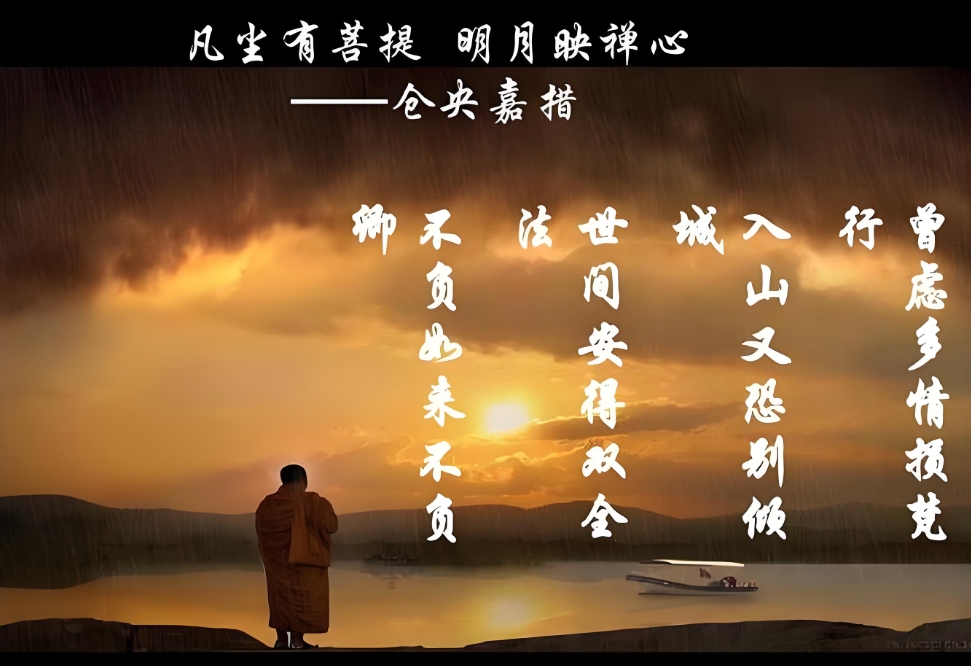仓央嘉措传8
1.四.活佛与荡子在昼夜交替
~写成的黑色字迹,已被水和雨滴消灭;
~未曾写出的心迹,虽要拭去也无从。
——仓央嘉措情歌
八廓街的酒肆里,所谓六世达赖创作的情歌迅速被前来参加祈愿法会的人们传唱到了所有讲藏语的地方。尽管有几分出于猎奇的心理,有几分源于对圣者的崇敬,但美丽的诗歌本身便有着比草原更强大的生命力,有着比雪域上的冷风更迅捷的脚步,有着比少男少女的初恋更动人心魄的魅惑。
但是,这妙音天女的欢歌此时却成了桑结嘉措最大的烦恼,因为爱之者相信这位年轻而俊美的六世达赖以密术的力量调伏了最为不驯的妙音天女,别有用心者则汲汲于散布流言飞语,说什么从仓央嘉措的表现来看,显然在十五岁之前一直都在过着自由的世俗生活,所谓一早就被选立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并在一个秘不示人的地方接受严格的佛教训练的说法,看来只不过是桑结嘉措临时编造出来的罢了。
2.桑结嘉措此时不知道有没有生出一丝悔意,二十年前匿五世达赖之丧不发,为自己换来了足足二十年的大权独揽,为蒙人治下的藏地争取了二十年的喘息之机,运道终于要逆转了么,仓央嘉措这个不更事的孩子呀,到底还会给自己、给全藏,惹来多大的麻烦!
八廓街的酒肆里,那日被拉藏汗的侍从们唱出的情歌,也不知有多少是真,多少是假,但桑结嘉措知道,这里边纵然有假,也是空穴来风、事出有因。仓央嘉措从扎什伦布寺回来之后,虽然不再提起还俗的事情,但越发地放任起自己的心性。纵然摆脱不了一身的镣铐,他也要夜夜舞蹈;纵然被禁闭在密不透风的囚室,他也要日日狂歌。而面对桑结嘉措的规劝,他干脆摆出了绳索和刀子,声言若在这重重枷锁下也不能获得一点自由,自己宁愿自缢,宁愿自刎。
桑结嘉措终于无话可说。他就是不能理解,像这般由黄金铸成的镣铐,由宝石垒砌的牢房,明明是这世上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呀。
3.自由能管什么用?是自由地挨饿,还是自由地受冻?是自由地流落街头,还是自由地过着喂马劈柴的日子?
想要走进仓央嘉措,复习他的爱情是必经之路。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他所爱过的那些女人,从名字到家族背景,早已埋入那片遥远的土地,统统没有确切的记载。关于她们,资料芜杂,传说与事实长时间交缠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难辨真伪。整理、辨别、筛选这些故事,需要耗费不少的时间与精力,但我们始终耐心,如同一个执念于真相的侦探,在仓央嘉措的诗与诗之间、资料与资料之间,寻找某种关联。与侦探不同的是,我们执念的,是那些已黄得发脆的古老爱情和这些爱情中所栖居的仓央嘉措的精魂。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女人也渐渐从故纸堆里款款走出来,活色生香。
~夜里去会情人,
~黎明天降大雪。
~还有什么秘密,
~雪地足印明白。
在许多年以后,她看到雪地上的足印,还是会心跳加速,一如十三年前还是十五年前的某个冬天或初春。
4.那个裹着单薄僧衣、在铺天盖地的雪和夜色中来去匆匆的年轻人,像一支针剂注入她的血管,在她滚烫的血液里升起一个细弱的泡后,不发出任何声响,便消失不见了。
他的出现是一个意外。每每想到和他相遇的前因后果,她都会吓出一身冷汗,感觉无限惊心动魄——任何一个差错都可能使她从来不曾遇见过他——如果那天出门前她没有换了一件又一件的衣裳,将晌午都挨过;如果邻居家的黄狗没有蹲在巷口,并叼走了她匆忙间掉落的耳环;如果她为人精明,记得上次走过的路;如果她从出生以来就讨厌花;如果那棵树上长出的花骨朵模样普普通通;如果她踩的是更结实的那根枝丫,那么,她抬起眼来,看到的又会是谁?是否有着和他一样温柔的态度,而这温柔的态度还长着一副让人过目难忘的面孔?是否能让那段日子一入夜就静得可怕,却怂恿心脏在她身体里喧腾、鼓噪,吵得她坐立不安?是否能够在见面之后,将夜变得更沉静,静得再也听不到除他以外的声音?
5.是否会踏雪而来,又踏雪而去,在雪地上留下一串纷杂的脚印与一场秘而不宣的爱情,任由整个布达拉宫去猜测?是否能将“再见”说得与“思念”一样动听,像一首音节明快的短诗?是否能让她甚至已忘记他的身份,却不会忘记他的眼睛?是否能让她只记得如何开始,却不记得如何结束?
夜又深了。日子还长得很,她可以慢慢过,青稞酒一坛接一坛,怎么也喝不完,日子后面还排着长长的日子。那么漫长的岁月,也许还会有人不发出任何声响,便消失不见了;只是不会再有人,像一支针剂注入她的血管,在她滚烫的血液里升起一个细弱的泡。
~人们说我的话,
~我心中承认是对的。
~我少年琐碎的脚步,
~曾到女店东家里去过。
她一生皆张扬,穿的袍子,一定是大红色、深蓝色、湖青色,领口盘着金线钩成的花;选的首饰,一定是松石或琥珀做的,用料不计成本,造型夸张;爱的人,一定长着分明的五官,跨上马、佩上刀就敢即刻奔赴战场,唱起歌来声音能传到下一个山头。
6.到她的店里喝酒,头一个规矩便是说话不能拖泥带水,嫌她的酒不好,只管扯着嗓子喊出来,她立刻笑盈盈地迎上来,给你重新满上好酒,话若投了机还会爽爽快快地请你喝两盅;但若是如妇人般小声议论,叫她听见了,她会毫不客气撵你出门,才不管损失了多大的生意。当身形清瘦、眼神柔和的仓央嘉措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只是照例随意地问了句:“喝茶还是喝酒?”
故事发生得很快,他爱上了她喝酒的样子:一碗接一碗,面颊给酒烧得通红,眼角斜飘着,笑起来“咕咕咕”地,露出整整齐齐两排雪白的牙齿,被别的妇人当做宝贝的巴珠也被她随意地摆在这里,或那里。每每看到她喝酒的样子,他就感到一阵痛快。
没过多久,各色议论便开始在街头巷尾流窜。但她心头欢喜得很,她顶喜欢从众人嘴里听到关于他和她的种种。她喜欢和他连在一起,哪怕只是名字。她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隐藏她与仓央嘉措的故事,甚至,她想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7.于是,她采用了一个孩子气的方式,将自己的店漆成了代表仓央嘉措的颜色——黄色。
夜晚,月亮高高地挂在窗户的一角,细细碎碎的脚步声从巷子那头传过来,她探出头去,看情人瘦削的身影被月光拉得老长,毫不留情地投到冰冷的石板路上;看情人从那头走到这头,进到门里来。关上门,她笑着把白天听来的议论都告诉他,关于他俩的各式各样的揣测,或离奇或恶毒。他话不多,只是笑,有时笑得歇斯底里,眼泪都出来。
他总是将头埋在她的怀里,狠狠地,恨不得能嵌进去,再也不出来。有一次,她一边轻轻抚摸他的脖子,一边笑着说,我听人说,只有找不到家的小孩才会采取这样的睡姿。他唔了一声,仍旧埋着头,一动不动。那一晚,他在她怀里待的时间特别长。
还有一次,他话变得很多,往常他把头埋在她怀里时几乎是一言不发的。他向她认真打听流言的每一个版本,要求她细细复述,不放过任何一个细枝末节:
8.他们说看见你捧着一坛子酒就到我嘴边来,还用那条鲜黄色的巾子给我擦了嘴?还有人说我每晚攀着绳子爬上你的窗户,某天我还差一点失足跌了下去?卖胭脂的老妈妈说她听到过我对你唱了支露骨的情歌,到底是哪首歌?什么,什么,那个小和尚还告诉你我回宫后所受的责难,都是怎样的责难?……他听完一遍,要求重新听一遍,再一遍,再一遍。她也不厌其烦地讲了一遍,再一遍,再一遍,直到夜深了,灯油尽了,他一脸满足地沉沉睡去。她知道他为什么想听——对于一个布达拉宫的囚徒来说,这些传闻是一种反抗,尽管是那么微不足道,且于事无补。他的对手太狡猾,用来囚禁他的不是锁链,而是藏人仰望的桂冠,于是,可以囚禁得冠冕堂皇。得到“活佛”的称号,一辈子按神的方式活着,这只是让人羡慕的生活,不是让人幸福的生活。
9.在当时的人看来,仓央嘉措作为一个达赖,行径实在过于荒诞,接近于疯子。但小说家切斯特顿曾说过,所谓的疯子并不是失去理智的人,而是失去一切,只剩理智的人。她不会说切斯特顿说的话,但她正是如此理解他的。
~接受了她的爱,
~我却牺牲了佛缘。
~若毅然入山修行,
~又违背了她的心愿。
海拔三千六百五十八米,高一百一十米,布达拉宫几乎可以触摸到天堂。
点一炷香,双手合十,仓央嘉措在离天堂最近的地方默默祈祷,祈祷的内容是能离开这个直通天堂的地方。他祈祷的语调先是从容而悲伤,渐渐地,变得有些怨毒;他开始絮絮叨叨,讲那些人是如何为了与佛理完全相悖的目的将他推到佛前,禁锢他的身体,甚至强迫他的灵魂就范。
处在这样的高度,对人来说是很可怕的。——一个陌生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可怕?
即使身体保持安全,灵魂也很可能坠落。——那个声音继续从容不迫地把话讲完。
10.仓央嘉措惊异地打开门,看到与刚才听到的话风格截然不同的一张脸,她年纪很轻,一副不经世事的模样。
还未等仓央嘉措开口,她自顾自地解释,习惯从高处俯瞰世界的人,会自以为对万物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利,他们志得意满地想到,在通向目的地的路上,对他人造成的侮辱与损害也闪耀着神圣的光芒。布达拉宫的高度,可以送一些灵魂展翅飞翔,也可以折断一些灵魂的翅膀。
她只是一个在布达拉宫迷路的少女。她并没有把她听到的话看得太重,她自自然然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话说完了又自自然然地转身离开。她到很久以后才知道,仓央嘉措那段时间几乎找遍了拉萨的大街小巷。
她从不肯在夜里与仓央嘉措幽会。我讨厌夜晚,它不分青红皂白地替一切行为做掩护。她是这样说的。
而仓央嘉措小心翼翼地捕捉她的每个语气、眼神,将它们一个一个拼凑起来,组成一座刻着她的名字的秘密花园,然后终日徜徉其中,探寻里面每一株虎头兰、玫瑰、思竹、天竺葵、大丽花、格桑花、卓玛花与绿绒蒿。
11.他的口中并没有如外人所想象的那么多甜言蜜语,他说:我找你,其实是在找一个答案,我想知道,用灵魂去交换权力、财富、土地是合算的吗?
她撇撇嘴角,不屑一顾:合算,但是,你们有灵魂可以拿去交换吗?
知道为什么人们只给神佛塑像,却从来不给恶魔塑像吗?那是因为神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证明自己存在,如果没有佛像,你从人间找得出神的影子么?但恶魔不需要,它就潜伏在每个人的心中,唆使人们去争斗、妒忌、贪婪、淫乱、欺骗、背叛,无预任何证明。看看人们犯下的罪,你就会知道恶魔确实存在。她说。
你看,当从下向上仰望时,高大庄严的布达拉宫带着一股磅礴的力量倾泻进信徒的眼睛,强有力地闯入他们的心灵,使他们觉得,连布达拉宫顶上的云都比别处的云更为洁白可爱。但是,如果僧人们刻苦修炼只是为了成为西藏的统治者,拜倒在佛像面前,心里却在向权力磕头;如果僧人们口中念着长长的经文,却只对土地和金钱忠诚;
12.如果僧人们直至深夜也不阖眼、佛堂的灯燃至天明,却不是研习佛法,而是思考权术,那么,布达拉宫不过是有着圣洁外表的名利场,且比赌场、酒肆、妓院更为邪恶,因为它的路牌指向天堂,实际却将人引向地狱。不过,不要忘记了红山正努力将布达拉宫举向天空,所有的罪恶都被太阳照得一清二楚,无所遁形。她的语气愈加轻蔑,神态却一如既往地天真。
仓央嘉措喜欢她这样说话,即使她攻击的对象中包含了他。他甚至刻意记下她的每句话,在与他人交谈时故作不经意地说出一两句,随即是恶作剧式的漫长停顿,那神色简直就像在暗示对方:你们千方百计窝藏的秘密已经泄露了出去。看到对方错愕的表情,他的心头涌起一阵快意——他愿意同敌人一起在她毫不留情的审判中同归于尽。
~在那高高的东方山顶,
~升起一轮皎洁的月亮,
~玛吉阿米的脸庞,
~浮现在我心上。
13. 马车来来往往,街道上尘土飞扬。门口,几个卖土豆的孩子放下手中的篮子,土豆翻倒在地他们也顾不上看一眼,头挨头紧紧凑在一起,聚精会神地盯着手里的游戏,谁也不知道主人交代的生意在他们的脑袋里到底还剩下多少。隔壁,氆氇(pǔlu)店总让人错觉它空无一人,衣着朴素的店老板在氆氇汹涌的色彩中缩为一个灰白色的小点,只有当生意上门时他才会从一片斑斓中站起来,从一个小点舒展成拥有灿烂笑容的店老板,迎着姑娘们好奇的打量,殷勤介绍十样锦与十字花的区别。隔壁的隔壁,小木匠神气地拿着图纸摆来摆去,听人说,去年最后一天他烧掉了自己不满意的作品。街的斜对角,裹着头巾的老妇背靠着被阳光晒得发烫的墙,微眯着眼,利索地穿针引线,魔术般地,一个个瑰丽的图案从她枯干的掌纹和皴裂的皮肤中诞生——绣花巾子越积越多,将墙角淹没,从远处看起来就像一个奇异的梦:
14. 到底是房子开出了花,还是这一丛花长出了整栋房子?兜售藏香的姑娘有着不输男人的爽朗个性,而她又那么年轻、好看,街上的少年都爱围着她打转。就在刚才,一个长相清秀的年轻人偷偷跟她说了什么,她大笑起来,撒腿向另一条巷子跑去,大把大把的香被留在路边,继续散发雪莲、冰片、陈香、甘松的味道。老鳏夫打着响亮的饱嗝经过,他的眼睛已经浑浊,看不清手里拿的是一块石头还是一枚鸡蛋,但他固执地表示,某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看见失踪多年的儿子出现在这条街上。菜摊上的萝卜又干又小,老板娘爱惜地将每一个都擦拭干净后,便斜倚在门口面无表情地看人来人往。从她的轮廓你已读不出任何故事,但谁都知道,许多年前有人爱过她,用年轻而光滑的手爬过她的窗;她也爱过一个人,但那个人并不看她一眼,她为此哭过、闹过,甚至在半夜去敲他家的门,直到他突然死去。一只猫低着身子拐进一个门洞,不见了。此时,酒肆的门帘被掀开了。
15.到这里为止,都与往常一模一样,仓央嘉措心满意足地看着这一切。这是拉萨街头每一天都在重复的情节,也是他一生都不曾厌倦的戏码。
此时,酒肆的门帘被掀开了,熟悉的情节暗暗起了变化。该如何形容掀起帘子的人呢?她让你想到,她一定是迎着太阳出生的,将来也一定会迎着太阳死亡。她很安静,不笑,也不说话,说她神情忧郁也未尝不可,但很奇怪,你只消看她一眼,就能笃定她一生不曾坐在阴影里,也没有见过坟墓、蛀虫和谎言。她微微低头,灵巧地进到酒肆里边来,那些彩色的氆氇、撒了一地的香、陈旧的渴望和爱情便都成了她的背景。他还在琢磨她的表情,她已抱着酒坛转身离去。待他追出门去,世界又恢复到她出现前的样子。
接下来的日子充满了期待。下一个转角,站着的会是谁?那条在梦中出现的老巷,是不是暗示她就在它的尽头?街边身影佝偻的老人、手持羽毛扇子的妓女、拄着木杖的盲人,嘴里唠唠叨叨的内容,会不会有关于她的?
16.寡妇盛在桶里的蜜,她有没有搅动过?商人搞过鬼的砝码,她有没有发现背后肮脏的秘密?仓央嘉措并不刻意寻找,但他每踏出一步心里都带着一种隐约的希望。到后来,他也说不清他的希望究竟是什么,到底是希望尽快找到她,还是希望怀着找到她的希望却一直找不到,好使他对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新的希望。
第二次见面依然在酒肆里,这次掀帘子的人是仓央嘉措。他在酒肆里等了她一整天,傍晚,桑结嘉措派人接他回去,他突然就发了脾气,怒气冲冲地掀起帘子,正遇上她埋头往里走。
像是为了方便仓央嘉措认出她,她穿着和上次一样的衣衫、梳着和上次一样的发型、抱着和上次一样的酒坛,连表情都维持不变。而这一次的印象,并没有与上一次的印象重叠,而是扩展了上一个印象的内涵。与她擦身而过的瞬间,仓央嘉措觉得自己正与春天并肩。
他想走上前去跟她说点什么,但士兵不由分说地将他送上了回宫的马车。
17.嘈杂的声音让她回过头来,隔着门帘也能看见她清澈的眼眸中所含的责备,仓央嘉措脸红了,像一个出了丑的孩子急于掩饰自己的狼狈,低声呼喝士兵快走。马蹄声“嗒嗒嗒”,走了很远,他也没有回过头去看一眼。一路上他只觉得背脊烫得厉害。
过后的几天,他赌气似的决意不再到那家酒肆去。但没多久,他又记不起他赌气的理由来,恢复了每天去酒肆的习惯。那段时间,她每天下午都会来买酒,整个人散发着温暖和煦的气息。仓央嘉措却始终没有同她说一句话。渐渐地,她不再作为特别的情节存在,而是成为了他烂熟于心的街头故事的一部分,同样让他烂熟于心的,还有他每次看见她时卑微的心情。
故事结束在那年冬季。马车来来往往,街道上尘土飞扬,卖土豆的孩子依然将生意放在一旁,氆氇店老板依然缩为一个灰白色的小点,兜售藏香的姑娘依然笑得爽朗,酒肆的门帘突然被掀起,他的心脏急剧收缩,到这里为止,都与往常一模一样。只是,她并没有走进来。
18.仓央嘉措的爱情总让我想起电影《死亡诗社》中的一句台词:“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吸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以免当我生命终结我发现自己从没有活过。”我以为,爱情是仓央嘉措在他有限的权力范围内能找到的唯一的“丛林”。
第四章·生关死劫
拉萨的祈愿大会还像往年一样的热闹,还是有千千万万淳朴的藏民从遥远的家乡赶来,一步一叩首地绕着转经路祈祷着今生与来世的幸福,也为他们的政教领袖仓央嘉措、桑结嘉措和拉藏汗祈福。这些淳朴的百姓并不知道,那些高高在上、光彩四射的大人物们私下里也各有各的心计,在祈愿大会这祥和而欢快的气氛里,他们的明争暗斗即将进入白热化了。
有距离才能有仰望,而在大人物们的彼此之间,是不存在这种距离的。
到了祈愿大会预定的日子,空地上的大跳神仪式便一年一度地开始了。
激动的围观者们并不知道,仪式上的恶魔虽然迅速地以灭亡告终,而真实世界里更加惨烈的神魔之战才将将拉开了序幕。1703年的西藏,山风满楼。
19.
一.真相扑朔迷离
~佛言:人怀爱欲不见道者,譬如澄水,致手搅之,众人共临,无有睹其影者。人以爱欲交错,心中浊兴,故不见道。
——《四十二章经》
如果斗争是一场暴雨,那么谣言就是雨前那漫天的浓云。1703年的西藏,谣言四起。
达赖汗死后,拉藏汗弑兄自立,并与桑结嘉措交恶。——前文讲过这个说法,当时的很多藏人都相信这个说法,甚至今天的一些出版物仍然沿袭着这个说法,但事实上,这只是桑结嘉措在与拉藏汗交恶之后所散布出来的一则流言。拉藏汗的长兄要么是病死的,要么是被桑结嘉措秘密毒死的。让人们大跌眼镜的是,拉藏汗的继位原本是仓央嘉措促成的,而这只推手的背后自然就是桑结嘉措本人了。
桑结嘉措之所以中意于拉藏,是因为在达赖汗所有的儿子里,只有拉藏一直住在青海,不但对西藏的事务完全陌生,更与西藏的政教人物没有任何的交往,既然和硕特蒙古必须要选立一位汗王,对西藏最有利的当然是选立这样一位看上去不大可能干涉西藏事务的人物了。
20.至于拉藏汗竟会如此野心勃勃地要在西藏夺权,却是桑结嘉措始料未及的了。
围绕着仓央嘉措的流言自然更多。有人说仓央嘉措恋上了桑结嘉措的女儿,如火如荼的爱情一发而不可收拾,于是,就在1703年的某个夜晚,仓央嘉措带着六七名随从潜出了布达拉宫,到一里之外的招地与情人幽会,途中突然遭到十几名暴徒的袭击。暴徒们似乎是有意地避开了仓央嘉措本人,却对他的随从们痛下杀手,杀死了最受仓央嘉措宠信的塔尔占鼐(nài),塔尔占鼐的弟弟拉旺也受了重伤。
惊魂未定的仓央嘉措冲到了桑结嘉措的家里,面对面地质问后者,说:若无第巴大人的指示,谁敢做出如此大胆的事来!桑结嘉措当即作出了追查真凶的允诺,却迟迟不能交出人来。
当时正在拉萨的清朝使者荐良记述了这样的传闻:听说六世达赖与第巴的女儿犯了奸情,达赖的侍从拉旺也不干净,所以第巴桑结嘉措与五名亲信秘密商议,要把拉旺杀掉。
21.但在动手的过程中,桑结嘉措的亲信们误杀了拉旺的哥哥塔尔占鼐,拉旺虽被砍伤,却总算保住了性命。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督察此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算告破,捉住了桑结嘉措的那五名亲信,把他们交给了拉藏汗。桑结嘉措向拉藏汗苦苦求情,但拉藏汗终是不允,到底还是杀了他们。从此,桑结嘉措便与拉藏汗结下了深仇。
拉藏汗在给康熙皇帝递交的奏折里也提到过这件事情,只在一个细节上与荐良的记载不同:据拉藏汗说,仓央嘉措已经娶了桑结嘉措的女儿。
在这一扑朔迷离、真伪难辨的事件中,每个人的反应倒还是合乎逻辑的:仓央嘉措放荡不羁、我行我素,心里只有单纯的爱恨,根本不去想政治上的盘根错节,不惜把凶手交给拉藏汗处理;桑结嘉措工于心计,谋定而后动,一旦遇事,也只是委曲求全,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把脸皮彻底撕破;拉藏汗气势汹汹,只要是对桑结嘉措不利的事情,他一定会做,而且会毫不掩饰地去做。
22.这件事在拉萨闹得满城风雨,仓央嘉措、桑结嘉措和拉藏汗这三大领袖之间的矛盾终于公开化了,成为街谈巷议的焦点话题。有人说仓央嘉措使用一种神异的密术捉住了所有的行凶者,因此公开了与桑结嘉措的矛盾,而年轻活佛的密术修为之高,简直是莲花生大师再世;也有人说桑结嘉措坚持要拉藏汗释放自己的五名亲信,结果导致了一场小规模的武装冲突,拉藏汗借机废黜了桑结嘉措,西藏的大权被掌握在拉藏汗和仓央嘉措的手里……
无论如何,因着这件事的关系,仓央嘉措对桑结嘉措越发不满,却与拉藏汗亲近起来。据一位从拉萨返归青海的蒙古贝勒的话,桑结嘉措仍然掌握着第巴大权,并未被拉藏汗废黜,拉藏汗也没有废黜第巴的实力;至于仓央嘉措,行为举止一如凡人,常常和拉藏汗一起放鸟枪、射箭。
这位蒙古贝勒的话被清朝驻青海的使臣记录在案,上奏给康熙皇帝,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五世班禅写给康熙皇帝的文书里也说:仓央嘉措的行止一如凡人,完全不像是一位喇嘛。
23.更有甚者,从日喀则流传出了这样一个说法:仓央嘉措在扎什伦布寺要求还俗的时候,把自己的心意写成了一封书信交给五世班禅,信里不但以死相胁,还说了许多自毁神性的话来。大意是:自从我降生之后,人们相信我说的一些话足以证实我就是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但这些话其实都是我父母和我家乡的人说的,我自己对此一无所知。等我记事之后,也从没有过自己就是转世灵童的念头。是因为第巴出于某种原因找来五世达赖的信物让我认领,并交给我班禅所著的关于达赖活佛历代转世的经卷,我才走到了如今的一步,这只是合了第巴和各位的心思,却不合我的本意。你们说我是转世活佛,但我根本就不喜欢佛教经卷。我既不愿意占据达赖活佛之位,也不想骗人讲经受戒,所以对佛教的修行并不用心。我生性贪玩,虽然现在还无碍于戒律,但将来恐怕会酿成大过,所以我才瞒着第巴,希望能将先前所受的戒律在班禅面前退还。这虽然违拗了第巴和众人的意愿,但我的老师江央扎巴对此是很了解的……
24.这种种传闻不仅在拉萨引起了一片大哗,就连北京也为之大伤脑筋。青海使臣的奏折、西藏使臣的奏折、班禅活佛的文书、仓央嘉措写给班禅的信笺,当时摆在康熙帝案头的这些文件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蒙古堂档》、《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宫中档人名包》,一件件尘封的历史档案,在今天看来,仍然可以感受到三百年前那心与心的冲突、锁链与锁链的纠结、刀兵与刀兵的对峙。
尤其是仓央嘉措写给五世班禅的那封信,更是直接以当事人的身份说出了自己身上发生的所谓转世,不过是出自桑结嘉措的政治安排与父母、乡人的愚昧和虚荣。
政坛的高手们显然并不会认同这样一份感人的真诚,对他们而言,就算活佛是假,而既然已经弄假成真,就必须假戏真做下去,因为政治不计真伪,只计利害。这位任性的活佛呀,如果放任他的言行,黄教的威信会受到重大的损害,那些对黄教不满的人、政治投机分子,尤其是蒙古人,势必借机发难,局面将一发而不可收拾。
25.深明个中利害的桑结嘉措迅速作出了两项决定:一是在黄教内部统一思想,无论大家对这位六世达赖有怎样的不满,有怎样的疑惑,这个时候必须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因为死保仓央嘉措就等于死保黄教;二是必须以非常手段铲除政治对手——拉藏汗对西藏事务已经干涉得过多,又和仓央嘉措走得太近,眼看着就要把后者争取过去了。
政治斗争的一个常用手段就是对敌人进行分化瓦解,然后拉一派、打一派,拉藏汗用的正是这招,认准了达赖与第巴之间的裂痕,分化瓦解之,把仓央嘉措争取到了自己的这边,孤立了桑结嘉措。
仓央嘉措是最单纯的男人、最浪漫的诗人,也是最容易被利用的政治傀儡。这个时候,二十出头的仓央嘉措正觉得自己的人生总算舒了一口气,原本一天天都不得不生活在桑结嘉措的锁链下,生活在五世班禅的锁链下,生活在所有藏人目光的锁链下,一点点奢侈的自由在夜晚才能获得,
26.而如今,总算有一个善解人意的拉藏汗为自己打开锁链,在阳光下陪着自己射箭、打鸟枪,替自己惩治了桑结嘉措派来的刺客。他还称赞自己的诗歌,陪着自己在拉萨的酒肆里疯闹,甚至他也像一个大孩子那样恶作剧似的和自己商量出一些奇思妙计,为的是“整一整那个跋扈而刻板的第巴大人”。
仓央嘉措哪里知道,这些所谓的恶作剧真的让桑结嘉措大感头痛。康熙朝的档案记载,桑结嘉措曾经对一位熟稔的青海亲王的使者哀叹:“五世达赖在世的时候有过指示,一切事情都由我自专办理。可现在呢,这一代的达赖活佛和拉藏汗一起,什么事都不让我管,我想辞官也辞不了。”这位使者也说:“眼看着第巴的日子过得很难,六世达赖与拉藏汗与他不和,事情都不让他管。”
不知道桑结嘉措有没有懊悔过,当初正是自己选立了仓央嘉措作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本来是要他来作自己背后的一面旗帜,没想到自己却约束不住这个满心叛逆的大孩子,眼睁睁看着他作了自己政治对头手中一件刺向自己的利器。
27.但就算这样,自己还得尽最大的努力来保住仓央嘉措——没办法呀,这就是政治,仓央嘉措还要继续供着,但拉藏汗必须除掉。
桑结嘉措的本意是用政治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拉藏汗既然拉拢仓央嘉措来架空自己,自己不妨也使些手段来架空拉藏汗。于是,桑结嘉措面对着拉藏汗咄咄逼人的攻势,表面上不但不与之抗争,反而屈尊降贵,给拉藏汗送上“成吉思汗”这个伟大的尊号,但同时又让仓央嘉措坐察奇尔巴顿汗之床。
所谓察奇尔巴顿汗,就是转轮王的意思。在西藏的佛教传统里,世界以须弥山为中心,为四大部洲所环绕,当初莲花生与寂护所建的桑耶寺就是对这一世界构架的精心模拟。转轮王降生之后,依次征服四大部洲。征服一洲时称铁轮王,征服二洲时称铜轮王,征服三洲时称银轮王,征服四洲时称金轮王。菩萨在这样的王者家族里转世,以转轮王之身度化众生。
28.所以,从佛教初入藏地以来,那些伟大的圣王们,松赞干布、墀(chí)徳祖赞、墀松德赞、牟(móu)尼、墀德松赞、热巴坚,这些在本书的第一部里陆续介绍过的赞普们,他们都是菩萨的化身,也都是转轮王家族的重要成员,更是仓央嘉措的历代前身。
只是,随着佛教力量的不断巩固,菩萨便不仅化身于转轮王的家族,而是更多地化身为宗教大德。“三素尔”、阿底峡尊者、玛尔巴、都松钦巴、米拉热巴、噶玛拔希、宗喀(kā)巴,这些在本书第一部里陆续出现的佛教宗师们,他们都是菩萨的化身,也多是仓央嘉措的前世。
仓央嘉措如今被冠以转轮王的头衔,无疑是向世人强调着那个古老的传统:观音菩萨之于藏地,不仅是宗教之主,也是世俗之王。言下之意便是:另奉一位与六世达赖并立的汗王是不合传统的,藏民无论于宗教、于世俗,都只能服从于一位领袖,那就是仓央嘉措。
29.桑结嘉措这一计可谓一石二鸟,既借着抬高仓央嘉措来架空拉藏汗,又离间着正走得越来越近的仓央嘉措与拉藏汗的关系——毕竟一山不容二虎,仓央嘉措虽然并不是虎,但即便只在名义上,一个西藏又怎能容许转轮王与成吉思汗的共存呢?
但让桑结嘉措为之气结的是,仓央嘉措就连达赖活佛的身份都急于摆脱,自然更不把什么转轮王的称号当一回事了,反而是拉藏汗四处炫耀着成吉思汗的尊号,提醒人们时时把自己与那位伟大的蒙元帝国奠基人联系在一起。
于是,在劣势中跌得更低的桑结嘉措只能铤而走险了。
♥ ♥ ♥ 未完待续 ♥ ♥ ♥
本文仅作练习研读使用,如有侵权请练习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