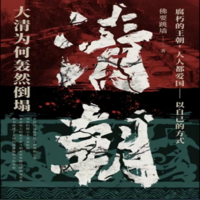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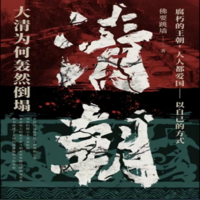
版权信息:
书名《大清为何轰然倒塌》 作者:佛要跳墙
仅供习读,如侵联删!
第三章 革命的萌芽——“书生造反”
1
血流给谁看?
庙堂和江湖这两条线基本还是遵循了几千年的老剧本。但从这里开始,我们要开始聊一伙书生。他们用血肉之躯,打破了“重复重复再重复”的循环,开始搞起了新玩法。这玩法,就是革命。
说起来,“革命”两个字恐怕是近代史课本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搞得好像我们是为了革命而革命一样,不过显然事实不是如此,起码第一代革命家肯定不是这个思路。严格来说,我们学的既是“中国革命史”,也是“中华自强史”。
革命是为了救国,但救国的最后手段才是革命,这一点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我们绝不是平白无故上来就要闹革命的。
2
满清眼中的中国革命早期三大“反贼团伙”——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追根溯源几乎都有过“改良”的念头。谭嗣同本来是个革命派,后来一听说有机会改良,马上就跑北京跟康有为混了;孙中山刚出道的时候,又是找关系又是发帖子,想跟李鸿章攀个关系,当面聊聊自强之路;章太炎第一次跑路就是因为支持“维新”……说到底,大家都曾是改良人。
所以,当我看到有些人说,“国家被列强入侵时,他们不去拥护朝廷抵御外敌,只会在后方捣乱。”拜托,造反是要掉脑袋的好不好,这群人个个都是“北清复交”的高材生,在体制内改良难道不好吗?要不是山穷水尽,谁想去搞革命。
3
很显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朝廷骨子里再烂,起码看起来还是个庞然大物,“天命”俨然还在。所以当时读书人的普遍想法还是改良,不会跳跃性地要去革(找)命(死)。
我们聊聊谭嗣同大家就明白了。顺便解释一下很多人关于“老谭为啥不跑路,宁愿赴死”的疑惑。总有人觉得他是白死的。
首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
谭嗣同是革命党!
谭嗣同是革命党!
谭嗣同是革命党!
谭老大是藏在维新派里的铁血革命党。人家很早就立志“驱除鞑虏”,在湖南、湖北各种混地下势力,传播《扬州十日记》之类的禁书,搞串联,拉着哥老会准备革命。
4
那为啥一个革命党要去跟康有为这帮改良派混呢?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对改良心存幻想。大家都是读书人,谁不知道中国乱了列强会趁火打劫?个个饱读诗书,造反的结局通常是啥谁心里没点数?
你想,连朱元璋这种当和(乞)尚(丐)的,造反前都还犹犹豫豫,要先去算一卦卜吉凶,何况人家谭嗣同呢。爹是湖广总督,他是超级官二代,当年京城的“四大公子”之一。只不过谭嗣同在中央核心圈层混了一圈,终于搞明白了,改良没戏。满清已经从根上烂了,洋务救不了、立宪救不了、皇帝自己也救不了。
5
戊戌变法100天,悲惨的不仅仅是六君子人头落地,更悲惨的是那个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革命之外,别无他法。
为啥非要“革命流血从我开始”,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误信了改良的革命党。
他的血是流给谁看的呢?戊戌变法的义士们坐着囚车为国赴死,北京的百姓们忙着往他们身上扔菜叶子。愚民们起码还得再扔20年,到1919年鲁迅写“人血馒头”的时候还在扔,这血不是流给他们看的。
清末百姓看革命党被砍头,跟看戏没两样
这血,是流给兄弟看的,是让革命同志知道,存在幻想是多么危险,妥协和退让只会灭亡。中国革命,从此和胡虏势不两立。火与血之外,别无他途。
谁是他的兄弟?毕永年和唐才常。
6
毕永年,湖南人,官宦世家,属于军区大院的中高层干部性质的。老毕的特长是跑江湖,官二代兼会党龙头那种。康有为计划政变软禁慈禧,就是想用他作为先锋。谭嗣同死后,毕永年逃亡日本,加入了孙文的兴中会,就是他帮着孙中山和湖南哥老会打通了天地线。
唐才常,湖南人,县府道三级考试第一,人称“小三元及第”,张之洞的高徒。正常来说,是要跟着张总出将入相的。不过唐总对自己的前途另有安排。1900年,他发动自立军起义,事败被杀,脑袋挂在城墙上。临刑前,赋诗“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
“故友”就是谭嗣同。
谭嗣同、毕永年、唐才常这仨才真是最牛的结拜兄弟。
谭老大的事情还没完。
7
唐才常的好友兼两湖书院的师弟,眼看着师兄身首异处,便放弃了对张之洞的幻想,创立了“华兴会”。之后和孙文共同创立“同盟会”,时人称他们俩为“孙黄”。这位师弟的名字叫黄兴,字克强,黄花岗起义的领头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他是中国革命的头等大英雄。
谭嗣同和唐才常当年在湖南创立了“长沙时务学堂”,有名爱徒名叫蔡艮寅。他跟随恩师参加自立军,兵败逃亡日本,考入“陆军士官学校”(就是蒋委员长号称自己读过的那个)。回国后辗转加入云南新军,辛亥年响应武昌起义,起事推翻云贵总督宣布独立。再之后袁大头称帝,他又出兵讨袁,人称“再造共和”。他当年逃亡时给自己改了名字,叫蔡锷。
8
因为袁大头坑了谭嗣同,所以谭老大的学生就反过来逼死他,这非常合理。
唐才常是岳麓书院的学生。他和谭嗣同创建了“南学会”,一周一次在岳麓开设讲座,其中有个热心的会员,名叫杨昌济。他自己成就不大,不过他有一个超龄入学的学生,热爱体育,脾气倔犟,这青年叫毛泽东。
薪火相传,革命不息。
谭嗣同11岁那年,谭家不幸染上白喉,母亲、姐姐相继病逝,他也昏迷三日不醒。家人以为无望,他却死里逃生。父亲悲伤之余,给他取字“复生”。
22年后,谭复生“我自横刀向天笑”,慷慨赴义。这次,他将复生为千万义士,在血与火中,烧光那个旧世界。
9
书生的觉醒
正是从谭嗣同开始,推翻大清的事业开始有了一条新的路径——用新思想武装了自己头脑的知识分子们,开始了真正的革命。不仅仅是革清王朝的命,更是要革这三千年封建王朝的命。
当然,光有理想是不够的,我们要不停地强调,热情不能取代方法论,满腔热血挡不过一颗子弹。这跟创业一个道理,CEO只知道天天逼人996,硬把员工孩子创业成留守儿童,却从来不花时间想想商业模式,那他通常连公司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区别在于,当市场钱多的时候,创始人搞个“狼性”人设,总有人愿意掏钱再给你机会。但放到革命年代,一个错误就能让你脑袋搬家,那就没得蹦跶了。
10
也跟创业一样,革命要解决:哪里拉风投(革命资金)、哪里找合伙人(拉到核心团队)、怎么组织公司(华兴会、同盟会……各种会的章程和制度)、基层员工怎么招(找谁地推)、怎么搞市场(理念如何推广,报纸怎么宣传)……
你觉得很烦了吗?那我得说,这才刚刚开始。
革命必然会经历:合伙人内讧(比如陶成章就挨了蒋介石的黑枪)、公司资金短缺无法完成项目(参考孙中山搞的那些组织混乱的起义)、公司发展方向有巨大争议(毛教员和张国焘的北上抗日还是南下四川之争)……
所以革命和创业是一个工种,只不过创业能买币续命,做人民币玩家,革命则强制要求一命通关。
11
同样,就跟创业一样,你首先得要有个商业模式。对于这个,所有人第一反应基本就是抄作业。马云抄eBay、抄PayPal,刘强东抄亚马逊,大家都是这么干的,没啥丢人的。
改良可以抄日本,革命抄谁呢?这在国外还真没啥好例子,不过没事儿,咱们历史长,总能找到案例。总之接下来主要有三件事情可以做:鼓吹、暗杀、起义。
革命第一招,是鼓吹,鼓吹就是宣传。
这个直接抄朱元璋就好了。明太祖征元朝檄文“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到了清末则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都是一脉相承的。
12
特别注意啊,理想归理想、宣传归宣传,这一点一定要拎得清。中山先生当然知道革命最终的目的是“建立民国”,但那时还是愚民流行吃人血馒头的时代,什么民国、共和、立宪,百姓表示一个字都听不懂。不理解这一点的,可以看看阿富汗的故事,感受一下和阿富汗人民探讨“美式民主”和“苏联社会主义”的难度。
那啥能听懂呢?“驱除鞑虏”!翻一翻《鹿鼎记》就懂了,天桥下韦小宝听的是《大明英烈传》,百姓耳朵里听到的是朱元璋杀蒙古人,心里念的却都是满清鞑子。这是一个思路的。
革命宣传,就是用人民群众听得懂的话来传播革命理念。阿Q说革命党“白衣白甲,戴着崇祯皇帝的孝”,高中课本的解释是这“代表了人民群众不理解革命”。拜托,这显然就是革命党宣传的成功案例好不好?
13
“社会主义”是给读书人听的,“打土豪分田地”才是留给未庄的阿Q们听的。“消费升级”是个玄学,“拼多多百亿补贴”才是句好口号。
顺便说一句,中国革命的特点是“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第一代革命党的工作,就是“推翻满清”。至于民众理解成反清是为了“复明”“兴汉”还是“建立民国”,这都没那么重要,先完成第一个艰苦任务再说。
大家如果在创业公司待过,就很能明白这种心态了。5块本金要做10块钱的事儿,能熬过一天是一天。梦想当然是建立能生存102年的公司,但现实是下周先给我死皮赖脸地搞到两个客户活下去再说。
14
所以网上老是有人说孙中山当初是中了日本民族主义者的圈套,搞出“驱除鞑虏”这种宣言。因为“驱除鞑虏”了,可不就把东三省、新疆、蒙古连带着驱除出去,汉族缩回到中原基本盘,方便日本人蚕食了吗?
拜托,老孙12岁去美国留学,17岁就开始搞地下党,30岁不到就能说服会党跟自己造反搞广州起义,怎么可能连这点道行都没有。
他一辈子都在为革命拉风投,利用各种势力来为革命添砖加瓦,典型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为达目的使尽了手段。
当年的老孙跟美国人谈“反抗帝国压迫”,跟日本人谈“黄种人大团结、大亚洲主义”,跟英国人谈“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跟法国人谈“投资中国革命的惊人回报”,跟黑社会谈“反清复明”,跟读书人谈“共和社会”……
15
拉风投的本事练的炉火纯青,怎么会着这种道儿?
所以你看清末的革命宣传,对于高层,讲共和、讲民国;到了基层,就基本是以“反清”为主题了。
从宣传口号来说,鼓吹反清这事儿执行的非常到位,毕竟连未庄的阿Q都能听到革命党要反清复明,这个绩效完成度可以打个满分了。不过严格来说,功劳簿上耍笔杆子的前辈只能领30%,剩下是谁来帮忙的呢?当然是满清自己喽。
一方面,晚清治国一塌糊涂,打不过英法也就算了,闭关锁国了这么多年,老百姓基本分不清英国、美国,普遍感觉自己是被外星人给打了似的,或者是类似于蒙古骑兵又来了的那种感觉。反正还能接受。但被日本人打了这事儿,心态可就彻底崩了。
16
被谁打都不能被日本人打啊!甲午海战之前,从光绪、慈禧、翁同龢一直到路人甲,大家普遍认为打不过欧美,打赢你日本还是可以的嘛。毕竟洋务运动之后,《美国海军年鉴》说我大清水师全球第九,妥妥的东亚列强,各路人马相当乐观。
当然,是不是真“列强”不知道,不过朝廷肯定是把自己当列强了。脑子比较清醒的自然是北洋水师的亲爹李鸿章,一直认为不能开战,然而没有什么用,软骨头的话有什么好听的。
现实大家都知道了,脸被打得噼啪作响。孙中山后来说,甲午之前他谈革命老是被当成疯子,甲午之后大家觉得他是个“先知”,情况完全不同了。
17
另一方面,咱们之前说过,仇恨这东西,传上千年有点难,延续个几百年一般是没问题的。有一句说一句,汉族记仇,老百姓不吭声,不代表没人记得。
所以当时革命党纷纷把《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录》这些事儿翻出来大肆宣传。那个高中必考的邹容《革命军》,开篇就是谈“扬州十日”。发行的时候经常是和《扬州十日记》捆绑销售。读完真是让人睚眦尽裂,对清狗恨入骨髓。
这书在清末那种全民文盲的时代卖了110万册,换到现在可以理解成销量3000万册,类似《明朝那些事儿》正版加盗版那个级别的销量,可谓厉害到了极点。所以搞宣传,有一大半靠的是满清自己黑料多,怨不得别人。
18
革命第二招,是暗杀,暗杀就是派刺客。
先吐个槽,有个作家写了一本关于狼的书,大意就是农耕文明身上是羊性,游牧民族是狼性,要呼唤狼性……恃强凌弱屠城杀平民是不是狼性我不懂,不过说汉地十八省只有羊性,那就真是瞎扯了。
汉地是没有狼性,汉地有的是血性。七尺男儿,“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
19
清末就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时代,是志士愤怒的时代。吴樾、史坚如、秋瑾、徐锡麟……前辈们血溅轩辕,震慑天下。如果太史公泉下有知,不知道会如何去写1900年代的《刺客列传》。
你以为刺客是彪形大汉、五大三粗吗?其实他们丰神俊朗、眉目清秀。刺杀广东巡抚德寿的史坚如,人称“容貌妇人风骨仙”。他爷爷是翰林院编修,从小家境富裕。就是这样的人,埋了一百斤炸药在两广提督德寿房下,“博浪一击胆如天”。可惜功败垂成,地道挖偏了,没炸死正主。临刑前被拔光指甲,仍誓不屈服,言“一击未中,悔恨终生”,在普通孩子大三的年纪(21岁)慷慨就义、血洒珠江。
20
你以为刺客都是文盲,被洗了脑,结果盲目送命吗?其实他们饱读诗书,文、字俱佳。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徐锡麟、参与安庆起义的秋瑾都是留日高材生。前者刺杀成功后,被凌迟挖心。后者牵连被杀,死前作诗“秋风秋雨愁煞人”。
后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革命先驱陈独秀、大先生鲁迅,当年都是光复会暗杀团成员。蔡元培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陈独秀是北方暗杀团的(就是吴樾的那个)、鲁迅一度考虑去刺杀,后来因为家有老母才作罢。
也就是说,脑袋被挂在城墙上的那些人,如果熬过那几年,说不定也是个校长、文豪、主席……然而生不逢时,只能拿着大好头颅,“伏尸二人,流血五步”。
所以,中原没狼性不奇怪,毕竟血性太强,没法变回畜牲。
21
说起刺杀,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我还是要多说两句,功劳不能全算到孙中山头上。现在历史课本一般不太愿意多提这个,所以乍一看好像这些事儿都是同盟会领导的一样。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同盟会嘛,顾名思义,他就是个“同盟”。如果大家不是特别理解啥意思的话,回想一下《鹿鼎记》的“杀龟大会”就明白了。杀龟大会优秀的地方,同盟会都有,但他的臭毛病同盟会也一样都没跑掉,不过好在没那么严重。
比如杀龟大会是反清,但其实反清完了到底咋弄基本没谱。天地会要立唐王、沐王府要立桂王、李西华说立个屁,咱们重新搞个皇帝出来也没啥不好的。最后大家只能在“杀掉吴三桂”这件事情上达成阶段性一致。
22
他们同盟会其实也是这个德性,推翻满清后到底怎么搞?立宪?三权分立?五权分立?联省自治?大家稀里糊涂、主意多得很。但最后大家能达成“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共识,这就比杀龟大会强太多了。
再比如,杀龟大会上搞了个十八省“锄奸盟”,陈近南、顾亭林还成了总军师,声势浩大。然而也并没有什么用,总军师别说指挥少林、华山这种中间派的,连沐王府和天地会这两个强硬派能不能协调都是个问题。
同样,同盟会三大台柱子,孙中山的兴中会,主要是一帮广东人;黄兴的华兴会,主要是一帮湖南人;陶成章的光复会,主要是一帮浙江人。孙中山虽然是“总军师”,但其实指挥起来非常困难。
23
比杀龟大会好的是,华兴会的黄兴是“二把手人格”,按实力他其实是可以当老大的,但黄总非常坚定地拥护孙总,力保革命大旗不倒,维护了团结。你可以认为就是陈近南和沐剑声之间非常团结,这就让革命胜算大增。
顺口说一句,对于这类政党缺少战斗力的问题,孙中山一直非常恼火。二次革命失败后一度病急乱投医,想要搞“签字画押”、保证完全服从指挥这种传统会党的做法,要不是后来走上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道路,开始借鉴苏联,根本不可能搞出国民党和北伐军来。
最后,非常遗憾地说,内讧这种事儿总是一茬接着一茬。锄奸盟还没开工,郑克爽倒是先去搞陈近南去了。同样,反清八字还没一撇,光复会就和孙中山闹掰了。
24
矛盾主要是资金分配的问题,这种事儿在创业公司非常普遍。贫贱夫妻百事哀嘛,总共就没几个钱,三个副总都认定自己的项目成功机会大,内部不吵架才怪呢。不过大家主要是骂仗,辛亥之前还没到动刀动枪的地步,这就比杀龟大会强,也算是大有进步了。
这三点一结合,大家就明白了,虽然说是“同盟”,但各自独立性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是光复会,基本上是老大陶成章、章太炎自己在玩自己的。所以严格来说,徐锡麟、秋瑾、吴樾……这些响当当的名字,跟孙中山的确关系不大。
更让人无语的是,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和光复会抢浙江都督的位子,陈其美的结拜兄弟蒋介石暗杀了陶成章,光复会群龙无首,最终被吞并。这就更是黑料十足了。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嘛,有意无意的,国民党上台后,追溯革命党史,很多功劳也就挪到了同盟会头上。
25
行文至此,我们稍微评价两句。一般而言,读完以上的“革命·刺客列传”,大多数人会热血沸腾,但看到革命党人兄弟阋墙又不免有些悲哀。这也是人之常情。
中国历史往往充斥着“三同”:“同生共死、同床异梦、同室操戈。”革命也难脱窠臼。陶成章、陈炯明、廖仲恺、四一二、皖南事变……每个名词后面都是血淋淋的内耗和黑料。
看到这些东西吧,有的人幻灭了,觉得革命太黑暗了,心灰意冷;有的人兴奋了,原来革命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呛天呛地各种不服;有的人一声叹息,人间正道是沧桑,嘴炮容易做事难。
我们没法为别人做道德评判,只能说事实就是如此,人性和局势就是如此复杂。个人而言,我是觉得读革命史属于“所见即所得”,你能看到什么,不在于革命是什么,而在于你想看到什么。
所以我再讲三件事儿,看完之后,大家对革命的感觉会更复杂,但也更真实一些。
26
孰易?孰难?谁来评判?
第一件事儿是关于“立孤与死孰难”,故事是大家都熟悉的赵氏孤儿。
容我啰嗦两句,讲讲故事大纲。
春秋晋灵公时代,权臣屠岸贾只手遮天,害死赵氏满门,只留下一个孤儿。程婴为保存赵家唯一的血脉,向老臣公孙杵臼求救。但此时屠岸贾已布下天罗地网,两人实难脱身。
于是公孙杵臼问程婴:“死和把孤儿养大相比,哪个难?”——“立孤与死孰难?”
程婴说:“死容易,把孩子养大难。”——“死易,立孤难耳。”
于是公孙杵臼说:“好,那请让我做简单的,把孩子养大的事儿,就靠你了。”——“吾为其易者,请先死。”
27
于是,程婴把孤儿和自己亲儿子调包,然后假意告发公孙杵臼。屠岸贾大喜,当着他的面杀了孩子和公孙先生。程婴亲眼见儿子、好友被杀,肝肠寸断而不能外露。之后,又因卖孤求荣而被天下唾骂。
忍辱负重十五年,程婴终于把赵氏孤儿抚养成人,取名“武”。两人设计为父报仇,诛灭了屠岸贾家族,恢复赵家爵位。功成之后,程婴决意自尽,前去拜别主公。
赵武泣泪挽留,程婴说:“当初公孙先生认为我能完成大事,所以先我而死,现在大事已毕,我岂能贪生。”于是坦然赴死。
“立孤与死孰难”,就是“赴死和革命孰难”。戊戌事败,谭嗣同对梁启超说:“程婴杵臼,吾与足下分任之。”之后从容就义。革命党人,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只是“引刀成一快”固然不易,“同志仍需努力”只有更难。
28
陈天华、杨守仁、姚宏业,这些都曾经是响当当的人物,但前途茫茫、救国无方,他们终于难以抑制悲愤绝望,蹈海自尽。
甚至连黄兴这种老斗士,黄花岗起义失败后,看到革命党人年轻一代消耗殆尽,也一度意志消沉,想拿个炸药包和两广总督张鸣岐同归于尽算了。
要理解这种痛苦,大家可以听听汪精卫的故事。2009年陈德森拍了部《十月围城》,讲述五湖四海的义士为保护孙中山而英勇献身。有观众嘲笑说:“革命说是为了救中国,可怎么死的都是年轻人,老革命一个都没死?”这话也不奇怪,毕竟一百年前就有人说过。
29
1908年,河口起义被镇压,同盟会迎来了第八次造反失败。黄兴流亡新加坡,孙中山继续满世界找钱。梁启超那时候还是跟着康有为混“保皇党”圈子的,是同盟会的竞争对手,在《新民丛报》上说同盟会是“远距离革命家”,只会躲在海外忽悠别人去送死。
孙中山是老江湖了,听到这种话只当他是在放屁。汪精卫那时候才25岁,心高气傲,不顾胡汉民的苦劝,决心以死明志,前往北京刺杀载沣。临行前,留下一封信:“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愿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
30
为什么要去找死?因为年年打脸、年年死人、年年催债、年年嘲笑,这种日子怎么过?
立孤与死孰易?死易。
革命与赴死孰难?革命难。
死了,成烈士了,也就一了百了。但只要不死,你就得继续失败、继续愧疚、继续被骂……继续革命。
第二件事儿是关于徐锡麟的。
徐锡麟刺杀恩铭,舍生取义的故事,高中历史都教过了。不过课本不太愿意提的是:恩铭其实是个开明好官。
31
恩铭,旗人出身,28岁任山东知县。同治十二年,黄河决堤,他与役夫同吃同住在工地。之后治河道、整盐务、赈灾民,一路升到江苏布政使。他是清末的实干家兼开明官僚。
他任安徽巡抚时,已经60了。但老而弥坚,创建安徽讲武堂、安徽巡警学堂。他又觉得中国缺少人才,需要更多优秀教师,于是尽心尽力,筹款创建安徽师范学堂。这所学堂,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安徽的活动基地。在之后,改为中学,由毛教员手写提名:“安庆第一中学”。
32
徐锡麟,就是恩铭一手提拔的安徽巡警学堂校长。他拜恩铭为师,被引为亲信,官运亨通,以至于革命党人陶成章一度怀疑他做了官后,不想革命了。
1906年,光复会准备安庆起义。徐锡麟先请恩铭检阅警察学堂的毕业生,就在颁发毕业证书时,突然拔枪,向恩师连开七枪,拉开了起义的序幕。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徐锡麟并非孤例。1905年,清朝预备立宪,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做准备。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33
吴樾,光复会北方暗杀团成员,陈独秀挚友,认定“清朝立宪如果成功,只会更久地蒙蔽汉人”,于是前往暗杀五大臣。结果行刺不成,自己反被炸得手足齐断、腹破肠断而亡。
五大臣出洋因此被阻隔半年,终于还是成行。其中有一位叫戴鸿慈,回国后改大清刑部为法部,开始了中国司法独立的进程。他建成了中国第一所现代监狱,叫做“京师模范监狱”,被认为是世界管理水平最优的监狱之一,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市监狱”。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34
徐锡麟临刑前,主审官问他是否孙中山同党,他回答“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再问他:“畜牲,你何以忍心刺杀恩公?”徐锡麟说:“恩铭于我,是有私惠;我杀恩铭,只为苍生。”
孰是孰非?人间正道是沧桑。
最后一件事儿是关于孙中山的。
老孙这个人吧,黑料简直是满坑满谷。他去世后,孙先生长期的竞争对手梁启超在《孙文的价值》里说:“我对孙君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吾们所看见的,只是孙君的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
35
是不是觉得很兴奋?毕竟一门三院士他爹都狠狠批评老孙“不择手段”了,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只不过老梁还有后半句:“在现在这种社会里头,不会用手段的人,便悖于适者生存的原则,孙君不得不如此,我们也有相当的原谅。”
为啥要说“相当的原谅”呢?因为老梁是过来人,他自己也知道,教书育人可以不用脏手,可惜光凭嘴皮子上下一碰可没办法颠覆政府。刀口舔血的年代,老梁身边那一帮动手搞革命的,哪一个不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
36
从他恩师康有为开始,有一个算一个,但凡想搞成点事儿的,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你把一帮子能力最强、意志最坚定、手段最狠的人放在一起,不内斗才怪呢。
只不过孙文不需要他人原谅。孙中山生前死后,最不缺的就是“骂”,最不需要的就是“原谅”。
少年时代,他砸自己村里的泥菩萨,被骂不敬祖宗,后来却被称作光宗耀祖;青年时代,他搞广州起义失败,被读书人骂痴心妄想,等到甲午之后,众口又称赞他早日看出清廷无药可救,为起义失败扼腕长叹;
37
中年时代,宋教仁被刺,他想要二次革命推翻袁世凯,被骂不识大体,破坏共和,后来袁世凯倒行逆施,悍然称帝,大家又觉得老孙果然目光如炬,看出老袁狼子野心;人生最后几年,他联俄联共,二次黄埔创业,又被梁启超说是苏联人的傀儡……
只能说,特殊年代,好人不长命,坏人也活不久,只有孙文这样的猛人,才活得下去。而只有活下去,才会有希望。
三个故事讲完了,现在回到陶成章和内斗。有人或许会为他不值,但老陶这种人,自己也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寂寂无闻又如何?含冤而死又如何?对这群人来说,只要能“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这条命、这点委屈、这点名声又算什么?
38
讲完了革命的宣传、清末的刺客,感慨完革命的不易,我们来稍稍复盘一下已经出现的三波人:庙堂之上,汉臣侵蚀满清权力;江湖中,会党势力遍布全国;“秀才造反”的书生们,已经醒悟了鼓吹、刺杀、造反三要素。那么接下来要讲的,就是革命的终极手段——造反了。
什么是造反,当然不是阿Q所理解的“同去同去”那么简单。造反,就是民间武装暴动,就是颠覆,就是打倒建制派,就是以卵击石、以小博大,就是大卫对歌利亚……从古至今,造反永远是百死一生甚至万死一生的行当。
领导者要利用极度有限的资源,去推翻清政府这个庞然大物,完成近似不可能的任务。造反,实在是一门高难度技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