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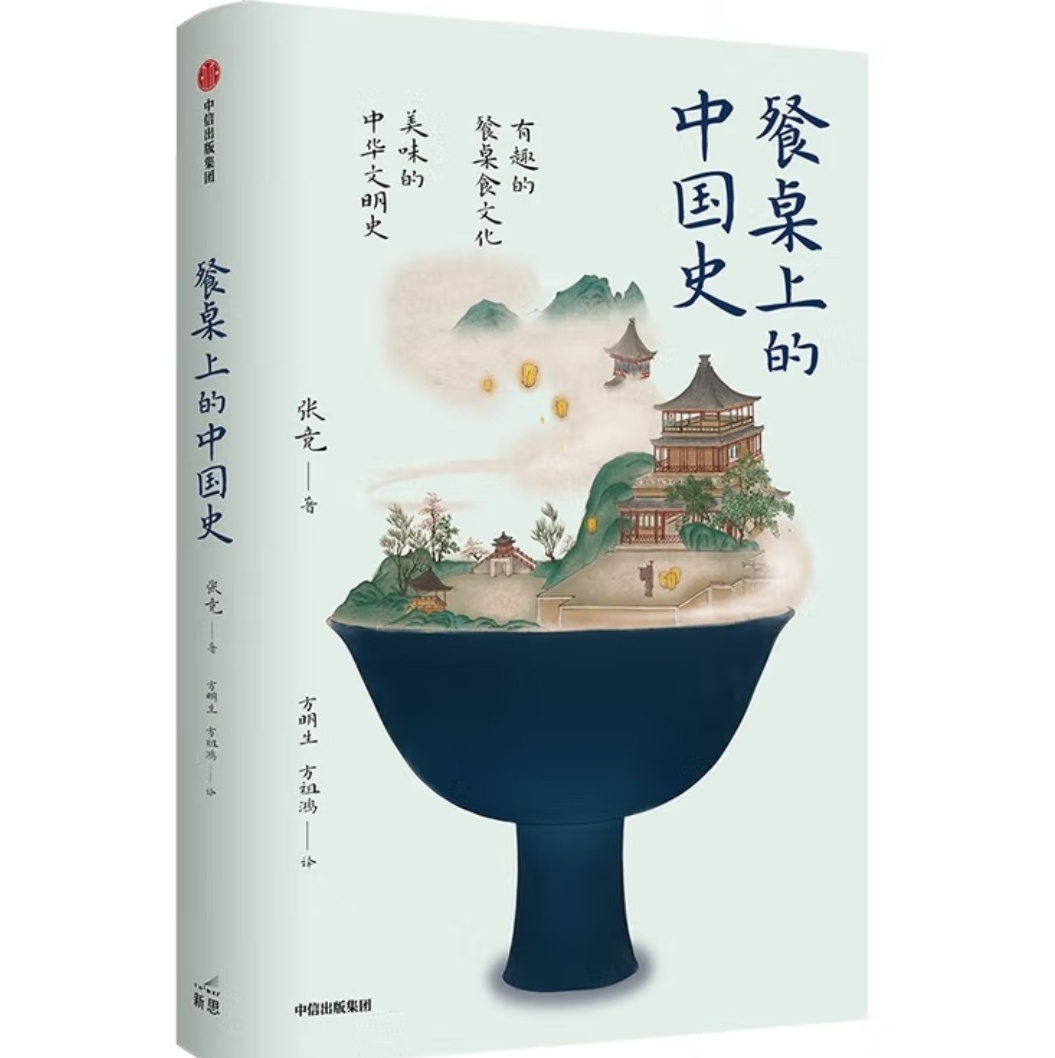
•饭是中国人的主食?其实连孔子也没得天天吃。
•儒学经典《论语》《礼记》不只教做人,其实也是美食教科书。
•张骞出使西域,一大贡献是带回了美食,还有制造美食的高科技。
•汉朝的街道上开始出现餐饮业,《盐铁论》痛批这些美食好吃到让人腐败与堕落。
•从春秋到唐朝,中国人其实是用勺子吃饭的,只有捞汤里的料才用筷子。
你吃了一辈子的中国菜,
其中的食材与菜式起源,
跟你以为的大不相同!
第一章 从孔子的餐桌说起
春秋战国时代
(下篇)
三、受时代限制的烹饪方法
【“生肉为脍(kuài)”常现餐桌】
1.
菜肴依据烹饪方法的不同,其食材的外形、味道会完全不同。那么,同样的食材,孔子时代的人们又是如何烹调食用的呢?
如前所述,《论语》中有“食不厌精,脍(kuài)不厌细”的说法。正如《汉书•东方朔传》中的“生肉为脍”的说法,脍就是将鱼或肉切细后蘸醋食用的菜肴,这与日本的刺身的吃法相同,是生吃的食物。
现代中国,除了极少一部分地区,基本上不吃生鱼和生肉。正式的中餐里没有生食的菜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日本料理店中刺身开始流行,只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新现象。)但春秋时代生食是十分平常的事,孔子也喜欢吃生肉片(脍)。《礼记》中记载,“脍”的调味品,春天用葱,秋天用芥末。吃生鹿肉则要用酱调味。
为什么要生吃?现代人美味佳肴吃多了,于是绞尽脑汁,变着花样吃。红烧、水煮、清蒸、油炸、熏制、串烤都吃腻了,便会觉得刺身很鲜猛。但站在古人的立场上想,看法就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变化。
2.
在铁器发明之前,烧饭烧菜是件麻烦事。锅碗瓢盆都是陶器,除了煮、蒸以外,别无选择。最大的问题是陶器传热性不好,加热很费时间。在农忙期或战时,根本不可能有此雅兴。
肉也好,鱼也好,切细生吃简单可行,开始时是不得已而为之,长久了就会习惯,也会想出各种吃法。铁器普及后,中国的生吃文化迅速消失。这一现象从侧面说明,生吃习惯是受了餐具限制的影响,乃不得已而为之。
吃生肉片的习惯在中国现在已经失传了,在日本却保留了下来。现代日本人不仅吃生鱼片,连牛肉、马肉、鸡肉都切成薄片蘸酱油而食。此外,阿拉斯加的因纽特人至今仍保持吃生鹿肉的习惯。
日本吃“脍”的历史非常悠久,但吃刺身是始于江户时代,据说起始于“渔民料理”。海上捕鱼时无法生火炒菜,抓上来的鱼只能剖而食之。比较可信的说法是,酱油在江户时代开始大量生产,蘸着酱油吃生鱼片美味可口,于是这道菜一发而不可收,王公贵族、下里巴人都趋之若鹜(wù)。因纽特人吃生鹿肉的习惯,应该也是狩猎时受烹调器具限制而形成的。
【古代烹饪法之滥(làn)觞(shāng)】
3.
中国最古老的烹饪方法之一是“煮”,最古老的菜肴是“汤”。肉,不管什么样的肉,大都是煮透后炖成汤喝。其实,早在孔子时代之前的殷商时代(前1600-前1046),煮就是主要的烹饪方法了。
煮这种烹饪方法时间长度相差很大,同样是煮,是稍微煮一下,还是花长时间煮透,做出来的菜肴区别很大。做肉菜,煮后取肉汁食用,还是把肉先切细,然后与汤汁一起食用,吃法不同就是不同的菜肴了。殷商时代,一直到春秋时代,菜肴的主要烹饪方法是煮成汤或羹的方式。
即使是汤和羹,也有各种类别,有以肉为主做的汤,也有只用蔬菜做的。《礼记•内则》中记载:“羹食,自诸侯以下至于庶人无等。”表明汤或羹这种菜肴从统治者到老百姓,广泛为人们所食用,并没有什么身份上的差别。
另一种“蒸”的做法,与煮一起被广泛运用在烹饪上。在王公贵族的家里,用“鼎”作为烹饪器具煮肉,再将肉放入底部开小孔的叫作“甑(zèng)”的炊具里,最后放在“釜(fǔ)”或“鬲(gé)”上面蒸。
做鱼或肉的菜肴时,经常用“烤”这样的烹饪方法。烤的方法分成“炮(páo)” “燔(fán)” “炙(zhì)”等。炮是将肉涂上泥巴后烤。燔就是烤。炙则是直接在火上烤。在古代,这些烤法可能各有讲究,可惜其操作细节都失传了。
4.
对于当时大多数人来说,日常的菜肴还是汤菜居多。汤菜即使肉的用量很少,加上其他食材后也能做成一道菜。而烤的话,没有一定量的肉就没法烹调。另外,汤菜用腌制的肉也能做,烤则只能用新鲜的肉。王公贵族,又当别论。而对春秋时代的寻常人家来说,把肉做成汤菜来吃,是最为常用的方法。
虽然汤菜是当时一般人最常用的菜肴,但烹饪方法也有讲究。有只用肉或鱼制作的,也有在其中加入蔬菜的。不只是汤菜,在那个时代什么蔬菜与什么肉配合,在《礼记》中皆有详细记述。例如烹饪猪肉,春天配韭菜,秋天配蓼(liǎo);配制调味品也有讲究,牛、羊、猪肉用花椒,其他的肉用梅子。还有,鹌鹑、鸡的汤菜里也可以加蓼。这些配料,有时不只是作为蔬菜使用,也作为调味品使用。从这些记述中可以推测,与主要食材搭配的烹饪方法在当时已经有了。这种烹饪方法也为后世所继承,现代中国菜中,主菜使用多种食材的情况很多。但春秋时代的人们吃的蔬菜与现代人食用的很不相同,因此孔子当时吃的菜肴的风味与现代中国菜的风味可能相差甚远。
5.
往前追溯一点,大约在西周时代,鱼可能是煮着吃的。《诗经•桧(kuài)风·匪风》中有这样的诗句:“谁能亨鱼?溉之釜(fǔ)鬻(yù)。”“亨”就是煮的意思,这句诗的意思是:“有谁能煮好吃的鱼?先把锅子洗干净了。”含有要把鱼煮得好吃并不容易的意思。《小雅•六月》中有这样的诗句:“饮御诸友,焦(此处念páo,在此成语中也写作“炰(páo)”)鳖(biē)脍(kuài)鲤。” “焦鳖”是裹起来烤的甲鱼。这个菜与脍鲤(生的鲤鱼肉)一起拿来招待贵宾。而现代中国的菜肴里,烹饪鱼类常用油煎或清蒸,煮汤的已不多见。但在日本料理中,迄今为止,煮鱼的料理还是很常见的。
此外,除了野外的露天餐饮或街头的大排档外,现在基本不用在火上直接烤的方法做鱼。不仅在餐厅,平常在家里也很少直接用火烤鱼吃。但是《国语•楚语上》里记载,作为祭祀供物,“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士大夫阶级以猪、狗为祭品,平民则用烤鱼祭祀祖先及祭拜神灵)。一般来说,祭祀结束后供品就被众人分食了,因此可以推测,春秋战国时代烤是很普遍的烹饪鱼的方法。
【凉拌菜与腌菜之由来】
6.
中国的制铁业始于何时还没有定论。铁制的农具在春秋时代已被制造出来了,但文献中没有提到有铁锅。当然,像现代才有的这种薄铁锅肯定还没有出现。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中期,人们还没有使用铁锅。用陶器或青铜器的锅子就能烧煮的汤菜,就成为当时主要的菜肴。
“炒”这种烹饪方法还没有出现时,蔬菜的烹饪方法是很有限的。很多蔬菜不适合蒸或烤,除了汤菜,主要的烹饪方法就是做成凉拌菜或腌菜。春秋时代的蔬菜食用方法,与之后的时代相比十分简朴。史书中常出现“菹(zū)”这个字,指的是醋渍或盐腌。
在当时,只用蔬菜做的菜看为王公贵族所嫌弃,被视为穷人吃的食物。《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中有这样的记载:
原文:
孙叔敖相(xiàng)楚,栈(zhàn)车牝(pìn)马,粝(lì)饼菜羹,枯鱼之膳……面有饥色,则良大夫也,其俭偪(bī)下。
译文:
孙叔敖担任了楚国的宰相,但外出时乘坐的还是那种一般的士大夫搭乘的、用母马拉的车,吃的是粗糙的饭、蔬菜汤、干鱼之类……看起来一副受饥挨饿的样子。这样的人太俭省了,即便是个好的大臣,对下面的人来说也太过苛刻了。
作者对孙叔敖的举止并不推崇。可见,只有蔬菜的汤菜,在当时是很粗糙的菜肴。另外,在《论语》中,也将“菜羹”与“疏食”(即粗糙的饭食)相提并论。
四、神享用的供品与人品尝的菜肴
【清蒸全鸡溯源】
7.
中国菜与日本料理,在两个方面很不相同。其一是日本料理除了鱼,在烹调时不留下动物的原形;其二是日本料理不论正式场合,还是家庭烹饪,都不用家畜的头、脚、内脏。有个别神社在祭祀时用鹿头作为供品,但从整个日本料理来看,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几可看作例外。绝大多数的日本人都不知道这些神社的祭祀习惯。
笔者在中国生活的时候,曾在家里招待过几位日本朋友,准备向他们介绍我最得意之作:蒸鸡。我一大早宰了不到六个月的童子鸡,将整只鸡放在锅里蒸。除了放入绍兴酒、生姜以及切细的葱和少许盐外,不放其他调味品。由于蒸的时候没有多余的水分,所以味道浓郁,肉质柔软。奇怪的是,几位日本朋友对这道菜完全不感兴趣,无论怎么推荐,他们都不动筷子。后来才知道,日本人不吃用整个动物制作的菜肴。要是看到整只鸡、鸭、兔或鸽子放在餐桌上,大多数日本人的反应都是拒绝的。不过只要看不出动物的原形,日本人就百无禁忌,什么都敢尝一口。
8.
反观中国人的餐桌,从大饭店到一般人家里,几乎餐餐可见整只动物原形制作的料理。猪蹄一般是整只红烧的,蒸整鸡或蒸整只甲鱼都是很常见的菜肴。著名的北京烤鸭,在让客人品尝美味之前,先将烤好的鸭子放上餐桌,让食客观赏鸭子烤的程度,待客人看得心满意足后,才开始一片片地将肉削下来。在日本基本看不到这种饮食方法。在日本,若吃烤鸭,准备工作一定全部在厨房里完成,端上餐桌时,鸭子的形状已经完全不见了。有的店还将鸭肉在饼里包好后再端上来。在中国,不仅是北京烤鸭,烤乳猪也是将皮和肉切开,切成长方形,放回到背脊和肋骨上,再端上餐桌的。
江苏省镇江市有一道叫作“酱烧猪头”的名菜,是在《随园食单》中就出现过的、非常有历史渊源的菜肴。这道菜先是将猪头中的骨头取出,切成三到四块烧煮。菜肴烧好后,放入餐盘时,要还原原本猪头的形状,再端上餐桌。
【“供奉”与“食用”之间】
9.
中国菜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用到很多动物的内脏。肝、肾(腰子)、肺、心、胃、肠等都做进菜肴里。另外,猪、鸡、鸭的血都是体面的食材。日本与中国在文化上虽然相近,但为何在食文化上有如此不同?理由可以列出很多,一个说法就是与祭祀的规矩有关。
日本人在祭祀时,基本上不使用肉类。日本的佛教在祭祀时供奉五种物品:米饭、煮菜、豆类(或凉拌菜)、香味作料、清汤,当然全是素食。神道教的祭祀一般是七种供品:米、盐、水、酒、时令疏菜、时令水果、有头和尾的鱼(大多是干鱿鱼)。此外,根据季节,可添加年糕或点心。不管佛教、神道教,都没有用肉类,也根本没有想到烹饪整只的家禽或家畜作为供物。除海产品外,日本人排斥对整只动物的烹饪,也不吃家禽或家畜的内脏、脚、头。我想这种心理与祭祀的习惯是相通的。日本料理中,有整条鱼做好后完整地端上餐桌的菜肴,是因为在祭祀供品中也有烹调好的整条鱼。不丢弃鱼的内脏也许是同样的理由。
中国的饮食习惯也与祭祀惯例有密切关系。古代祭祀天、地、祖先时,都供奉做好的菜肴。佛教传入之前,有祭祀神灵用“六牲”(即供奉六种禽畜)的习惯。另外,祭祀死者时也供奉菜肴。
10.
据《礼记•郊特牲》的记载,祭祀天的仪式上供奉牲畜的血,祭祀祖先的仪式“大飨(xiǎng)”上供奉生的肉,祭祀土地神(社)和五谷神(稷)的“三献”仪式上供奉半熟的肉,祭祀其他诸神的“一献”仪式上供奉的是与平时人们的食物相同、烧煮充分的肉。
另外,还记载着古人把牲畜的头、心、肺、肝脏作为供品的情况。为何用这样的物品做供品,《礼记•郊特牲》中这样记述:
原文:
首也者,直也。
译文:
祭祀用(动物的)头,因为它代表整体。
原文:
血祭,盛气也。祭肺肝心,贵气主也。
译文:
祭祀动物的血,是尊重生命力旺盛。祭祀动物的肺、肝、心,是尊重生命力的根源部分。
《礼记》虽是汉代编纂(zuǎn)的读物,但收录的内容多为先秦时代的。
而《国语•楚语下》中也有以下的记载:
原文:
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太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
译文:
天子平时的盛馔(zhuàn)用牛、羊、猪齐全的大牢,祭祀时要供上三份太牢;诸侯平时的盛馔用一头牛,祭祀时要供上太牢;卿平时的盛馔用一羊、一猪的少牢,祭祀时用一头牛;大夫平时的盛馔用一头猪,祭祀时要供上少牢;士平时的盛馔用鱼肉,祭祀时要供上一头猪;百姓平时吃菜蔬,祭祀时要供上鱼。
以上是作为祭祀法典的文献中的陈述,从中可窥见古代关于供品的详细规定。
【祭祀与饮食习惯】
11.
献给神灵和祖先的供物,原本是一定要用整只物品上供的。但像猪、牛那样的大型动物,整只拿来烹饪有很多不便。也许出于这样的原因,后来简化成将头、身体、腿等部位完整地烹饪后作为供品。即使是佛教传入之后,这种习惯还是被传承下来。近代以后,在亲人的葬礼上或祖先的忌日,也都使用烧煮好的全鸡、全鸭。
祭祀结束后,供品自然就成了参与祭祀的人们的食物。《礼记•郊特牲》中记载,祭祀的供品,作为先王转赠给臣下的食物,臣下应以感恩戴德之心受用之,并非要品尝其中的美味。即,供品先让神灵享用,然后人可以食用。现代中国菜中食用牛、羊的内脏,或猪的头、脚、脑等的习惯,很可能是源于这种古代祭祀风俗。
烹饪的方法与祭祀也有关系。《礼记•郊特牲》中记载了为何祭祀时要供奉不同烹饪方法做出来的不同肉菜:
原文:
腥、肆、爓(xún)、腍(rěn)祭,岂知神之所飨(xiǎng)也?主人自尽其敬而已矣!
译文:
在神灵前供奉肉类,用切成大块的生肉、劈开的肉、煮好的肉、煮透的肉。因为不知其中的哪一种能满足神灵的需求,主人为尽自己的敬意,唯有备全所有供品。
这里不免有借神的名义来尽享美食之嫌,但从中也可发现各种烹饪方法曾经与祭祀的风俗有很深的关系。
中国与日本的饮食习惯有巨大的差异,但从神所享用的东西也就是人所食用的东西这一视角上来看,中国与日本之间可以说并无多大差异。
五、孔子时代的餐桌礼仪
【饭是用手抓着吃的】
12.
笔者上小学时所读的连环画中有一幅孔子用餐时的画面:孔子坐在草席上,使用炕桌那样的矮桌,但餐具与现在使用的基本相同,且用筷子来用餐。当时并没有感到有什么疑问,也许现在很多人也没有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据《史记》记载,商纣王(约公元前11世纪)最早使用象牙的筷子。但考古学发掘显示,筷子最早只能追溯到春秋时期。暂且不论筷子究竟始于何时,即使孔子时代的人们已开始使用筷子,其使用方法与现在相比,应该也是大不相同的。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了一个颇有意思的故事:
原文:
孔子侍坐于鲁哀公,哀公赐之桃与黍,哀公曰:‘请用。’仲尼先饭黍而后啖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饭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对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谷之长也,祭先王为上盛。果蓏(luǒ)有六,而桃为下,祭先王不得入庙。丘之闻也,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今以五谷之长雪果蓏(luǒ)之下,是从上雪下也。丘以为妨(fáng)义,故不敢以先于宗庙之盛也。'
13.
译文:
有一天,孔子拜见鲁国的哀公,在近旁侍奉的位置坐下。哀公赏赐孔子桃子和黍米,请孔子吃。孔子先吃黍米饭,然后吃桃子。周围的人都捂着嘴暗笑。哀公对孔子说:“黍米饭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除去桃子上的毛的。”孔子回答:“我知道这种规矩,但黍米是五谷中位置最高的,祭祀先祖时被用作上等的祭品。而桃子是六种瓜果中最低下的,祭祀先祖时不得入祖庙。我听说,君子以低贱的东西擦拭尊贵的东西,而没有听说反过来的做法。现在用五谷之首的黍米去擦拭瓜果中最末位的桃子,会变成上下颠倒,这是违背大义的,我不能那么做。”
暂且不论孔子是为了劝谏鲁哀公才说这番话,还是他不知道贵族的奢侈用餐方式,从这个情节中能发现一个意外的事实:用来除去桃子毛的黍米饭,应该没有配上筷子。这样的话,孔子就是用手抓着饭吃的,这或许就是当时的用餐方法。如果当时是像现在这样用筷子吃饭的话,无论如何,孔子一定不会用手抓黍米饭来吃的。
【筷子是取菜用的】
14.
《礼记·曲礼》中记载了黍米饭用餐的正确做法—“饭黍毋以箸”(食用黍的时候不要用筷子),显然吃黍米饭时是不用筷子的。《管子·弟子职》中也有“饭必奉擥(lǎn),羹不以手”(饭用手捧着吃,汤是无法直接用手吃的,要用筷子和调羹)。
《礼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与地位高的人一起用餐时,由于会在同样的食器中抓饭食用,这时,双手不能搓。关于这一点,唐代的儒学家孔颖达(574—648)曾作注解释,因为古代人是用手来吃饭的,在和别人一起用餐时,手一定要干净。如果在吃饭前搓手的话,会被认为不干净,从而被一起用餐的人所鄙视。
另外,当时与客人或地位高的人一起用餐时,饭不能捏成团来拿。这一点,孔颖达也有解释:在同样的食器中拿饭食用之时,如果把饭捏成团就会拿得更多,这样就会给人一种争抢食物的印象,导致个人形象受损。但这只是指和别人一起用餐时的礼仪,平时一个人用餐时这么做并无大碍。据《吕氏春秋•慎大》记载,作为诸侯的赵襄子就是把饭捏成团吃的。
15.
这种古代习俗甚至至今还在江南一带留存着。有一种称为“粢(zī)饭”的早餐食品,一般只能在大众餐馆或路边摊上吃到,即将糯米和粳(jīng)米按一定比例混合,在蒸笼中蒸熟,可根据客人的要求在中间加上油条或砂糖,捏成团后送到客人手里。这种食物就是用手拿着吃的,不用筷子,吃法与日本的饭团相似。不过这几年间,这种食品已不多见,更常见的是便利店供应的日式饭团。
《礼记》中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吃饭时仍不用筷子。取菜时是用筷子的;喝热汤时,在吃汤中的蔬菜时是用筷子的,没有加入蔬菜的汤是不用筷子的。但现代中国,人们一般是用汤匙来喝汤的。
有趣的是,朝鲜半岛上有与此相似的饮食习惯。韩国人用餐时,吃饭不用筷子而用勺子,取菜时用筷子。喝汤时,只有汤中有菜时才用筷子。这种饮食习惯似乎继承了春秋时代的遗风。
【分食制源远流长】
16.
现代中国,许多人在同一张餐桌上用餐时,习惯于在同一个器皿里取菜。但春秋战国时代与此不同。饭是盛在同一个餐具中的,而菜肴是按人分盆的,与现在日本的分食制相似。
《管子•弟子职》中有这样的记载:“各彻其馈(kuì),如于宾客。”(各自撤去自己食案的时候,要像撤去宾客的食案一样谨慎而行。)可以证明当时的用餐方式是分食制。另有记载,老师们用餐时,侍奉的弟子须不断巡视,按照情况为老师持续地添加食物。如果饭和菜肴是从一个食器中取的话,是无法这样侍奉的。
综合《管子》中的记述,以及前面引用的《礼记》中的记述,可以推断当时的习惯是这样的:平时的餐饮,饭也好,菜肴也好,都是分食的。但来了客人的话,饭备于同一个器皿中供大家分享,而菜肴基本上是一人一份。
餐桌上的饭和菜肴的放置方式也有详细的规定。据《礼记》记载,在劝来客进食时,饭放在吃饭人的左侧,汤放在右侧,鱼和烤过的肉放在外侧。醋、盐等调味料是放在内侧的,葱等作料是放在外侧的。
17.
另外,肉类菜肴,带骨头的放在左边,切下的整块肉放在右边。从调味品、作料的放置方法看,这很明显是一个人的食案。从桌上的菜肴放置方式看,也可以推断当时的用餐方式是分食的。
另外,上菜也有一定的顺序。同样是《管子•弟子职》,其中有记载:上菜的正确顺序是先上家禽或家畜的菜肴,然后上蔬菜汤,最后用餐接近尾声时上饭。这当中也记述了如果是老师用餐,弟子应如何侍奉的礼仪。这样来看,日常的饮食恐怕与上述描述大同小异。
作为与用餐相关的礼仪,有在食用前要洗手、食用后要漱口等规范。但这种礼仪普及到何种程度不很清楚,可能也不适用于所有场合。在《礼记•丧大记》中记载,吃粥时可不用洗手,但食用竹笼里的饭时必须洗手。这里所记述的是服丧期间的礼仪,饭前洗手是因为大家都用手从竹笼中取饭。
食后漱口的规范也并非千篇一律。《管子》中记载,老师吃完后用水漱口,学生吃完后,则是用手遮盖,擦去嘴角上的残渍即可。
【先祖们一日两餐】
18.
关于一天中用餐的次数,《庄子•逍遥游》中有这样的说法:“三餐而反,腹犹果然。”(一日三餐食用后,就不会感觉肚子饿了。)从这样的记述来看,在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已经确立了一日三餐的观念。
但似乎一般的老百姓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据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土的木简上的记载,殷商时期(前1600—前1046)普通老百姓一天只食用两餐(宋镇豪,1994);用餐的时间也因地区不同而有些不一样,大体是7点一9点食用第一餐,15点一17点食用第二餐。
早上吃的像是主食,一般比下午用餐的量要多。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仍维持着这样的习惯。在秦代的木简里,仍有按一日两餐的基准分配粮食的规则的记述,可证明在庶民中此后也继续着这种饮食方式。不仅如此,就是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还有一日两餐的地方。笔者1966年曾在广东省珠海市短期居住过。那时兄长在陆军医院当医生,工作日时是一日三餐,休假日则按当地的风俗,食堂只在11点和17点供应两餐。当时并没有遭遇灾害或饥荒。这也许是自古留下的风俗习惯。
当然,在上层阶级当中并非如此。可以推测当时的上层阶级是一日三餐的,一般老百姓则是一日两餐。此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上升,一日三餐的习俗也逐渐扩展至平民阶层。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