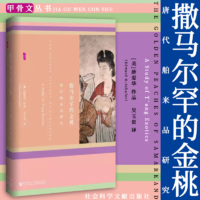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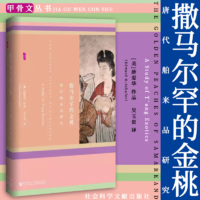
第十一章 药物(2)
底也迦
1.
乾封二年(667),拂林国使臣向唐朝皇帝献“底也迦”,这是一种货真价实的万能解毒药。据普林尼记载,这种丸药有多达六百种不同的成分。据汉文史料记载,底也迦“出西戎,彼人云用猪肝作之。状似久坏丸药,赤黑色。胡人时将至此,甚珍重之”。苏恭也说,底也迦主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积聚”。至于这种万能药的制剂中是否会有诸如没药、鸦片以及大麻——中世纪伊斯兰的解毒药中通常就有这些药物——之类的成分,我们还不清楚。
豆蔻
2.
中国本土就有土生的豆蔻,但是由于热带出产的豆蔻在唐代更受人们的喜爱,所以就有大量的热带豆蔻进入唐朝境内。“黑豆蔻”或“苦豆蔻”在汉文中又称作“益智子”。黑豆蔻出自岭南与印度支那,所以我们可以将这种植物看作是一种“半外来”的植物。据记载,将益智子“去核,取外皮,蜜煮为粽食”,可以起到健脑的作用,所以这种食物又叫作“益智粽”。但是益智子还具有更多的一般性质的滋补作用,主“益气、安神、补不足”,“夜多小便者,取二十四枚入盐同煎,服有奇验”。
“真豆蔻”出自交趾,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时,这种干果就已经从印度销往希腊,而且在罗马非常有名。据李珣报道,豆蔻叶“近苦而有甘”,豆蔻的叶、皮、果者可以入药。
“变种豆蔻”是印度支那出产的一种带有樟脑味的豆蔻,它也是唐朝进口的豆蔻中的一种,对于治疗“上气喘嗽”尤其有效。
3.
爪哇的“圆豆蔻”或“串豆蔻”是从一个叫作伽古罗的地方运到唐朝的,这个地方显然在马来半岛西海岸。这个国家的名字仍然保留在阿拉伯文里,它的意思就是“豆蔻”(qāqulah)。看来这种植物是从爪哇带来的,而马来半岛则是出于商业的目的才种植这种植物的。到了十一世纪时,圆豆蔻就被移植到了广东。唐朝人将这种豆蔻称作“白豆蔻”,正如段成式所说,这是因为圆豆蔻“子作花如蒲萄。其子初出微青,熟则变白,七月采”。白豆蔻有各种重要的医疗用途,其中包括治疗支气管炎和肺充血。
九世纪是一个诗人们被奢华、新奇的异国情调以及奇香异彩强烈吸引的时代。“豆蔻”这个词在九、十世纪的诗歌中是个很常见的词,在吴鞏、李贺、杜牧以及韩偓等人的诗歌作品中都出现过这个词。
肉豆蔻
4.
陈藏器是记述“nutmeg”的第一位中国人,他将“nutmeg”称作“肉豆蔻”。据陈藏器记载,这种香料——虽然当时似乎并没有将它作为一种香料来使用——是由“大舶”带到唐朝来的,而且与豆蔻一样,是“迦拘勒”地区的土产。但是,根据李珣的说法,肉豆蔻生于“昆仑大秦国”。这种说法并没有告诉我们肉豆蔻的原产地,但是却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肉豆蔻贸易范围的信息。其实早在六世纪时,欧洲就已经知道了东印度出产的肉豆蔻。在唐朝有一种用肉豆蔻研成末做成的粥,可以用来治疗各种消化功能紊乱的症状和腹泻。肉豆蔻及其配方在中国显然是很受欢迎的,因为到了宋朝初年,在岭南就已经种植了这种植物。
郁金与蓬莪术
5.
郁金属于姜黄属植物,是一种能够分泌出大量色素而且多少带有一些香味的根茎产品。从最狭义上来说,郁金在姜黄属植物中是一种微带辛味、多用作颜料的物种;据悉,这种普通的郁金是中国西南地区土生土长的品种。与普通郁金有密切亲缘关系的一种植物,是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地区以蓬莪术知名的一种高级的芳香品种。蓬莪术主要是用作香料的原料。在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地区,还有姜黄属植物的许多其他的品种,它们分别被用作染色剂、医药、咖喱粉以及香料制剂等多种用途。
6.
在汉文中,这些植物的集合名称叫作“郁金”,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指出的,虽然“番红花”在汉文中被比较明确地被称为“郁金香”,但是“郁金”这个字也是指“番红花”而言。总而言之,在贸易中和实际应用时,郁金与郁金香往往混淆不清,当有关文献中强调其香味时,我们就可以推知:这不是指郁金香就是指蓬莪术,反之,就是指郁金。
据唐史记载,天竺“有金刚、旃檀、郁金(或‘蓬莪术’?),与大秦、扶南、交趾贸易”。或者这里说的“郁金”是指郁金香也未可知。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它很可能是指郁金、蓬莪术和郁金香这三种植物。
7.
与这种情况类似的是,在唐代,“郁金”是大勃律、谢䫻、乌苌、迦湿弥逻等地的产品。这些国家大都位于印度的西北部地区,就这一点而言,唐史中记载的“郁金”很可能是指“郁金香”,尤其对于迦湿弥逻来说,它作为郁金香的故土实际上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了。
另外,波斯人则认为蓬莪术生于中国。波斯人的这种看法,或许可以由中国称为“姜黄”的一种姜属植物得到解释。姜黄也是由西域传入的。苏恭告诉我们说,姜黄“西域人谓之‘蒁’”,这个字的发音类似于“Jud”或“Jet”;在另一处,苏恭又说因为普通的郁金可以医治马病,所以“胡人谓之‘马蒁’”。或许汉字“蒁”就是某种东方语言中的“Zedoary”(蓬莪术)的第一个音节的译音;在阿拉伯语中,蓬莪术叫作“jadwār”。
8.
在唐朝医药中,郁金主要用于治疗“血积下气,生肌止血,破恶血”。据记载,郁金还常常被用来涤染妇女的衣物,在染衣物的同时,它还能够使衣服上带上一股轻微的香味,但是这里的“郁金”究竟是指郁金(turmeric),还是指郁金香(saffron)——在古代,郁金香也被作为染料来用——我们还不能断定。而与龙脑香一起铺在天子将要经过的道路上的“郁金”粉,则不是郁金香就是蓬莪术——请比较1960年发自布鲁塞尔的一条新闻:“11月15日,在杜博安国王与多妮娅·伊·阿拉贡的婚礼上,将在布鲁塞尔购物街中最繁华的吕讷韦大街上喷洒香水。”在九世纪中叶,唐宣宗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废除了唐朝铺洒香粉的习惯。
胡桐树脂
9.
在汉文中,将许多很重要但是却相互无关的树都称为“桐”。大体上来说,“桐”一般是指泡桐属植物,由于泡桐长着美丽的紫花,所以它又被称作“花桐”。从语言上来看,可以与桐类植物归为一类的树主要有被称作“梧桐”或“青桐”的“凤凰树”;有被称为“油桐”的“木油树”;有被称作“刺桐”的“珊瑚树”;还有被称为“胡桐”的“脂杨”。胡桐的树脂又被称作“大叶钻天杨树脂”(tacamahac),这个名称还被用来称呼北美的香脂白杨树脂和一种印度支那的树产出的芳香榄脂,而这种树却根本就不属于杨树。到了唐代时,被称为“胡桐”的这种树脂就已经传入中国内地。
10.
所谓胡桐树脂出自一种杨树,这种树的木材还可以用来制作家具。从中国的西北和戈壁地区一直向西通往欧洲的广大地区,到处都生长着这种杨树。这种树的汉文名称是因为它与“梧桐”(凤凰树)相似而得名,而不是因为与泡桐类似而得名。这种杨树的树脂在唐朝的市场上叫作“胡桐津”或“胡桐泪”。有些古时候的权威认为,胡桐泪是“虫食其树而脂下流者”。胡桐树脂“有夹烂木者”“有沦入土石碱卤地者”等等。甘肃、哈密以及突厥斯坦和伊朗各地也是唐朝使用的胡桐树脂的来源地。
医生们利用这种胡桐树脂治疗“大毒热,腹烦满”,而且还将它作为催吐剂来使用。更重要的是,胡桐树脂还被珠宝工匠,尤其是隶属于宫廷的珠宝匠作为一种焊接金银器的焊剂来使用。
刺蜜
11.
陈藏器是记述西域交河出产的“刺蜜”的唯一的唐朝药物学家。他说:“交河沙中有草,头上有毛,毛中有蜜,胡人名为‘给勃罗’(khār-burra,即‘羊羔刺’)。”这种说法使我们想起了阿拉伯的“骆驼刺”。陈藏器显然是研究了这种甜蜜的渗出液,他还具列了刺蜜能够治疗的多种疾病,其中包括“暴痢下血”。
另外还有一种与刺蜜相近的糖质物质,或许是与刺蜜出自同一来源。据记载,这种物质“生巴(四川)西绝域中”,陈藏器将它称作“甘露蜜”,这种名称将它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天生神奇的甘露联系了起来。陈藏器主张用甘露蜜来治疗“胸膈诸热,明目止渴”。
吉莱阿德香膏
12.
吉莱阿德香膏又称“麦加香膏”,是一种阿拉伯植物的汁液,据说是示巴女王将它引进了巴勒斯坦。九世纪时,这种绿色的树脂引起了段成式的注意,他记载说,这种香膏“汁如油,以涂疥癣,无不瘥。其油极贵,价重于千金”。据段成式记载,这种香膏出自拂林国。的确,罗马人是知道这种香膏的,因为在庞培和韦斯巴芗的凯旋仪式上,就曾经展示过产出吉莱阿德香膏的勃参树。段成式所记录的汉文名“阿勃参”,是这种树的名称的叙利亚语形式“apursāmā”,它来源于希腊文“bálsamon”。但是我们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吉莱阿德香膏当时已经传入了唐朝。
波斯树脂
13.
波斯树脂是一种有甜味的树脂,它是一种树的树液,这种树与生产阿魏的树有亲缘关系。段成式也知道这种树脂。他还记录了波斯树的波斯文名称“bīrzai”(䭱齐)和与阿拉姆语“khelbānita”同一语源的闪语名“顸勃梨咃”。“khelbānita”是犹太人使用的圣香的四种成分之一的名称。普林尼和其他罗马作家也知道这种树脂。段成式说这种树脂生于波斯和大秦(一般指罗马的亚洲部分),并且认为它可以“入药疗病”。但是我们同样也不能肯定在唐朝境内是否见到过这种树脂。
阿魏
14.
与波斯树脂不同,阿魏作为一种药物和调料,在唐朝很有名气。唐朝人普遍接受了这种药物的西域名称,将它称为“阿魏”。这个名字很可能就是吐火罗语“aṅkwa”的译音,唐朝人还知道它的梵文名称“hiṅgu”(形虞)。进口的阿魏有晒干的树脂饼和根切片两种,据认为,后者的质量不及前者。当时有许多亚洲国家都向唐朝提供这种昂贵的药材。其中主要者有谢䫻,此外还有波斯以及其他没有记载国名的南亚和中亚的国家。阿魏进入唐朝有两条途径,其一是由位于准噶尔边缘的唐朝重镇北庭每年作为土贡向朝廷进贡,另外一个途径就是由商舶经由南中国海运来。
15.
阿魏可以刺激神经,帮助消化,但是唐朝人利用最多的是它“体性极臭而能止臭”的奇异性能。阿魏还是一种高效的杀虫剂;而且“阿魏枣许为末,以牛乳或肉汁煎五六沸服之,至暮以乳服”,可以“辟鬼除邪”。
贯休和尚是一位天才的画家和诗人,他生活在九、十世纪之交,享年八十多岁。据贯休写的《桐江闲居》诗来看,阿魏可以与茶同时服用:
静室焚檀印,深炉烧铁瓶。
茶和阿魏暖,火种柏根磬。
数只飞来鹤,成堆读了经。
何妨如支遁,骑马入青瞑。
16.
这里说的“香印”当然是指香钟。支遁是四世纪时的一位隐居僧人,他还是一个非常喜欢骑马的人。我曾经反复强调过,段成式的笔记中的资料,更多的是得自广泛阅读各种语文的书籍,而不是靠他亲身的观察,所以我们不能根据他的书中记载有某种植物或动物,就贸然地断定这种植物或动物在唐朝出现过。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位兴趣广泛的学者的知识来源并不是仅仅限于书本。在详细描述生产阿魏的树时,段成式曾经提到了向他提供了相互矛盾的资料的两位僧人,其中一位是“拂林人”,名叫“弯”,而另一位是某个叫“提婆”的摩揭陀人。向段成式提供资料的这位拂林人很可能是小亚地区的人或叙利亚人。这件事表明,在段成式记载外来物时,他必定依靠了其他一些没有留下姓名的外国人所提供的口头资料。
蓖麻子
17.
据苏恭说,“��麻”有唐朝种者,也有胡中来者,因其“结子如牛蜱”,故名“��麻”。苏恭说的就是蓖麻子。在古代的许多地区,蓖麻都因为产油而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据认为,蓖麻最初很可能是在埃及栽培的,埃及人用蓖麻油来点灯。在唐朝,蓖麻子以及用蓖麻子榨的油都是用来治病的。
清泻山扁豆
我们将印度的“金黄”或“王树”以及阿拉伯的“印度角豆树”或“项链黄瓜”称作“天竺金莲花”或“金花”,或者更名副其实地将它称为“清泻山扁豆”。这种树的花非常美丽,长长的荚中生着鲜红的籽实。它是一种印度土生的树,因为它籽实周围的黑色果肉是一种享有盛誉的、治疗便秘的药物,所以从很早开始,清泻山扁豆就传遍了所有的热带国家。在唐代,清泻山扁豆被称为“婆罗门皂荚”或“波斯皂荚”,这是因为这种树与中国的“皂荚”(the Chinese honey locust)或被叫作“墨皂荚”的“皂豆树”(soapbean tree)很相似的缘故。清泻山扁豆的印度名称叫“āragvadha”(阿勒勃),阿勒勃对于唐朝医生来说是很熟悉的一种药物,他们用阿勒勃的籽实来治疗多种内科疾病。
海藻
18.
食用海藻类植物在中国并不算鲜见,例如可以调制美味菜汤的紫菜,就是中国中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的一种常见的出产——有时紫菜是从日本带来的。石莼是一种生长在南海浅水域中的“海莴苣”,在唐朝时,它就以“石莼”知名。当时石莼被作为一种利尿剂使用。唐朝人还注意到了石莼在“胡人”医学中的用法,并且将它记录了下来。
淡海带是一种褐色的海藻或海草,它含有丰富的碘、钾和糖。在唐代,淡海带被称为“昆布”,每年都由朝鲜半岛的新罗国贡献。东胡部落渤海靺鞨向唐朝朝廷贡献的土贡中也有昆布。据记载“海岛之人爱食之,为无好菜,只食此物,服久相习,病亦不生,遂传说其功于北人,食之皆生病,是水土不宜耳。”昆布作为治疗各种肿瘤的一种特效药,深受唐朝人的欢迎,其中有一种肿瘤看起来肯定是甲状腺肿。
人参
19.
在传统的中草药中,人参的人形根茎是真正的草本灵丹妙药。这种“神草”或“皱面还丹”——所谓“皱面还丹”是一个拟炼丹术的名称,它表明了人参的神奇功效——生长在山西太行山脉中的紫团山,但是大多数人参和最上等的人参都是从朝鲜半岛的高丽、新罗、百济诸国以及东北各地采集来的。据记载:
新罗国所贡者有手足,状如人形,长尺余,以杉木夹定,红丝缠饰之。
将人参作为礼物赠送友人,是唐朝的一种习俗。馈赠人参就像赠送一首诗、一幅画或者是一枚宝石一样司空见惯。
20.
在唐朝的诗歌中留下了许多因接受人参而表示谢意的篇章。例如皮日休在一首言辞极为夸张的诗歌中称,这种根茎在益寿延年方面的价值远远在道家术士的力量之上。唐朝的药物学家和其他许多人都认为,人参“主五劳七伤……补五脏六腑”。中国—朝鲜出产的人参的价值可以与希腊—阿拉伯出产的曼德拉草相媲美。根据中国科学家新近的研究,古人所记载的人参的神奇药效,其实并不足为奇,他们的研究表明,人参实际上含有一种刺激交感、中枢神经系统和泌尿、生殖系统的兴奋剂。
各种药草
21.
“延胡索”是蓝堇属的一种植物,这种植物的黄色根茎是由奚国经安东都护府传入唐朝的。据记载,延胡索可以治疗肾病。
“白附子”是远东的一种“麻风树”的块茎,这种微毒、褐色的块茎生长在朝鲜以及甘肃的边远地区的沙地中,它在当时被用来治疗“心疼”。
“仙茅”是一种星形花草本植物的根茎,一位天竺僧人将它献给了唐玄宗。仙茅又称“婆罗门参”,意思是说它在滋补健身、恢复元气方面的功能可以与人参相比。唐末或宋初,在中国种植了仙茅,到了十二世纪时,这种植物已经成功地移植到了广西。
22.
“乾陀木皮”这种药草见于李珣的记载,据李珣说,乾陀木皮“生西国,彼人用染僧褐,故名;乾陀,褐色也。……安南亦有”。“乾陀”这个名字很可能就是梵文“gandha”(香料)或者“kanthā”(百衲衣)的译音。在唐代,人们将乾陀木皮与酒一起煎服,用来“温腹暖胃”。
“黄屑”是安南贡献的土贡,可以作为黄色染料,还能够止咳,治疗腹疼。它显然是黄檀末或与此类似的一种东西。
“胡黄莲”生长在波斯沿海地区,它的根茎能够治疗肠道疾病和痔疮。胡黄莲究竟是一种什么植物,现在还没有定论。宋代时,这种植物就已经移植到了陕西和甘肃地区,但是现在似乎已经绝迹了。
23.
唐朝人将某种有毒的种子称为“鹤虱”。它是从包括波斯在内的西域传来的一种植物,外国人称之为“天鹅虱”。鹤虱可以用来驱虫和治疗各种溃疡以及肿瘤。
芦荟是从非洲多肉植物中提取出来的一种苦味的结晶。因为它“味苦如胆”,所以又被称为“象胆”。芦荟被用于治疗“小儿诸疳热”,据说芦荟产于波斯。
“雚菌”是生长在东海芦苇盐泽中的一种白蕈,雚菌与酒和服,可以治疗绦虫。
其他还有一些神秘而未知的药草,例如由北天竺和吐火罗的僧使带来供朝廷享用的那些无法考知的“胡药”,以及由那些研究外来药物的专家——如陈藏器、李珣等具列的药草等。在这些药草中,甚至有一种“带之令夫相爱”的“无风独摇草”。
毛粪石
24.
在中国,来源于动物的药物中还没有一种比毛粪石更有名。确切地说,毛粪石是在许多反刍动物的第四胃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山羊的第四胃中——发现的一种结石;作为一种解毒剂,毛粪石在近东地区享有盛誉。在中世纪中国,将“毛粪石”称作“牛黄”,但是当时中国所说的“牛黄”与毛粪石的经典定义往往是不相符合的。即使不是大多数,起码有一部分“牛黄”是从牛的胆囊中取出来的胆石,而不是胃里的结石。这种胆石在医疗中的作用与其说是物质的,倒不如说是精神的。据记载:“牛有黄者或吐弄之”,“尝有人得其所吐黄剖之,中有物如蝶飞去”。
25.
这种怪异的记载,其实不足为奇,因为还有记载称,牛黄确实具有“安魂定魄,辟邪魅,卒中恶”的功能。这种贵重的药材是中国本地的产品。大部分牛黄都出产于山东,作为土贡,山东的许多城镇每年都要向朝廷贡献牛黄,同时贡献的还有石器和可食用的软体动物。四川也出产一些牛黄。甚至像波斯这样遥远的地区也非常需要这种中国的“毛粪石”。在波斯地区,牛黄作为辟邪物和药物,很受人们的珍视。另一方面,唐朝也从新罗国得到了大量的牛黄;另外还有一些牛黄来自东北和南诏。上元二年(761),拔汗那向唐朝进贡了一种被称作“蛇黄”的、形状像龙一样的结石,这在当时必定引起过很大的震动。
腽肭
26.
在《本草纲目》中,保存了一段由李珣从古代地志中摘录的引文,在这段引文中描绘了一种叫作“腽肭”的朝鲜动物。据记载:
(腽肭兽)出东海中,状若鹿形,头似狗,长尾。每日出,即浮在水面。昆仑家以弓矢射之,取其外肾,阴干百日,味甘香美也。
所谓“外肾”,当然是指动物的睾丸。“昆仑家”则是“昆仑儿”的异称,指印度尼西亚人。此处提到的在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昆仑儿”很令人费解——除非它只是泛指“熟练的海上渔猎者”。这种叫“腽肭”的动物显然是某种“海豹”。如果我们将记载中的“长尾”当真的话,也有可能是指水獭。这种动物大多是在“新罗海内”捕得的。这种药与药草和酒服,可以治疗“鬼气尸疰,梦与鬼交”以及各种阳痿症。很可能海狸香和麝猫香也是以腽肭的名义买卖的,在唐代时,还没有将它们区别开来。
蚺蛇胆
27.
在真腊地区的诸城邑,游荡着一些专门猎取人的胆汁的可怕猎手,唐朝虽然没有这种以猎取人的胆汁为业的猎手,但是唐属安南的蚺蛇却必须为了京城医师的需要而献出它们的胆囊。这些爬行动物的胆囊也被普安(位于今贵州省)专门采集胆汁的人以同样的方式摘去。李珣仔细观察了南方的生活,他曾经目睹了每年五月五日“养蛇户”剥取蚺蛇胆的情形:
普安州有养蛇户,每年五月五日即担蚺蛇入府,祗候取胆。余曾亲见,皆于大笼之中,藉以软草,盘曲其上。两人舁归一条在地上,即以十数拐子从头翻其身,旋以拐子按之,不得转侧。即于腹上约其尺寸,用利刃决之。肝胆突出,即割下其胆,皆如鸭子大,暴干以备上供。却合内肝,以线缝合其疮口,即收入笼。或云舁归放川泽。
28.
段成式也听说过蚺蛇的传闻,他记录了一种更简单的捕蛇方法:
蚺蛇长十丈,尝吞鹿,鹿消尽,乃绕树,则腹中之骨穿鳞而出,养疮时,肪腴甚美。或以妇人衣投之,则蟠而不起。其胆上旬近头,中旬近心,下旬近尾。
在药市上的人往往用其他动物的胆冒充真正的蚺蛇胆,但是内行的药物学家有一种识别真假蚺蛇胆的方法:“试法,剔取粟许着净水中。浮游水上,回旋行走者为真”,而沉入水里的就是假货。一般情况下都是以猪胆和虎胆来冒充蚺蛇胆的。
蚺蛇胆在唐朝医药中的应用,将唐朝与印度支那联系了起来;在柬埔寨和其他地区,蚺蛇胆也在医药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唐朝医师用蚺蛇胆治疗“血痢,虫蛊下血”以及其他的疾病。
白蜡
29.
安南白蜡就是晒白的普通黄色蜜蜡。在唐代,甚至连这种白蜡也有医疗上的用途。据记载,“孕妇胎动,下血不绝欲死,以鸡子大煎(白蜡)三五沸,投美酒半升服,立瘥(一种巫术治疗法?);又主白发。镊去(白发),消蜡点孔中,即生黑者”。
人发
八世纪时,大量人发从东北和朝鲜送到了长安。读者可能对此会感到惊讶,究竟这些外国人的长发会有什么特殊的功效,使它们更胜过唐朝人的头发呢?除了巫医之外,这些头发是否还有其他的用途呢?相对来说,要探讨巫医使用头发的情形是比较容易的。对巫医而言,头发不仅具有很强的效力,而且还是很危险的药物。甄权的弟弟甄立言是与甄权齐名的医师,据唐史记载:“有道人心腹懑烦弥二岁,(立权)诊曰:‘腹有虫,误食发而然。’令饵雄黄一剂,少选,吐一蛇如拇,无目,烧之有发气,乃愈。”头发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变成了蛇。
30.
另据记载:
取生人发挂果树上,乌鸟不敢来食其实。又,人逃走,取其发于纬车上,却转之,则迷乱不知所适,此皆神化。
但是大多数与头发有关的药方,都与“自缢死,绳主颠狂”之类的药方属于同一类。当时之所以认为头发具有这样的功能,是因为人们认为头发具有束缚、捆系、紧紧缠绕的功能。如果“小儿惊啼”,用“乱油发烧研,乳汁或酒服少许,良”;如果成人“无故遗血”,则用“乱发及爪甲烧灰,酒服方寸匕”。
绿盐
31.
“绿盐”产于中亚焉耆地区和伊朗,同时也有从海上运来的绿盐。绿盐与天然的青铜碳酸盐即石青类似,而且也和石青一样,可以用来治疗眼疾。绿盐有时又称作“胆矾”,我们认为,它肯定是一种结晶状的硫酸铜,这是一种假想的治疗沙眼的药物。唐朝人用金属铜和醋配制出绿色的碱式碳酸铜,以作为绿盐的替代品。但是医师警告说:“以铜醋造者,不堪入药。”
(注:文中“?”“�”为生僻字或异体字,文档无法识别)
(第十一章 药物完结)
文章转载自网络
请尊重知识产权
侵权可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