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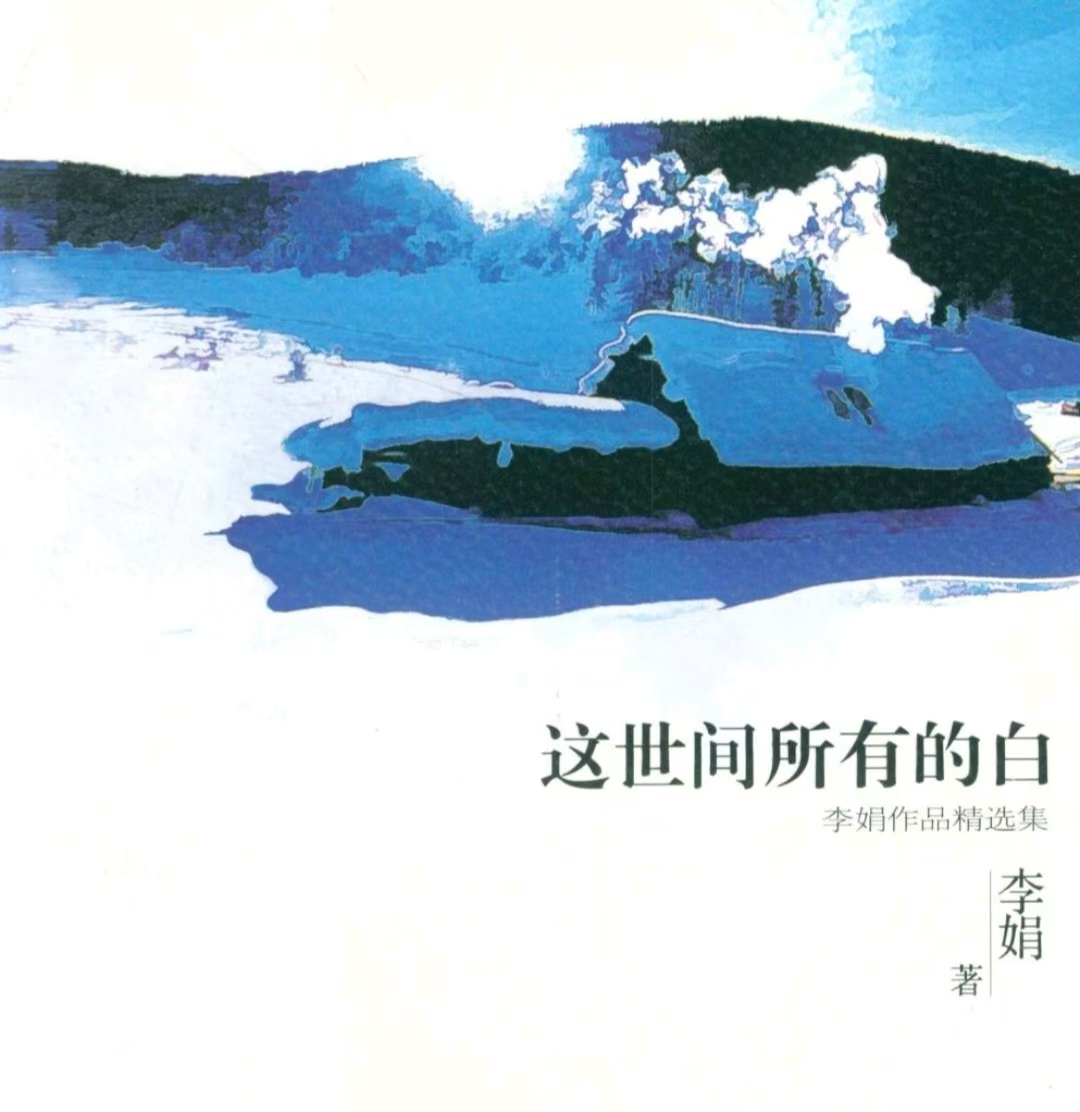
仅供习读,侵联立删。
1
要过不好不坏的生活
胡安西做了一张弓,听卡西说是用来射野鸽子的。但我只看到他用 来射老狗班班,而且走路的班班是射不中的,睡觉时倒能射中两三次。 班班被射中了也不会疼,于是便不理他,翻个身接着睡。
还射野鸽子呢,怎么看都没希望,就两股毛线拧弯一根柳条而已。 “箭”则是一根芨芨草。
我好说歹说才把弓借到手玩玩。瞄准班班后, 一拉弦,啪!—-箭 没射出去,弓给折断了。
我立刻沉着冷静地把断成两截的弓分别绕上毛线,这样, 一张大弓 立刻变成两张小弓,发给了胡安西和沙吾列兄弟俩一人一把。于是皆大 欢喜。两人分兵两路继续夹攻班班,班班还是不理他们。
2
后来才想起来:这荒茫茫的大地戈壁,哪儿来的柳条呢? 卡西说,是阿依横放羊路过爷爷家时,在河边折的。
爷爷家在吉尔阿特有现成的泥土房子住,就没有扎毡房了。房子修 在离我们驻地五公里处的北面山间谷地里,紧靠着额尔齐斯河南岸。
卡西说,爷爷家那边树多,不用拾牛粪,做饭全都烧柴火。意思 似乎是烧柴火是很体面的事情。但是看她的言行,似乎对牛粪也没什么 意见 。
我说,那为什么我们不搬到那边去?
卡西这啊那啊地努力解释了半天,也没能说明白。大概是与牛羊数 量有关的什么原因。
3
我们所在的春牧场是光秃秃的戈壁丘陵地带, 一棵树也不长的, 一小丛灌木都没有,最最高大的植物是芨芨草。取火的燃料也只有干 牛粪。牛真不容易,整天走很远很远的路,到处辛辛苦苦地找草吃, 到头来只是为了帮我们收集燃料似的。它们总是那么瘦,脊背和屁股 都尖尖的。
虽然比起冬天来说宽裕从容多了,但春天仍是紧巴巴的季节。好在 天气强有力地持续温暖着,青草在马不停蹄地生长。因水草稀薄,牛奶 产量比起冬天仍好不了多少,我们的茶水里很久都没添过牛奶了。日常 生活中省去了一早一晚挤牛奶这项劳动,时光基本上还算悠闲。扎克拜 妈妈三天两头和阿勒玛罕姐姐约着去额尔齐斯河南岸的亲戚家串门子, 家里总是只剩我和卡西带着两个孩子看家。
就是在这样的一天里,大人都不在家,一只黑色的羊羔死去了。 我问怎么死的。卡西淡淡地说不知道。
4
是啊,谁会知道呢?一只小羊羔最后时刻都感知到了什么样的痛 苦……之前我和卡西都不在,两个孩子在羊羔棚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 它。他们把它抱到家门口,蹲在它的面前,不停地抚摸它,目睹了它渐
渐死去的全过程。可是,他们什么也说不出来,等我俩发现时,羊羔已 经完全断气了。两个孩子仍然温和地摆弄着它,捧着它微睁着眼睛的小 脑袋,捏着它的小蹄子轻轻地拉扯,冲它喃喃低语。那情景,与其说把 它当成一件玩具在玩耍,不如说当作一个伙伴在安抚……又过了很久, 他俩仍围着小羊的尸体摆弄个不停,以为它很快会醒来。两张弓被扔在 远处一丛干枯的蓟草旁,静静并排搁在大地上。缠在弓上的玫红色毛线 那么鲜艳。
5
我很难过,此时乳房胀满乳汁的羊妈妈肯定还不知道已经永远失去 了宝宝。从今天黄昏到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将不停地寻找它。
但卡西没那个闲心难过,她开始准备烤馕。面早就揉好,已经醒了 一个多小时了。
我掐指一算,旧馕还有七八个,我们一家四口再吃三天才能吃得 完。等把旧馕吃完了,此时烤出来的新馕也相当遗憾地变成了旧馕…… 真是,为什么不缓一两天再烤呢。
刚烤出来的热乎乎香喷喷的馕不吃,却一定要吃旧的,真是令人伤 心。因为这样的话,生活中就一直只有旧馕可吃。
6
但再想一想,要是先吃新馕的话,当时是很享受啊。可旧馕又怎么 办?吃完新馕,旧馕就变得更坚硬更难下咽了,不吃的话又浪费粮食。 这好比把好日子全透支了,剩下的全是不好的日子。但如果能忍住诱 惑,就会始终过着不好不坏的日子。
那为什么不边打新馕边吃呢?因为那样的话,容易接不上茬。对 于动荡辛苦的游牧家庭来说,统统吃完后再临时打馕,有可能会使平 顺的日常生活出现手忙脚乱的情景。若有来客的话会更狼狈,让人笑
话——连现成的馕都没有,这日子怎能过成这样?这家女主人也太不会 经营打理了!
馕一次性就要烤够三四天的,如有招待客人的计划或即将搬家上 路,则会一口气打得更多,避免一切可能会应付不过来的突发情况。
7
在城里,街上卖的馕是用桶状的大馕坑烘烤出来的。烤馕师傅全 是男的,女的干不了那活,天大的一团面,只有男性的臂膀才揉得动。 揉好面后,扯下一小团面团抖啊抖啊,抖出中间带窝的圆形大饼,再粘 上芝麻粒和碎洋葱粒,然后俯身往馕坑边“啪!”地贴在馕坑壁上。整 个馕坑贴满面团后,就盖上大盖子烘烤。馕坑底部全是红红的煤炭。因 为馕是竖起来烤的,等取出后,每一只馕便都略呈水滴状:一端薄一端 厚。然后烤馕师傅轻松优美地给一个个馕表面抹上亮晶晶的清油,扔进 摊子上小山似的馕堆里,就有人源源不断去买啦。
生活在乡间的哈萨克农民也会在自家院子里砌馕坑烤馕,但现在大 多都使用烤箱了。烤箱一般镶在炉灶后的火墙上。等饭做好了,馕饼也 熟了。因为烤箱是方的,烤出的馕也是方的,像书,像一部部厚嘟嘟黄 艳艳的大部头。
8
在山野里烤馕的话,条件就简陋多了。但尽管条件有限,不好挑 剔,我还是对卡西这个小姑娘烤的馕很有意见。
盛面团用的破锡盆之前一直扔在火坑边用来装牛粪,早知道它的真 正用途是这个,我每天都会把它擦得亮锃锃的。
自然了,这只用途广泛的锡盆看上去很脏。卡西为了让它干净一 点,就反过来在石头上“哪哪哪!”磕了三下。然后,直接把刚揉好的新鲜面团扔了进去 ……
我以为她起码会用水浇一浇,再拿刷子抹布之类的用力擦洗。最次 也得拾根小棍,把盆底的泥块刮一刮啊 ……
但我闭了嘴一声不吭。如此这般烤出来的馕都吃了那么长时间了, 至少一次也没毒死过。连肚子疼都从没有过。
9
卡西先把牛粪堆点燃,烧一会儿后,把火堆四面扒开,将盛着面团 的锡盆放进火堆中间烧烫的空地上,再把四周烧红的牛粪聚拢环贴着锡 盆,最后在馕饼上盖一块皱皱巴巴的破铁皮——那是家里每天扫过地后 用来铲垃圾的简易簸箕……这回她连磕都没磕一下,盖上去的一刹那, 看到细密的土渣子从铁皮上自由地倾洒向洁白柔软的面饼。
她又把少许正在燃烧的牛粪放到铁皮上,因为方形的铁皮块实在太 小,锡盆又太大,只能勉强在盆沿上搁稳四个角,大大地露出四面的缝 隙,因此牛粪渣子不时豁豁啦啦漏进盆里 ……
加之卡西又不时地用铁钩揭起铁皮块查看下面的情形,于是场面更 加纷乱吓人 ……
10
虽然颇为惊恐,但站起身环顾四望时,我看到的是连绵起伏的荒山 野岭,看到寂静空旷的天空中, 一行大雁浩浩荡荡向西飞。与别的鸟儿 不同,雁群到来的情景简直可以说是“波澜壮阔”的,挟着无比巨大而 感人的力量。春天真的到来了。
放平视线,又看到我们孤独寂静的毡房,以及围裹着毡房的陈旧 褐毡和褪色的花带子。再看看四下,野地里除了碎石、尘土、刚冒出头 的青草茎和去年的干枯植被,再无一物。收回视线,看到卡西蹲在锡盆 边,浅黄色旧外套在这样的世界里明亮得扎眼,仅仅比她面前的火焰黯淡一些。这是一个多么小的小姑娘啊!……又看到死去的小羊静静横躺 在不远处。胡安西兄弟俩已经对它失去了兴趣,俩人又拾回小弓,追逐 好脾气的班班欢乐地游戏。最后低下头,透过锡盆和铁皮之间的缝隙, 看到面团一角已经轻轻镀上了一弯最美妙的食物才会呈现的金黄色。
11
这样的世界里会有什么样的脏东西呢?至少没有黑暗诡异的添加 剂,没有塑料包装纸,没有漫长周折的运输保存过程。面粉、水和盐 均匀地——如相拥熟睡一般——糅合在一起,然后一起与火相遇,在高 温中芳香地绽放、成熟……这荒野里会有什么肮脏之物呢?不过全是 泥土罢了,而无论什么都会变成泥土的。牛粪也罢,死去的小羊也罢。 火焰会抚平一切差异。没有火焰的地方,会有更为缓慢、耐心的一种燃 烧——那就是生长和死亡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在一点点降解着生命的突 兀尖锐之处。
总之,第一个馕非常圆满地成熟了,金黄的色泽分布均匀,香气喷 鼻。卡西把它取出来时,像刚才磕盆那样,在盆沿上也“哪哪哪”敲 了三下,于是馕饼上粘嵌的烧爛的黑色颗粒哗啦啦统统掉了下来。然后再 用抹布将其上上下下擦得油光发亮。最后拿进毡房,端端正正地靠着红色 的房架子立放。——多么完美的食物啊,完美得像十五的月亮一样!
12
浓烈而幸福的香气弥漫满室,进进出出都挣扎其中,扯心扯肺。
可是慢慢地,随着馕的凉却,那味儿也慢慢往回收敛、退守,最后 被紧紧地锁进了金黄色的外壳之中。只有掰开它,才能重新体会到那股 香味儿了。
再等两天的话,那香味又会随着馕的渐渐发硬而藏得更深更远。只 有缓慢认真地咀嚼才能触碰到——或是回想起——一点点……那种香气,就是那种当馕在刚刚出炉的辉煌时刻所喷薄的暴发户似的喜难自胜 的华美香气 … …
唉,真让人伤心。几乎从没吃过新鲜馕,却每天都得在新鲜馕的光 芒照耀下耐心地啃食黯淡平凡的旧馕。每到那时,我都会催促斯马胡力 多吃点。赶紧吃完眼下的旧馕,就可以稍微领略一点点新馕完全成为旧 馕之前的幸福滋味。
还有,新馕因为好吃,大家都会吃得多,连我也能一口气吃掉一整 个呢(直径30公分,厚6公分左右!)。那样的话,天天马不停蹄地烤 也不够吃啊。(2009)
13
涉江
搬家的头几天就开始收拾了,扎克拜妈妈将不常用的家什统统打 成包垛在空旷的坡顶上,毡房空了许多。搬家的头一天中午就拆去了毡 房。妈妈和我将所有家什器具归整一处,斯马胡力和卡西帕四处寻找放 养在外的马儿。傍晚时分,我和妈妈走遍了小山四周,把这段时间产生 的所有垃圾清理了一遍,凑作一堆烧掉。玻璃瓶之类烧不掉的东西就挖 坑深埋了,总之,大地之上不能留有任何阻碍青草生长的异物。
我很乐意做烧垃圾的事,因为可以烤火。沙尘暴过后,紧接着就是 寒流天气,大风又猛又冷。这是冬天结束时的最后一场寒流,这样的天 气至少得维持三到五天。我穿着羽绒服还裹着大衣, 一圈又一圈地缠着 围巾,埋怨地说:“头两天天气好的时候为什么不搬呢?”没人理我。
14
垃圾里大多是破衣服和破鞋子,缠有许多塑料包装物,还有两个塑 料盆,火势很猛,三四步之外就热浪滚滚,不能靠近。我在荒野里走来走 去,每拾到能燃烧的东西——干草束、马粪团之类——就赶紧走向火堆扔 进去,并不时冒着高温凑近火堆,用小棍扒拉一下,使之燃烧得更充分。
做这些时,脸烤得通红,头发都快烫焦了似的。但稍离开几步,又被浓重 的寒气袭裹了全身。太阳早已下山,旷野里仅存的明亮在这团火光的照耀 下如坠入大海深处一般遥远,这堆火焰像是从深厚的大地中直接喷薄而出 的,那么有力,那么热情。过了很久很久以后才熄灭,余烬仍耀眼地闪烁 在厚重的夜色中。那一处像是宝藏的大门开启了一道门缝。
没有毡房了,当天晚上我们只好挤在阿勒玛罕家的石头房子里睡 觉。大大小小八个人挤一张两米半宽的木榻,真够受的。
15
大家一直忙到夜里十一点才纷纷钻进被窝熄灯睡觉。我一想到只能 睡两三个小时,就很紧张,巴不得闭上眼睛就睡着。但胡安西和沙吾列 两个小家伙兴奋得不得了,觉得家里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又叫又跳, 好久以后才安静下来。
实际上扎克拜妈妈他们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凌晨一点大家就起来装 骆驼。我帮不上什么忙,便多睡了两个小时。凌晨三点,被阿勒玛罕推 醒,我摸黑从沙吾列身边爬起,里三层外三层套上全部的衣服,胖到胳 膊都放不下来为止。但还是觉得冷得要命。拎一拎暖瓶,昨晚剩下的茶 还有一点点,便给自己冲了满满一大碗喝了。茶水温吞吞的,喝完还是 没能暖和起来。
出去一看,大风呼啸,无星无月。东面黑乎乎的山那边有点亮光, 那是斯马胡力他们所在的地方。便低着头顶着大风,深一脚浅一脚地慢 慢摸去。走到山梁最高处时,风大得像是好几双手当胸推来似的,几乎 快要站立不稳了。眼睛被吹得生疼,直流泪水。
16
下了山慢慢走到近处,看到家里的太阳能灯泡挂在一把铁锨上,摇 摇晃晃,而铁锨插在大地上,笔直不动。灯光笼罩着十几步方圆的一团
颤动不已的小小世界,那个世界里只有妈妈他们三个,只有跪卧着等待 出发的骆驼和满地的大包小包。这个世界之外全是无边无际的黑暗。
谁也没有惊异我的出现。大家顶着大风神情严峻地干活,把一捆又 一捆巨大沉重的包裹箱笼架在驼峰两侧横绑的檩杆束或合起来的房架子 上,估计两边重量均衡了,再拉紧绳子,打结。打结时卡西和斯马胡力 隔着骆驼面对面拼命地拉扯绳头,为了能使上劲儿,两人都用脚紧紧蹬 着骆驼圆滚滚的肚皮。那骆驼沉默着,跪在中间一动不动,似乎明白这 一切意味着什么。
17
四点半,东方蒙蒙发白,四峰骆驼全部捆绑妥当。斯马胡力使劲踹 着它们的屁股,强迫它们站起来。我们的家,全都收拢在这四峰骆驼背 上了。骆驼一个连着一个,站在微明的天光里,冷冷清清。
我蒙着大头巾四处走动,检查有没有被遗漏的东西。这时阿依横别 克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他牵着我的马,那马儿也不知何时已装上了马鞍 和笼头。他扶我上了马(穿得太厚,腿都打不了弯了……)。出发了。
我握着缰绳坐在马上回头看,我们生活过的地方空空如也,只剩一 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圆形空地。我们一家人曾在那个圆圈里吃饭睡觉 的情形幻觉一般浮现了一下。
起程时天色也明朗多了,但离太阳升起还有一段漫长时光。才开 始,驼队进行得很慢很慢,羊群更慢。班班和怀特班前前后后地跑着, 只有它俩是喜悦的,虽然一直饿着肚子。
18
在北面山谷口开阔的空地上,驼队和羊群分开了。我、扎克拜妈妈 和斯马胡力领着驼队往北走,卡西一个人赶着羊群从东面绕了过去,东 面有吊桥。但驼队却能够涉水瞠过额尔齐斯河。驼队负重,得尽量让它
们抄近道。
我看着卡西孤独的金黄色棉衣越走越微弱,却永远不会消失似的, 那么倔犟。很久以后再扭头张望,那一点金黄色仍然不灭,在荒茫遥远 的山体间缓缓远去。
我们默默前行,天色越来越亮,风势渐渐小了。两个多小时后就 完全走出了吉尔阿特牧场的丘陵地带。又穿过一两个有许多白房子的村 庄后,抵达了额尔齐斯河南岸。驼队沿着冰雪铺积的河岸向东走了半个 小时后停下来,那一处水面最宽阔,水流较为平缓。斯马胡力找了一 处地方下了水,策马奔向河中心, 一路上马蹄踩破浮冰,溅起老高的水 花。但他还没到河中心就折转了回来,大声喊着:“可以!这里就可以 了!”招呼我们也下水。
19
这条最终汇入北冰洋的蓝色大河从东至西横亘眼前,寒气逼人。看 似平滑的一川碧玉,可我们都深知它挟天裹地的力量。上下游巨大的落 差造成湍急的流速,水流冲击力很大。
妈妈把骆驼之间连接的缰绳又整理了一遍,扣结打得既不能太松也 不能太紧。太松了一扯就脱开,会造成骆驼的失散。太紧的话, 一峰骆 驼被水冲走,其他的一时挣脱不得,会被统统拖走。
然后她牵着这串骆驼缓缓下水,跟在斯马胡力后面向对岸泅去。
斯马胡力在河水的轰鸣声中扭头冲我大喊:“李娟,你自己一个人 敢过来吗?”我赶紧连说了好几个“不”。他又大喊:“那等着吧!” 头也不回地去了。
20
我勒住马,停在河边冰层上,眼巴巴看着驼队分开激流,左摇右晃 地去向对岸。这边的世界只剩我一人了。天完全亮了。
不,和我在一起留在岸这边的还有怀特班。妈妈他们下水的时候, 老狗班班毫不犹豫也跳下冰层,跟在驼队后面缓慢游动,在浪花中只冒 出一个头来。而怀特班年龄小,从没经历过这种场面。它吓坏了,悲惨 地呜鸣着,几次跳下激流,又吓得赶紧跃上岸, 一个劲地冲水里的巴特 班吠呼。
但它回过头来,看到我还停留在岸这边,便赶紧靠拢过来,绕着我 呜咽,似乎我成了它唯一的安慰,唯一的保护人似的。后来就不叫了, 卧在我旁边,紧紧守着我。我掏了掏口袋,什么也没有,真想最后再给 它一点吃的啊。马上就要永远分别了,可它什么也不能知道,还以为虽 然离开了大家,好歹守住了我。
21
妈妈他们很久以后才靠岸,陆续上岸后,巴特班却还在河中央艰 难地向前游动,努力稳住身形不让水冲走。但我看到它明显地偏移了方 向,向着下游而去,眼看着离妈妈他们越来越远了……我想它可能力气 用尽,渐渐被河水冲走了。心提到了嗓子眼,忍不住大喊起来:“班 班!班班!”也不知道这样喊有什么意义,能帮上什么忙。好像它听到 了也会清醒过来,继续向前似的。
扎克拜妈妈顺着河岸向下游跑,似乎也在大声呼喊着班班。但水声 轰鸣,什么也听不到。终于,我看到它游到了河岸边的浅水处,水流在 那里回旋,水速减缓。于是班班一下子加快了速度,三下两下窜上了河 岸,激动地向妈妈奔去。然而到了近前又被妈妈喝止。妈妈不喜欢它的亲热举动。
这时斯马胡力骑着马下水返回,向我而来。
22
我轻轻对怀特班说:“你看巴特班多厉害!你比它年轻多了,腿又长,骨架子又大, 一定也能行的!”
怀特班眼睛明亮地看着我,因为对我所说的语言一无所知而显得分 外纯洁无辜。
很久后斯马胡力靠拢了,他接过我的缰绳,试着领我往前走。马儿 踩着水边的薄冰小心翼翼地下了水,浅水的晃动令人突然产生眩晕感。 我吓坏了,不知怎么的一下子把两只脚全缩了起来,抬到马背上夹住了 马脖子。斯马胡力大笑起来,安慰我不要怕,但我怎么可能不怕!水浅 的地方都这么吓人,待会到了水深的激流处,肯定会坐不稳掉下去的。 我死活不肯往前再走一步了。斯马胡力只好牵着我回到岸上,他上了我 的马,骑在我马鞍后面, 一手挽着我的缰绳, 一手牵着自己的空马,抱 着我似的继续前进。这下安心多了。
23
只是还在担心怀特班。回头看时,它绝望地在岸边来回走动,几次 伸出爪子试探着想下水,都缩了回去。没有希望了,我感觉到它没有希 望了。直到我们真的走远了,我又大喊了一声它的名字。它这才猛地冲 进水里,拼命向我们游来,我努力地扭头往后看,可惜这次同样没游多 远,这只笨狗又一次打了退堂鼓,连滚带爬回到岸上。亏它平时那么凶 狠的样子,肯定全部的胆量都用来咬班班了。
也可能并不是它胆小,是它了解自己的极限。它和巴特班体质不一 样,它只是一条普通的家狗,而巴特班可是牧羊犬品种。逞强只会让它 丧命……这可怕的寒冷的大水啊。它不愿意死去,又不愿意离开我们。 没有希望了。
24
没有家的狗最可怜,从此就成了野狗。如果在城市里,还能在垃 圾堆里扒寻些东西充饥。可这荒山野岭的,到哪里找吃的?今晚它睡在
哪里呢?会不会一个人孤独地回到我们扎过毡房的旧址上,坐在那里怀 着最后一线希望等待,但愿我们马上就会回到家,重新卸下骆驼,热热 闹闹扎起毡房,永远生活下去……夏天倒也罢了,饥饥饱饱都能扛得过 去。可冬天怎么办?冬天长达半年,它将带着委屈和不解死去……
又想到,要是刚才不顾一切把它抱在马背上的话……那不可能。妈妈 和斯马胡力肯定不会同意的。大家都认为狗是肮脏的,对一条狗示好的人 也令人讨厌。再说了,对于一条从没骑过马的狗来说,骑马的可怕程度恐 怕不亚于渡河。万一它搞不清怎么回事,行至河中央看到四面大水,本能 地挣扎起来的话,马一受惊,不只是它,我和斯马胡力也跟着完了。
25
刚才它要是跟着卡西帕的羊群从吊桥那边过来该多好!但是,就算 过了吊桥又能怎样?眼下的困难都不能克服的话,往后一路上还有那么 多的艰难险阻,它早晚也挨不过去的。可能这就是它的命运……
我胡思乱想着,不知不觉间快要接近河心了。河中央的风更猛于 两岸,更凉于其他地方。马浮在水中努力向前游动,我高高抬起两条腿 放在马背上,但裤子还是里里外外湿透一大片。但也顾不上许多了,我 们正处于最危险的地段。然而由于心怀对怀特班的悲伤,把惧意冲淡 了一些。我恍恍惚惚地往前看,眼前视野分成了两个世界,下半部是河 水,上半部是彼岸。彼岸广阔的风景正在持续向东推进,而河水则滚滚 向西流。两者错开的地方仿佛不是空间的错开而是时间的错开,奇异而 锋利,奇异而清澈。心里却还在明明白白地牵挂着怀特班,却已无力扭 头看一眼了。
26
眩晕感铺天盖地。斯马胡力,我们不是要过河吗?我们不是过河吗?为什么你却牵引着马逆流而上?我们的马头迎着波浪,分开 水流,分明在往上游进行。又好像马儿一动不动,只是大水迅速地经过了我们……我们为什么要逆流而上?我们不是要过河吗?……我糊涂起 来,却又不能开口说一句话。时间无比漫长,我们不停地向上游行进, 同时又一直停留在原地,像被困在了河中心。四面波涛滚滚。又那么 冷,那么冷。但冷已经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没有希望,真的没有希望 了 ……
直到终于接近对岸的时候,才猛地清醒过来!刚才的幻觉一下全部 消失。突然看清流动的只有河水,对岸广阔的风景一动不动,深深地静止着 。
原来渡河的时候,有一个常识,就是不能看着河水,要往远处看, 否则会失去参照物的。
27
斯马胡力一直盯着对岸的驼队前行,无论水怎么 流都不改变方向,所以走的是准确的直线距离。而我一会儿看水, 一会 儿看远方,目光游离,心神不宁,所以才有迎着逆流往上走的错觉。
而班班刚才肯定也产生了同样的错觉。它毕竟是条狗,身子小,淹 没水里后,没法看到对岸,只能凭本能逐波向前,所以在水里划出长长 的斜线兜了远路。我还以为它是被水冲到下游的呢!
全都过了河后,斯马胡力又检查了一遍驼队。妈妈冲着对岸呼唤着 怀特班,一遍又一遍,喊了许久。
我们再次整装起程后,沿着河岸向西走了许久。在河的对岸,怀特 班也在往西跑动,不时停下来隔江遥望、吠叫。它还以为它仍然是和我 们在一起的。直到我们在岔路口拐弯向北,才永远地分离。我不敢回头 看了。这时候,风又猛烈起来,冰冷的太阳高高升起。
(2009)
28
和卡西帕的交流
在我仅仅只会说单个的一些哈萨克单词——如“米”啊“面”啊, “牛”啊“羊”啊,“树”啊“水”啊之类的时候,和大家的交流之 中真是充满了深崖峭壁、险水暗礁。往往一席话说下来,大家越来越沉 默,你看我,我看你,眼神惊疑不定。我总是在给大家带来五花八门的 误 会 。
虽然长年生活在哈萨克地区,但由于家里是开杂货店和裁缝店 的,我与大家的生活交流仅限于讨价还价。除了记住全部商品的名称 及其简单的功用介绍之外,能比较完整地连成一句话说的哈萨克语几 乎只有以下这些:
——不行,不能再便宜了!就这个价!
——裙子已经做好了,但是还没有熨,请稍等五分钟。
——厚的裤袜刚卖完,三四天后会进货。
——可以试裤子,但得先脱掉你的鞋子。
29
刚开始介入扎克拜妈妈一家生活的时候,真是非常高兴。因为全 家人几乎一句汉语也不会,这下总可以跟着实实在在地学到好多哈萨克 语了吧?
结果到头来,自己还是停留在原先的水平,倒是妈妈他们跟着我实 实在在学到了好多汉语。
最初,我教给卡西的第一句话是:“我爱你。”
后来卡西又向我深刻地学到了一句口头禅:“可怜的。” 于是她总是不停地对我说:“可怜的李娟,我爱你!”
虽然从不曾具体地教过扎克拜妈妈一句汉语,但她很快也会熟练地 使用“我爱你”了。
一大早就会听到她快乐地说:“李娟,我爱你。茶好了吗?” 妈妈说的最熟练的两句汉话: 一、李娟谢谢你!二、李娟,桶!
30
前者是每天临睡前我为她捶了背之后。后者则在挤牛奶时,牛奶满 了一桶该换另一只桶了。
而全家人都说得最顺溜的一句汉语则是:“对不起!”
——大概因为我一天到晚总是在不停地说这句话。不知道为什么, 我整天不停地在做错事。
全家人里收获最大的是卡西,她足足记录了一整个本子的日常用 语。可一旦离开那个本子,她就一句话也应用不了,和我说话时,总是 一边嗯嗯啊啊地“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一边紧张地翻本子,指望能 找出一个最恰如其分的字眼。糟糕的是,她是随手记录的,也没编索 引。我一直打算买一本《哈汉词典》送给她。
相比之下,我就聪明多了。我最厉害的一次表达是试图告诉卡西自 己头一天晚上梦到了胡安西。 ——相当艰难。因为当时我所掌握的相关 单词只有“睡觉”、“昨晚”和“有”。至于如何完成这三个词之间的 联系与填充,跟小学生解答三角函数一样惶惶然。结果,我成功了 …… 接下来,我们俩都学会了“梦”这个单词的汉哈发音,并开始交流这个 词的其他用法。
31
我一直努力使用哈萨克语和大家交流,可这种努力每每被卡西破坏 掉,因为她也一直在努力使用汉语和我说话。
她要是说哈萨克语的话,我就算听不明白,好歹还能猜到些什么, 但要说汉语的话,我就彻底搞不清了。
总之,和卡西的交流在大部分时候都是失败的。好在那也算不上什 么惨痛的事情。顶多那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冥思苦想,最后两手一 拍:“走吧走吧,还是放羊去吧!”结束得干净利落。
卡西随身带着一本哈萨克语学校初中第三册的汉语课本。课本最 后附有数百个单词对照表,发音、意义、属性倒是一目了然,但大都 是没啥用处,如“钦差大臣”,如“拖鞋”,如“显微镜”,如“政治 犯”。真是的,游牧生活中怎么会用到拖鞋呢?难怪卡西上了这么多年 学,啥也没学到。
32
不过老实说,从我这里,似乎她也没学到什么像样的 ……
很多时候我嫌麻烦,教一个“脸”字吧,半天都发不准音,于是 改口教她“面”。“眉毛”两个字她总是记不住,便让她只记“眉” 一个字。
她怀疑地问:“都一样吗?”
我说:“当然一样了!”其实本来也是一样的嘛,只不过 ……
很长一段时间,卡西学得非常刻苦。每当她从我这里又学会了什么 新词汇,立刻如获至宝地记在小本子的空白处。
我说:“一天学会五个单词的话, 一个月后卡西就很厉害啦!”
她掐指一算,说:“不,我要一天学会二十个,这样一个星期就可 以很厉害了!”
我很赞赏她的志气,却暗自思忖:既然这么爱学习,上学的时候 都在干什么呢?好歹也读了八年的书啊,怎么就啥也没学到?……我看 过卡西的一张初二课程表,几乎每天都安排有汉语课,而本民族的语文 课,一星期却总共就四节。
33
那个记录单词的小本子她从不离身, 一有空就背啊背啊,嘴里默 念个不停:“香皂、肥皂、阴天、晴天、穿衣、穿鞋……”连傍晚赶 羊回家那一会儿工夫也不忘带上, 一边吆喝, 一边冲羊群扔石头, 一 边掏出书来低头迅速看一眼。去邻居家串门子也带着,聊一会儿天, 背一会儿书。
妈妈看她这么努力,感到很有趣。两人在赶羊回家的途中,会不停地考她。
妈妈指着自己的眼睛问:“这是什么?”
卡西响亮自信地回答:“目!” 又指着嘴:“这个?”
“口!”
再指指对面的森林。
“木!”
如果卡西帕将来放一辈子羊的话,最好不过。否则,操着从我这 里辛辛苦苦学到的本领(正确但没啥用处的本领)出去混世界……不堪设想 。
34
有一次看到小加依娜脖子上挂着一枚小小的牙齿,就问那是什么的 牙。其实也是随口一问,但海拉提和卡西两个却很慎重地凑到一起商量 了半天,最后她用汉语回答道:“老虎。”
我吓了一大跳,便用哈萨克语问道:“不对吧,你是想说 ‘ 狼 ' 吧 ? ”
“对对对!”卡西连忙点头。
接下来,我教会他们汉语里“狼”的正确发音。
然而,海拉提却又问道:“那‘老虎'是什么?”
话刚落音,卡西立刻坐直了,准备抢先下结论。刚一开口我就喝止 了她。虽说大胆发表意见是好事,但这个家伙也太没谱了。
可是关于老虎的问题,我自己也实在无法解释……这时,突然 看到海拉提家的小猫从旁边经过,灵光一闪,就说:“老虎就是很 大的猫!"
35
两人愣了一秒钟,卡西立刻恍然大悟状,连忙对海拉提说:“阿 尤,她是在说阿尤!”
我一听,什么嘛!“阿尤”是大棕熊!两码事嘛。但又不好解释, 毕竟说熊是只大猫也没错……再看看他俩那么兴奋的样子,大有“终于
明白了”的成就感,只好缄默。唉,错就错下去呗,幸好新疆是没有老 虎的,保管他们一辈子也没机会用上这个词 ……
后来的好几天里卡西一有空就念念有词:“老虎,阿尤,阿尤,老 虎 …… ”——把它牢牢记在了心里。真愧疚。
较之我的阴险,卡西的混乱更令人抓狂。
记得第一次和卡西正式交谈时,我问她兄弟姐妹共几人。她细细 盘算了好久,认真地问答说有四个,上面还有一个十九岁的姐姐阿娜尔 罕,还有两个哥哥。
36
当时可可还没有离开这个家庭。我看他还很年轻,就问:“可可是 最小的哥哥吗?”
她确凿地说:“是。” 我又问,可可结婚了吗? 同样的确凿:“是。”
结果,第二天, 一个妇女拖着两个孩子来家里喝茶。她向我介绍 道:“这是我的大姐姐!”
我说:“那么你是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是吗?” 她极肯定地称是。
我又强调地问道:“那么妈妈一共五个孩子?只有五个孩子?” 她掰着指头算了一遍,再一次点头确认。
又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一个年轻一点的女性抱着孩子跟着丈夫来拜 访。卡西再次认真地介绍:“这是第二个姐姐。”
天啦!—— “那妈妈到底有几个孩子啊?”
“ 六 个 。 ”
后来可可回到了戈壁滩上,斯马胡力接替他来放羊。我一看,斯马 胡力怎么看都比可可年轻多了,不像是老大。一问之下,才二十岁呢。 私下飞快地计算一番:就算弟弟可可只比斯马胡力小一岁,也只有十九 岁,十九岁的年纪上就结婚三年,媳妇怀两次孕了?大大的不对头!于 是我就逮着这姑娘盘问:“你好好地和我说,他们俩到底谁大啊?”
37
卡西反倒莫名其妙地看着我说:“当然可可大了,可可都结婚了, 斯马胡力还没结婚嘛!”反倒认为我是个傻瓜。
有一次卡西想问我妈有多大年纪,为此真是煞费苦心。问之前酝酿 了足足一分钟之久才慎重地开口:“李娟,你知道的嘛,我的,那个, 今年的十五,就是十五的那个的那个,对吗?”
我想她是在说她今年十五岁了,于是回答:“对。”
她又说:“我的妈妈,四十八,知道吗?” “ 知 道 。 ”
“那个,斯马胡力,二十,那个。对吧?” “对。”
“好——”她一拍巴掌,“那么,那你的妈妈?也是那个的那 个呢?”
我云里雾里。
她又指天画地拉七扯八解释了老半天。最后,我试着用哈萨克语问 道:“你是想问我妈妈有多大年纪对吧?”
她大喜,也用哈萨克语飞快地说:“对对!那她多大年纪了?”
38
我还没回过神来,斯马胡力和扎克拜妈妈已经笑倒在花毡上。
接下来她又想告诉我,她的外婆活到九十九岁过世。但她只知道 “九”这个单词汉语怎么说,却不会说“九十九”。她为此再次绞尽 了脑汁,最后一塌糊涂地开了口:“我的,妈妈的妈妈嘛,九九的九九 嘛,死了!”
“九九的九九?”我想了想,用哈萨克语问她:“是‘九月九日’ 还是‘九十九'?”
她说是九十九。
我又问:“什么九十九啊?”
于是她还得告诉我那个“岁”字,又陷入了一轮艰难跋涉之中:
“李娟,你知道,我,十五,那个;斯马胡力,二十,也是那个; 我的妈妈嘛,四十八,你知道那个嘛!我的妈妈的妈妈嘛,九十九的, 那个——那个是什么?”
我用哈萨克语说:“你是说九十九岁吗?”
大家又笑翻一场。
39
尽管如此,很长一段时期内,她坚持用鬼都扯不清的汉语和我交 流,不会说的地方统统用“这个”、“那个”或“哎呀”填补之。好在 之前有说过,我聪明嘛,又在一起生活久了,猜也猜得到她在什么样的 情况下要说什么样的话。
于是,大家都叫她“乱七八糟的卡西”。
老实说,其实卡西也有许多厉害的表达。比如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 上花毡不脱鞋子,多脏啊,她用哈萨克语回答了句什么我没听懂,于是
她又飞快地用汉语说道:“脚不香!” ……
“香”是前不久刚教会给她的,她很喜欢使用这个词。我们走进森 林时,她会幸福地自言自语:“香啊 …… ”
每当饭做好了揭开锅盖时,她也会大喝一声:“香!”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