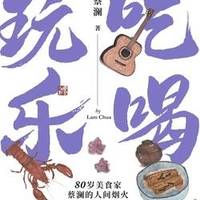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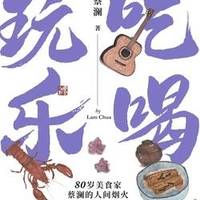
生活散文 之 吃喝玩乐:蔡澜的人间烟火06
第三章 奇人异士录
有些老友,忽然间想起,特别思念过往相处的一段时光。
染发膏
01
早上,到九龙城街市熟食档吃早餐,有人打招呼,转头一看,不是曾江是谁?好久没遇到他,不过在电视中天天见面,他们的染发膏广告,那么多年来,还是照放。
“第一次播是在什么地方?”我问。
“在戏院里。”他说,“当年只有丽的呼声的黑白电视,哪有彩色的?”
“你记得那时候的广告都是些什么吗?”
曾江说:“像好立克、阿华田等,都很硬销,像人人搬屋那样喊口号,用的都是临时演员,我是第一个所谓的名人。”
“谁替你接的?”
“那年代哪有什么经理人?代理商叫我上他们的公司谈,反正没拍过,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
“给了多少钱?”
“几千块罢了。”
02
“那时候几万块就可以买一层楼。”我说,“再也没给过钱吗?”
“代理会说签合同时写明广告是永远用的,没有年限,所以没有义务再给钱。如果我要用染发膏,可以免费赠送,哈哈哈。”
“当年你多少岁?”我问。
“二十岁,不到三十。”曾江说,“是一个美好的年代。”
“广告那么多年来没有改过?”我问。
“改过,后来又重新配了一次音,人也变了。”
“你没变呀!”我说。
“我没变,但是身边的那两个女人变了。当年的发型与服装都已不合时宜,用特技把原来那两个女人换掉了。”
我说:“你现在更好看,一头灰发。”
曾江大笑:“所以我没向他们要染发膏呀。”
倪匡减肥法
03
写稿写到清晨四点,打电话给倪匡兄。
“哈哈哈哈,”他问,“你们那边三更半夜了,怎么还不睡?”
“明天带团出发,可以在飞机上睡,空姐怎么叫也叫不醒我。你们呢,现在几点?”
“现在下午一点,怎么那么久没听到你的声音?”
“上次倪太来香港,我一直要请她吃饭,最后还是吃不成,真不好意思。”
“你不必不好意思,她现在又去了,剩下我一个人在旧金山。”
“吃东西呢?”
“我昨天只吃一餐。”倪匡兄说。
“那有没有比从前瘦一点?”
“没有,还是一身赘肉。”
我最近不那么胖,人家问我用什么减肥法,我回答说是“倪匡减肥法”。倪匡兄说过不吃就瘦。现在听倪匡兄自己说来,好像倪匡减肥法也不管用了。
04
“那一餐吃了些什么东西?”我问。
“烤羊腿呀。买了一只四五磅重去骨的,四百五十度火,烤个四十五分钟就可以半生不熟地吃,真美味。把那些羊油拿来炒青菜,不知多香!”
“用刀子把羊腿插几个洞,塞进蒜头,烤了更香。”我说。
“那么麻烦干什么?”他反问,“羊肉是所有肉类之中最好吃的了,怎么烤都行。”
“不怕膻?”
“羊膻了才好,广东人最古怪了,说这碟羊肉不膻,味道不错。哈哈哈哈,这是什么道理?不膻吃来干什么?”
我也赞同。四五磅的肉,怪不得一天吃一餐,也照样发胖。
故事
05
半夜和倪匡兄通电话。
“哈哈哈哈,”他大笑四声后说,“最近常看你改写的《新聊斋》,真过瘾。”
“也不是改写,只借它的精神。”我说。
“我小时候也是最爱读《聊斋志异》的。”倪匡兄回忆,“那么多篇东西,篇篇精彩,不管是长的还是短的。”
“蒲老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我赞同。
“对。”倪匡兄愈说愈兴奋,“有了故事,人物才突出。我们写的,都依照这个传统。年轻人总爱描写人物,以为说故事是老土。但是要想写出一篇故事感强的文章,难如登天,是他们想不出罢了,哈哈哈哈。”
“编故事的确真不容易,写得好、说得好也要有天分,加上后天的努力。从前在电影公司做事,导演想开戏,需要说一个故事给老板听,没想到大多数导演连一个简单的故事也说不清楚,怎么拍呢?所以你老兄的剧本那么受欢迎,导演说用你的剧本,老板都有信心。”
06
“我写的剧本看上去很快就能看完,但是导演不一定拍得出,哈哈哈哈。”倪匡兄又笑。
记得当年邵氏开戏,一有卖钱的题材,就约倪匡兄吃饭,并把主意告诉他。倪匡兄即刻如数家珍地提供种种资料,让投资者增强了信心。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记忆力那么好,说什么懂什么。
“看书呀!”他说,“书看多了,什么都会,什么都那么简单。”
我也读书,就是记不住。认识的几位朋友,记忆力最好的是金庸先生和他。胡金铨兄的记忆力亦佳,可惜少写作,他记的都是与导演手法有关的东西。
但是记忆力好不好是一回事,先要看肯不肯听别人说故事。有些人只是说,从来不听,一辈子说不出一个好故事。
何藩
07
有些老友,忽然间想起,特别思念过往相处的一段时光。何藩,你好吗?
让我洗刷记忆吧,何藩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国际摄影比赛中连续得奖二百六十七次的人,曾被选为博学会士及世界摄影十杰多回,曾著有《街头摄影丛谈》《现代摄影欣赏》诸书。
当年,阳光射成线条的香港石板街、菜市、食肆,皆为他的题材。虽然以后的摄影家们笑称这类图片皆为“泥中木舟”的样板,但当年不少游客都被何藩的黑白照吸引而来,旅游局应发一个奖给他。
硬照摄影师总有一个当电影导演的梦,何藩也不例外。一九七〇年他拍摄实验电影《离》,获英国宾巴利国际影展最佳电影。
08
之前,他已加入影坛,当时最大的电影公司有邵氏和电懋,他进了前者,在《燕子盗》一片当场记。影棚的人看他长得白白净净,做演员更好,就叫他扮演妖怪都想吃的唐僧。一共拍了《西游记》《铁扇公主》和《盘丝洞》数片。
他还是想当导演,一九七二年导演首部作品《血爱》之后,以执导唯美派电影及文艺片见称。
何藩每次见人,脸上都充满阳光式的微笑,和他一块谈题材,表情即刻变严肃,皱起八字眉,用手比画,像是一幅幅的构图和画面已在他心中出现,非常好玩。
也从来没见过脾气那么好的导演,他从不发火,温温吞吞,公司给什么拍什么,一到了现场,他就兴奋。
09
有多少钱制作他都能接受,他以外国人说的“鞋带一般的预算”,在一九七五年拍了一部叫《长发姑娘》的戏,赚个盆满钵满。
所用的主角丹娜,是一位面貌平庸的女子,但何藩在造型上有他的一套。叫丹娜把皮肤晒得黝黑,加一个爆炸型的发型,与清汤挂面似的长发印象完全相反。她又能脱,实在吸引不少年轻影迷。
何藩已移民国外,听说子孙成群。不知近况如何,甚思念。
丁雄泉先生
10
爱上丁雄泉先生的画,只因为被鲜艳的色彩所感染。
我认为短暂的人生没什么意思,若无花草树木,这个世界并非一个迪士尼乐园,没那么美好。愈是单调的生活环境,人们愈喜欢色彩。到西藏去就感觉得到,人的服装,又红又鲜,不像泥土那么灰暗。智利山上的农民,服装亦同。丁雄泉先生没有受过正统的绘画训练,当我要求向他学画时,他说:“画画谁都会,小孩子一开始就画洋娃娃、房子、花,或是他们的父母,问题是敢不敢用大胆的彩色。我能教你的,也只是色彩的观念。”
从此,在他的画室中,我们研究红、黄、绿、紫的搭配与调和。有时,他会把一张白描的人物画拿出来,让我上色。看过之后,他又添几笔,整幅画便活了起来。
我不贪心,知道永远成不了画家,精神负担就减轻了,胆子也跟着变大了。常蘸了色彩,泼墨般涂下去。
11
他儿子告诉过我:“爸爸一向珍惜他的作品,我从来没有看过他让人那么乱来的。
丁先生为了鼓励我,在那些已经被幼稚技巧弄坏的画上题字,说是两人合作,令我又感激又惭愧。
从来也没想过独创一格,能模仿到丁先生一点一滴,已经满足,做他的徒子徒孙,好过自称什么大师。当然,我画出来的东西,有丁先生的影子。
这次到欧洲,从法国乘火车驶往伦敦时,我提着的行李,也画上了鹦鹉和猫。在巴黎车站,有个女的忽然冲上前与我拥抱,我愕然时听到她大叫:“Mr. Walasse Ting(丁雄泉先生)!”
原来,她把我误认为丁雄泉先生。我的脸涨得通红,连忙解释。虽然对不起丁先生,但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成就感,永远感激他老人家对我的教导和爱护。
苏美璐
12
常为我的文章画插图的人,叫苏美璐,是位不食烟火的女孩子。
样子极为清秀,披长发,不施脂粉,个高,着平底布鞋。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之间产生了很强的默契,每次看到她的作品,都给我意外的惊喜。
我写了墨西哥的一位侍者,她没见过这个人,但依文字,画出来的样子像得不得了,我拿给一起去墨西哥拍外景的工作人员看,他们都把侍者的名字喊了出来。
画我的时候,她喜欢强调我的双颊,样子十分卡通,但把神情抓得牢牢。
办公室中留着她的一幅画,是家父去世后我向诸友鞠躬致谢的造型。全幅画只用黑白线条,我把画裱了,将旧黄色和尚袋剪了一小块下来,贴在画上,只能说是画蛇添足,但很有味道。
13
写倪匡的时候,她为我画了两张,其中之一:倪匡身穿“踢死兔”晚礼服,长了一条很长的狐狸尾巴。倪匡看了很喜欢,说文字虽佳,插图更美,要我向苏美璐讨了,现在挂在他旧金山家中的书房。
时常有读者来信询问美璐的地址,要向她买画。美璐对自己的作品似关心不关心,画完了交给杂志社,从来不把原稿留下,倪匡的那两张,她居然叫我自己向杂志社要。
美璐偶尔也替《时代周刊》和国泰航空的杂志画插图,今年国泰航空赠送的日历,是她的作品。
而美璐为什么住大屿山?她说生活简单,房租便宜,微少的收入,也够吃够住的了。
到年底,她与夫婿要搬回英国,我将失去一位好朋友。虽未到时候,人已惆怅。
埋葬
14
苏美璐抗拒了计算机多年,终于屈服,最近装了一台。
目的是想把她的作品扫描后传到香港。至今为止,都是我写了文章,传真给她,她看了即刻画插图,最后用DHL寄回来。
如果能够逼真地用计算机传来,这中间缩短和节省了多少时间和金钱?
她有这个意识多多少少受了我的影响,她认为我这个老头儿都学会了,她自己不可能不懂,只是思想上抗拒罢了。
效果如何,还没有定论。苏美璐把画传来,同时也照用快速邮递。她还要看看周刊的美术指导认为插图合不合格,再下定论。
艺术家们对作品要求甚高,对色彩一丝不苟,如果失真,就难过自己那一关,不像我们凡人,得过且过。
15
起初她电邮了我数次,都没有收到,后来才联络上。我也在计算机上回复她,她也没音讯,只好用传统方法传真讯问。
多年来,我们一直用传真联络,除了和工作无关的柴米油盐,什么都谈。她传真说备了一个档案,我的信件已堆积如山,如果现在改用计算机联络,是否表示一个时代的终结?
我回答说反正也不是什么文学作品,用任何方式都一样。而且,最重要的是日久之后,传真纸便逐渐消失,鼓励她还是用电邮好一点。
终于,我们用电邮联络上。她需要些资料作插图参考,我告诉她Google(谷歌浏览器)的网址,她发现了这个挖不尽的宝藏后,和她先生两人欣喜若狂,再也不那么憎恨计算机了。
这时,她的传真机忽然终止了一切功能,完全不能修理,她问我它是不是死去了?怎么办?
“在花园挖一个洞,将它埋了。”我说。虽然没有看到她的表情,我想她在首肯。
笑儿
16
阿明很乖,脸上一直挂着笑容。
记得她刚出生时,苏美璐曾经来信形容这个孩子,从来不哭。当年我正在写一系列的鬼故事,参考《聊斋志异》重新创作,读到书中的一个人物,就向苏美璐建议:“中文名阿明,字笑儿。”
父亲Ron Sandford,起初我不知中文名字的写法,就译了一个“朗沙福”,反正清宫中有一个意大利画家名叫郎世宁嘛。虽然Ron Sandford是苏格兰人,对我们来讲,老外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苏美璐来信更正,说中文名应该叫为“乐山夫”,是画家黄永光先生为他取的。好,即刻重写画展海报上的字。
中国人的姓名中间那个字,是用来表示辈分,从前我的名字之中有个字,发音与长辈相似,也要被改掉。现在这一家人,父女中间共享一个“山”,变成了同辈,犯了大忌。老外嘛,也无所谓了。
17
这几天,笑儿手上有件行李,那是送巧克力给她时的那个纸袋,内容已吃完,装进去的是一只布熊。小孩子,总有一两样不离身的东西,像莱纳斯的那条棉被一样。
这个纸袋一旦被拿走了,阿明就会大发脾气。我一看,马上带她去买冰激凌,雪糕一到手,笑儿不哭了。
她父亲说:“冰激凌,是小孩子的货币。”我对钱没什么观念,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笑儿在香港玩得高兴,忽然脸色又不对,向父母说:“我要回去。”
“请司机送她回酒店吧。”我说。
她父母说:“阿明要回的是Shetland(设得兰群岛)。”
那可得花三天时间,又带她去买雪糕。苏美璐说:“冰激凌,是小孩子的酒精。”这次我完全听懂了。
何嘉丽
18
电台名DJ(音乐节目主持人)何嘉丽,最近常跟我的旅行团到处跑。
嘉嘉工作之后打的几份工都是高薪,最近被挖去另一个大机构做事,更是如鱼得水,每逢假期就带妈妈旅行,充满孝心。
口齿伶俐是当然的,嘉嘉当年还出过几张畅销唱片,记忆犹新。
那首《夜温柔》,非常难唱,就算是歌喉好的人,也记不住歌词,不敢在卡拉OK中乱点这首歌。
《夜温柔》是我监制的一部叫《群莺乱舞》的电影中的主题曲,从那个时候认识她。
19
到现在还有很多听众怀念嘉嘉当年主持的电台节目《三个小神仙》。后来,她和我也合作过一个深夜的节目,叫《最紧要系好玩》。
从小木讷的我,没想到能在电台上出现,经过她多番的鼓励和训练,后来连电视也上了,嘉嘉能称得上是我的老师。
从年轻人身上,我学到很多,尤其现在的计算机,不向他们学习经验是不行的。曾经想拜师尊子,请他教我画漫画,那么去了语言不通的国家,如俄罗斯,也可以用漫画来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可惜大家事忙,挤不出时间来完成这个愿望。
20
目前我还在香港电台“客串”一个环节,于星期一早上九点二十分通话,向香港各位报告我的一些行踪。
星期一又到,我们的旅行团正向淡路岛出发,去看万国花卉博览会,电话响了。
和主持人聊了两句,就交给嘉嘉去讲,让她和疏远已久的听众打招呼。
电话中,主持人问:“蔡澜老去日本,不厌烦吗?”
嘉嘉说:“我们当团员的老跟也不厌烦,蔡澜当然不厌烦了。”
陈小姐
21
第一次遇到陈宝珠小姐本人。
何太太来吃越南食物,和她一起到九龙城的“金宝越南餐厅”去,我做陪客。
陈小姐温文尔雅,名副其实的淑女一名,样子还是那么美丽。
人生总要进入的阶段,陈小姐的也来到了,她给我的感觉只能用英文的“graceful”来形容,字典上这个词译为“优雅的、合度的”,都不够形容她。
前几天晚上,我们一班人吃饭时也讨论过“grace”这个词,研究了它与宗教的关系——是上帝的恩典。“a state of grace”更是上帝恩宠的状态。如果译作中文的“天赐”,也俗了一点。
22
餐厅吴老板要求与陈小姐合照,作为私人珍藏,由我抓相机。拍后我也不服输,和她一起拍了一张,大叫:“发达啰!”
饭后驱车到花墟散步,陈小姐没有来过,处处感到新奇,花名问了又问。
“这是什么?”她指一堆植物问。
“猪笼草。”我说,“由荷兰进口,改了一个‘猪笼入水’的名字,卖得很好。”
“香港人真会做生意。”她说。
这时,出现了一位中年妇女,兴奋地叫“宝珠姐”。陈小姐转身一看,即认得她,向我说:“是我的影迷。”
23 杀青段
影像即刻出现了,是两帮人大打出手的回忆。
陈小姐问她:“今年多少岁了?”
“四十七。”她含羞地回答。
“姐姐呢?”陈小姐还记得。中年妇女即刻用手提电话联络。陈小姐亲切地和她谈了几句,收线后告诉我“姐姐”当年更是疯狂。
中年妇女还讲了一个秘密,原来陈小姐是懂得种花的,但她一直没提起。
“叫我宝珠,或英文名字。”她向我说。
我微笑不语。叫陈小姐,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她永远是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