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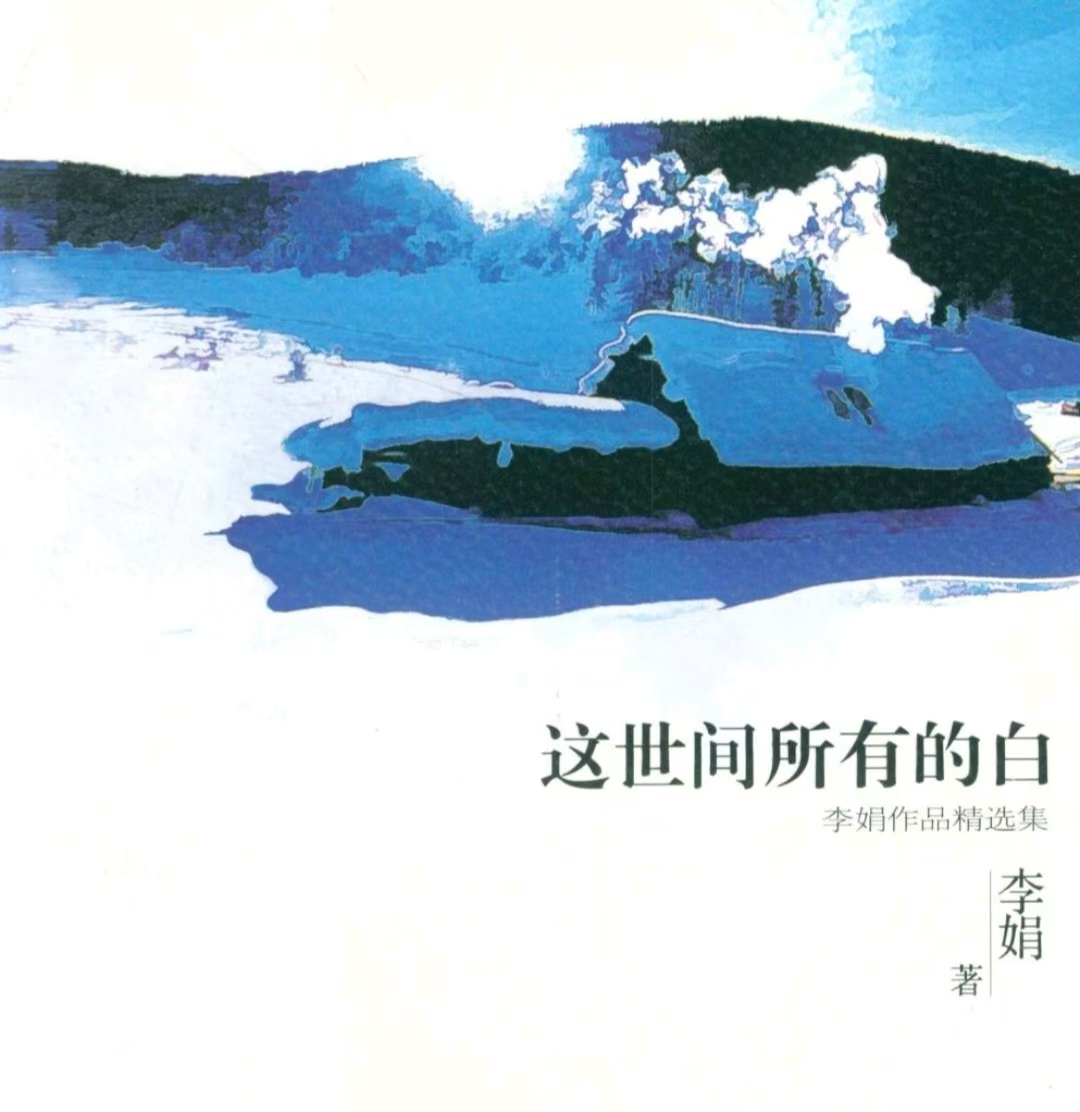
仅供习读,侵联立删。
1
2009年的冬天
前两天和朋友谈到窖冬菜的事,不由得想起了前年冬天的萝卜。
前年入冬前,我继父突然来到我家里(他和我妈一个在县上一个在 乡下,平时分开生活的),扛着一大袋子萝卜。他说:“娟啊,得把它 埋了,不然坏得快。”
我家没地窖,要窖冬菜,得在后院菜园里挖坑埋了。地底的温度不 高不低,较适合保存蔬菜之类的食物。
我说行啊。他就扛去埋了。全程我都没有参与。
他回来告诉我,埋到了茄子地边上靠近黄瓜的地方。 接下来,他就中风了。
偏瘫,不能说话,不能自理,只能微微活动左手,只能不停地哭泣。
我逗他:“那你总得告诉我萝卜埋哪儿了啊?” 他啊啊喔喔半天。
我说:“你好歹指一下啊?”
他往东指,又往北指,又往下指。
我给他纸笔:“你好歹画个示意图啊?”
他左手颤巍巍捏笔,先画个圈,又画个圈。我笑了,他也笑了。
2
那时无论茄子还是黄瓜都无影无踪了,连枯败的株秆也被隔壁的 两只无恶不作的小山羊细致啃净,没剩一点线索。加之很快又下了几场 雪,后院平整光溜,连个微微凸起的包都没有。
我一有空就扛着锨去后院刨萝卜。然而谈何容易!地面已经上冻, 硬邦邦。每挖开一块冻土层,就得躲回屋休息两到三遍。太冷了。
我估计着茄子黄瓜的位置,以一个圆点为中心,向四面拓展了足足 半径两米的辐射。萝卜们绝对地遁了。
渐渐地进入隆冬,实在没菜吃了,连咸菜也吃完了,连我妈的纺锤 也吃了。
我妈的纺锤是一根长筷子插在一个土豆上。羊毛纺完以后,纺锤一 直扔在床下面。四个月之后,瘪得跟核桃似的,非但没死,还开始四面 发芽了。一个寂静寒冷的深夜里,我想起了它,找到了它,为它的精神 所感动,并残忍地吃掉了它。
3
据说发芽的土豆有毒。可我一直好好地活到现在,大约因为毒的剂 量太小了吧。 一颗瘪土豆切丝炒出来的菜,盛出来一小撮刚盖住碗底。
家里还有一些芡粉,我搅成糊,用平底锅摊成水晶片,凉透后切成 条,再当作粉条回锅炒。
土粉条也很快吃完了。
好在还有四个蒜!我揉了面团。在水里洗出面筋。面汤沉淀了用铁 盘子蒸成凉皮。切成条浇上酱油醋辣椒酱,再把珍贵的蒜——这个冬天
唯一的植物气息——剁碎了拌进去……四颗蒜共有六十瓣蒜粒,于是吃 了六十份凉皮,慰藉了我整整两个月啊!
这样,只吃凉皮,就吃掉了十几公斤面粉。
4
蒜也没有的时候,还有辣椒酱。这是最富裕的库存!那年秋天我妈 做了二十公斤辣椒酱!
但天天吃辣椒酱也不是个事啊,吃得脸上都长出“辣椒”两个字了。
最惨的是,鸡也不下蛋了。虽然鸭子还在下蛋,但鸭蛋是赛虎和两 个猫咪的口粮,我不好意思和它们争嘴。
于是,继续刨萝卜。
雪越下越大,后院积了一两米厚,后门堵得结结实实,我好容易才 掏了一条仅容侧身而过的一线天小道通向厕所。那样的小道,我妈那种 体型绝对过不去。
我试着再挖一条一线天通向菜地。但……谈何容易!
最可恨的是赛虎,从来不肯帮忙。按说,这会儿报答我的时候也到 了。亏它夏天搞空名堂挖耗子洞挖得废寝忘食,怎么喊都不回家。这会 儿,挖个萝卜都不好商量。
5
那个冬天只有我一人在家。我妈带着继父四处奔波、治疗。中间她 只回来一次,帮我把煤从雪堆里刨出来并全挪进了室内。然后又走了。
我妈自然过得比我辛苦多了。但她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离开之前 砸了电视机。没有吃的已经悲摧,没有娱乐则更 ……
偏那个冬天又奇长,整整五个月!
我开始看《圣经》。这是家里唯一没看过的书。我被迫把耶稣的家
谱摸得一清二楚。但个人觉得,还是《古兰经》更好看些。
开始织毛衣。我家毛线多的是。 开始染衣服。我家染料几大箱。
开始……再没啥可开始的了。织毛衣,染衣服,铲雪,做饭,喂鸡 喂鸭喂兔子喂猫喂狗,生炉子,砸煤,睡觉,写字。 一共九项内容,填 充了那个冬天全部生活。五个月啊 ……
6
其他还好说,没有吃的这个现实实在难挨。家里所有能入口的东西 如下:面粉、大米、葵花籽油、辣椒酱以及最初的鸡蛋、咸菜、大蒜和 纺锤。对了,还有瓜子,我家就是种葵花的。那个冬天我嗑瓜子嗑到嘴 角都皴了。
好在虽不丰富,面粉、大米等基本口粮还算充分。至少没绝粮。那 段时间雪大,路总是不通,万一断了粮,我就只好以嗑瓜子为生了!那 时,恐怕不只嘴角,扁桃腺垂体都会皴的!
这么一想,又觉得幸好没电视!否则一旦出现盛宴画面,那对人的 摧残啊 ……
无论如何,冬天还是过去了。只是化雪的时候比较忙乱。最热的那 几天,门前波涛滚滚,似乎整个阿克哈拉的融雪全流过来了。我每天围 追堵截,投入激烈的战斗,那时我最大的梦想是能有一双雨靴。
7
显然,光凭围追堵截是远远不行的。我开始大修水利工程,挖了一 条沟,指望能够把院子里的积水(墙根处的水半尺深!)引到院外。结 果失算了,反而把院子外的水全引到了院内(墙根水一尺深……)。
为此大狗豆豆对我恨之入骨,我把它的狗窝淹了。于是,它每天抓
门,硬挤到房子里过夜。
真是佩服李冰父子,没有水平仪,也能修出都江堰!
化雪时也是清理积雪的最好时候。我觉得当务之急,应该是先挖出 我妈的摩托车。要不然雪水一浸,车非废了不可。于是在雪堆里掏了大半 天。挖出来的摩托车倒是锃光瓦亮,一点儿也没锈。但我妈回来后也没表 扬我。因为车的后视镜、仪表盘和车轮旁边的护板全被我的铁锨砸碎了。
那时路也通了,阿克哈拉也有一些蔬菜卖了。
8
总之冬天还是过去了。只是继父的病一直没有好转(直到现在仍没 有好转……),妈妈把他带回了阿克哈拉,天气好的时候,他就软塌塌 地坐在门口晒太阳。
对了,一开始说的是萝卜的事。萝卜消失了一个冬天。似乎它们冷 得不行了的时候,就纷纷往地底深处钻。等暖和了,又开始往回钻。五 月,雪全化完了,我平整土地,播撒种子。挖至一处时——我发誓正是 我整个冬天上下求索的地方———锨铲断一根萝卜,再一锨,又断了一 根……已经融得跟糨糊一样了。我只好搅一搅,拍一拍,将萝卜酱和泥 土充分混合,成为最好的肥料。
我回到房子,再问继父:“萝卜呢?” 他依旧啊啊啊地说了许多。
我又问:“你是不是说发芽了?”
这回,他发音标准地大声说:“莫有!” (2011)
9
冬牧场
南下跋涉的头一天上午,我们的驼队和畜群长时间穿行在没完没 了的丘陵地带。直到正午时分,我们转过一处高地,视野才豁然开阔,
眼下一马平川。大地是浅色的,无边无际。而天空是深色的,像金属一 样沉重、光洁、坚硬。天地之间空无一物……那像是世界对面的一个世 界,世界尽头的幕布上的世界,无法进入的世界。我们还是沉默着慢慢 进入了。
走在这样的大地中央,才感觉到地球真的是圆的——我们甚至可以 看到大地真的在往四面八方微微下沉,我们的驼队正缓缓移动在这球面 的最高点。
大约两个小时后,空旷的视野里出现了一长溜铁丝网,从东到西,拦 住了一切。而我们继续前进,很久以后走到近前,才看到土路与铁丝网的 交叉处有豁口。穿过这豁口,继续深入大地的西南方向。很久很久以后, 又看到这铁丝网的另外一面——仍然横亘东西,前不见头后不见尾。
10
在这荒凉的戈壁滩上,为什么要建造这么巨大的一个工程,圈起如此广阔无物的土地?
对此,居麻的说法是:为了能让戈壁滩变得跟喀纳斯(阿勒泰最著 名的国家级森林公园)一样。不准我们的羊再吃草了,只让野马去吃,让 草使劲长。不然的话,内地人来了,就会说:“都说新疆是好地方,其实 啥也没有嘛,全是戈壁滩嘛!”——草也没有,野马也没有,也拍不成电 视,也照不成相,太难看了!太丢脸了!所以一定要保护起来 …
我估计这是基层干部们在给动迁的牧民做思想工作时给出的一个不 耐烦的解释。
真正的原因大约是近几年推行“退牧还草”政策,防止过度放牧, 所以进行圈划,分区轮牧。
据说铁丝网要围五年,现在已经围了三年了。
我们的邻居一家四口, 一对小夫妻, 一个小伙子, 一个小婴儿。男 主人就是新什别克。
11
刚到沙窝子时,我问居麻女主人叫什么,居麻说不知道。又问那个 小伙子叫什么,也说不知道。再问他们分别多大年纪,还是不知道。我 大为奇怪:“你们不是邻居吗?”
后来才知,今年是两家人开始做邻居的第一年,其实大家都不 熟的。
往年,这数万亩的牧场上只住着居麻一家人。而新什别克家的牧地 正好在铁丝网圈住的范围里,被勒令休牧后,虽失去了牧地,却得到了 补偿金。于是他们用这补偿金重新租借牧场,继续放羊。这个冬天,新 什别克共付给居麻家四千块钱的租金。去年雪大,今年牧草丰足,因此
对居麻家来说,四千块钱还是很划算的。
我又打听了一番,隔壁有两百多只羊,三十来只大畜(骆驼居多)。 一整个冬天下来,每位才摊到不到二十块钱的伙食费!真是节约标兵。
12
我们生活刚稳定下来不久, 一个大雾的月夜里,两个迷路的不速之 客带来了一个坏消息,正与这次租借牧地有关。
话说这俩人原本去北面的邻牧场,结果迷路了。他们声称自己开汽 车过来的,显然那辆汽车肯定不咋样,因为两人穿衣的架势跟骑马差不 多。一位居然套着阔大笨重的生皮的羊皮裤,年轻点的那位像妇人一样 裹着宝石蓝的厚墩墩的羊毛马夹。两人急于赶路,传递完消息,又问清 道路,茶也不喝就走了。客人走后,居麻激动又气愤,就此事逮着嫂子 大声争论起来,还把嫂子当成对立方呵斥了半天。嫂子始终默默无语地 提着纺锤捻羊毛线。
原来这块牧地并不是居麻一家的,原先属于三家人共有,但其中 一家多年前迁去了哈萨克斯坦,另一家也很快改行做起了生意。于是这 些年来只有居麻一家守着这几万亩荒野,从没人过问什么。可草场刚租 出去,做生意的那家就开始过问了。他家认为新什别克付的租金应该两 家平分,便去乡领导那里告了状。居麻大怒,冲我嚷嚷:“他自己又不 来,怪我干啥?别说告到乡里,就是告到中央也是我有理!”可我觉得 他实在没啥理。
13
这件事大家议论了两天,并商量好了说辞,坐等告状的那家前来理 论。可人家才不傻,犯得着吗?骂个架跑这么远。调解委员会的自然更 不会来了,公家那么穷,哪有钱报销汽油费。
这事似乎再无后话,大家松了口气。可我却始终不安,隐隐感觉到 了牧场和牧人日渐微薄的命运。
传说中最好的牧场是这样的:那里“奶水像河一样流淌,云雀在绵 羊身上筑巢孵卵”——充分的和平与丰饶。而现实中更多的却是荒凉和 贫瘠,寂寞和无助。现实中,大家还是得年复一年地服从自然的意志, 南北折返不已。春天,牧人们追逐着融化的雪线北上,秋天又被大雪驱 逐着渐次南下。不停地出发,不停地告别。春天接羔,夏天催膘,秋天 配种,冬天孕育。羊的一生是牧人的一年,牧人的一生呢?这绵延千里 的家园,这些大地最隐秘微小的褶皱,这每一处最狭小脆弱的栖身之 地……青春啊,财富啊,爱情啊,希望啊,全都默默无声。
14
前来收购马匹的一位生意人告诉我:再过两年——顶多只有两年时 间,就再也看不到这样搬家游牧的情景了!从明年开始,南下的羊群到 了乌伦古河畔就停下,再也不会继续往南深入。
我大吃一惊:“也太快了吧?” 我的反应很令他生气。
我噤声。其实我的意思是,虽说这种古老的传统生产方式本身正在 萎缩,但这么突然的大动作,对人们的生活和心理该是多大的冲击和摇 撼 啊 。
过了半天我忍不住又问:“是真的吗?是谁说的?有上面的文件?” 他说:“文件肯定有,我们肯定看不到。反正大家都这么说嘛。”
居麻大喊了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又嚷嚷道:“是他说的!昨天 给我打的电话!”
大家哄堂大笑,转移了话题。
15
其实我还想问:“你们觉得定居好吗?”再一想,真是个蠢问题。 定居当然好了!谁不向往体面稳定、舒适安逸的生活呢?
荒野终将被放弃。牧人不再是这片大地的主人。牛羊不再踩踏这片 大地的每一个角落,秋天的草籽轻飘飘地浮在土壤上,使之深入泥土的 力量再也没有了,作为它们生长养料的大量牲畜粪便再也没有了,荒野 彻底停留在广阔无助的岑寂之中……荒野终将被放弃。
而在北方,在乌伦古河两岸,大量的荒地将被开垦成农田,饥渴地 吮吸唯一的河流。化肥将催生出肥大多汁的草料,绰绰有余地维持畜群 度过漫长寒冬。这有什么可说的呢?
居麻一喝醉了就骂我滚。我要是有志气,应该甩开门就滚。可甩 开门能滚到哪里去?门外黄沙漫漫,风雪交加,无论朝着哪个方向,走 一个礼拜也走不到公路上去,况且还得拖个比我还大的行李,况且还有 狼,只好忍气吞声。
16
我刚进入这片荒野的时候,每天下午干完自己的活,趁天气好, 总会一个人出去走很远很远。我曾以我们的黑色沙窝子为中心,朝着四 面八方各走过好几公里。每当我穿过一片旷野,爬上旷野尽头最高的沙 丘,看到的仍是另一片旷野,以及这旷野尽头的另一道沙梁,无穷无 尽。—-当我又一次爬上一个高处,多么希望能突然看到远处的人居炊 烟啊!可什么也没有,连一个骑马而来的影子都没有。天空永远严丝合 缝地扣在大地上,深蓝,单调,一成不变。黄昏斜阳横扫,草地异常放 光。那时最美的草是一种纤细的白草,一根一根笔直地立在暮色中,通
体明亮。它们的黑暗全给了它们的阴影。它们的阴影长长地拖往东方, 像鱼汛时节的鱼群一样整齐有序地行进在大地上,力量深沉。
17
走了很久很久,很静很静。 一回头,我们的羊群陡然出现在身后几 十米远处(刚到的头几天,无人管理羊群,任它们自己在附近移动), 默默埋首大地,啃食枯草。这么安静。记得不久之前身后还是一片空茫 的。它们是从哪里出现的?它们为何要如此耐心地、小心地靠近我?我 这样一个软弱单薄的人,有什么可依赖的呢?
在这无可凭附的荒野,人又能依赖什么呢?我们安定下来的第二 天,就在沙窝子附近的沙丘最高处插了一把铁鍁,挂了一件旧大衣。远 远看去,像是站了个人在那里——用以吓唬狼。刚驻扎下来时,有寻找 骆驼的牧人前来提醒:前几日,两只狼在大白天里袭击了羊群,咬死了 四只羊。
从此,这个假人成为我们的地标,无论走多远,只要回头看到它还 好端端地站在那里,心里便踏实。反之则心慌意乱,东南西北一下子全 乱套了,尤其是阴天里。
18
略懂汉话的居麻对“迷路”一词的说法是“忘了”。说:“今天下 午嘛,我又‘忘了’。羊在哪个地方,我在哪个地方,这边那边,不知 道了嘛!"
我试着打听过我们待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地名,但这么简单的问题, 居麻却怎么也领会不了。于是直到现在我都没弄清自己到底在茫茫大地 的哪一个角落度过了一整个冬天……只知道那里位于阿克哈拉的西南方 向,行程不到两百公里,骑马三天,紧挨着杜热乡的牧地,地势东高西
低。据我的初步调查,这一带能串门的邻居(骑马路程在一日之内)有 二十来户,每户人口很少有超过四个人的。共十来块牧地,每块牧地面 积在两万至三万亩之间。大致算下来,每平方公里不到二分之一个人
(后来我从牧畜局查了一下有关数据,密度比这个还小,整个富蕴县的 冬季牧场,每平方公里不到四分之一个人)。
19
放下茶碗,起身告辞的人,门一打开,投入寒冷与广阔;门一合 上,就传来了他的歌声。就连我,每当走出地窝子不到三步远,也总忍 不住放声唱歌呢!大约因为一进入荒野,当你微弱得只剩呼吸时,感到 什么也无法填满眼前的空旷与阔大时,就只好唱起歌来,只好用歌声去 放大自己的气息,用歌声去占据广阔的安静。
加玛一直戴着一对廉价又粗糙的红色假水钻的耳环,才开始我觉得 俗气极了。很快却发现,它们的红色和它们的亮闪闪在这荒野中简直如 同另外的太阳和月亮那样光华动人!
另外她还有一枚镶有粉红色碧玺的银戒指,这个可是货真价实的值 钱货,便更显得她双手的一举一动都美好又矜持。
我还见过许多年迈的、辛劳一生的哈萨克妇人,她们枯老而扭曲的 双手上戴满硕大耀眼的宝石戒指,这些夸张的饰物令她们黯淡的生命充满尊严,闪耀着她们朴素一生里全部的荣耀与傲慢。——这里毕竟是荒 野啊,单调、空旷、沉寂、艰辛,再微小的装饰物出现在这里,都忍不 住用心浓烈、大放光彩。
20
有一天加玛在一件旧衣服的口袋深处摸到了一枚假金戒指。当时已 经挤得皱皱巴巴,拧成一团了。居麻把它掰直了,再套在一根细铁棍上
敲敲砸砸一番,使之恢复了原状。为表示友谊,加玛把它送给了我。我 非常喜欢,因为它看上去和真的金子一模一样。若是以前,我是说什么 也不会把这样的假东西戴在手上的。可如今,在荒野深处这个俭朴甚至 寒修的家庭里,在仅具备最基本日常用具的生活里,在空无一物的天地 间,它是我唯一的修饰,是我莫大的安慰。它提醒自己是女性,并且是 有希望和热情的……每当我赶着小牛向荒野深处走去,总是忍不住不时 用右手去抚摸左手的手指,好像那枚戒指是我身体上唯一的触角,唯一 的秉持,唯一的开启之处。在蓝天下,它总是那么明亮而意味深长。
21
十二月初,每隔两天,就会有南迁的披红挂彩的驼队和羊群遥远地 经过我们的牧地。我和加玛高高站在沙丘上,长时间目送他们远去,默 数他们的骆驼数量,判断他们的财富。什么也不为,什么也不说。他们 的行进真是骄傲又孤独。在荒野中他们最倔犟。
有一天早茶后,加玛唤我出去,我一看,又一支队伍经过西面的荒 野向南慢慢行进着。但是加玛又提醒我:“看,没有马。”仔细一看, 果然,队伍里只有一个人步行牵着驼队,同时还兼顾赶羊。看来看去再 也没有别人了。比起之前几支又是摩托车又是座饰华美的马匹的队伍, 可真寒啊。加玛判断道:没有马是因为他家昨夜驻扎时,马跑散了; 只有一个人前进是因为其他人都找马去了。
无论如何,那情景让人看了很是辛酸。这是荒野,什么样的挫折都 得接受,什么样的灾难都得吞咽。(2011)
22
唯一的水
出发进入冬牧场之前,我妈羡慕地对我说:“这个冬天你可以喝到 最好的水了!”我也以为然。因为冬牧场位于沙漠地带,唯一的水源来 自于雪。雪水多好啊,是天上掉下来的蒸馏水!而阿克哈拉位于乌伦古 河畔的戈壁滩上,饮用井水,碱很重。这些年越发咸苦了,用来烧汤的 话根本不用再放盐。洗出来的衣服也泛着厚厚的白碱圈。
可实际上呢……沙漠里的水,味道是不坏,甚至还算非常甘爽,没 有一点咸味或异味,但其透明度……若在以往,这样的水我看一眼都会 吓晕。
去年是雪灾之年,而今年则出奇的大旱。只在十一月末有一场像 样的雪,接下来一直到十二月底还没啥动静。好容易某个深夜里纷纷扬 扬下了一阵,瞬间大地上就白了。可第二天早上满怀希望出门一看,仍 然是个黑乎乎的沙窝子——总是雪后紧接着又起风。我真嫉妒东面的牧 人,雪一定都被吹到他们那里去了。
23
好在大风过后,沙丘的洼陷处及草根处多少会积留一些残雪,但很薄,顶多一两公分。这样的雪,我收集半个小时化开后的水还不够 洗一双袜子。又由于是风吹来的,一路上和沙土、枯草、粪渣紧密团结 在一起……化开后混浊不堪,锅里有一寸多厚的沙子(难怪背着那么 沉!)、不忍细数的羊粪蛋,甚至还会出现马粪团这样的庞然大物 …… 就算完全沉淀了,水的颜色也黄红可疑——未必比我袜子干净。
然而再想,袜子毕竟是臭的,这水尝起来啥味也没有,肯定比袜子 强多了。喝吧!
并非我们采雪时不细心,如果像修表一样小心翼翼地收集,倒是能 弄得纯粹一些。可那样的话,一个礼拜也装不满一袋子。
24
我用一只浅盘子把被风吹得紧致结实的积雪一小块一小块地齐根铲 起倒进编织袋里。加玛用一只水勺像舀水一样舀着装。嫂子直接用扫把 呼呼啦啦扫成一大堆再装……加玛的速度是我的两倍,嫂子的速度是我 的十倍。
居麻从来不干采雪这样的事,因此非常挑剔。每天放羊回家,一进 地窝子先凑到大锡锅前瞟一眼。若是看到水里羊粪蛋很少,马粪团一个 也没,就欣慰地说:“这锅水肯定是李娟拿回来的。”——答对!
这样的雪装了三天之后,我决定这个冬天再不洗澡了! 一个礼拜之后,又决定再也不换洗衣服了……
25
用来背雪的袋子曾装过五十斤的混合饲料,这样的袋子装满雪再顿 瓷实了,足有三十来斤。重倒也罢了,还那么远。并且距离一天比一天 远!近一些的沙丘上的雪早就被找完了。扛一袋雪回家,途中足足得休息五六次,到家已经给压得头晕眼花。而一天最少得背两趟才能勉强维 持全家人一天的用水量。
家里有四口人,水的主要用途是烧茶。除我之外,大家都特能喝 茶。一天最少布六道茶, 一次最少得消灭掉满满一暖瓶。剩下的水用来 做饭。 一天只有一顿饭,就是夜里的那顿正餐,吃些面条汤、拉面什么 的(其他时间都喝茶泡干馕)。再剩下的水用来洗碗(往往一碗水洗一 撂碗)。最后的则用来洗脸洗手——用手壶浇着洗,这种方式倒非常省 水,四个人的洗漱用水加起来也不到小半盆。
26
洗碗水虽不多,但也省下来给狗泡几块干馕,或给怀孕的母牛当营养餐 。
刚搬来时,居麻修补炉基和破损漏风的屋顶、门框时和泥巴的水, 则是攒的洗手水。
十二月中旬,加玛要走了,回乌河之畔照顾生病的奶奶。她是整洁 自尊的姑娘,不愿意蓬头垢面地走出荒野, 一定要洗头发。为此,那天 傍晚嫂子一挤完牛奶就出去找雪,在夜色里背回一大袋。不但让姑娘洗 了头,还洗了好几件衣服。
尽管自己嚷嚷着再不洗头了,但看着加玛洗,还是很眼红。搬家 时吹了几天风,到地方又干了两三天羊圈的活,头发脏得已经硬邦邦的 了。不说别人看着难看,自己都难受。于是在加玛洗完头的第二天,我 下狠心一口气背了三趟雪……但到用时,却只舍得用小半盆……就算是 自己背来的雪,也不好意思多用。
27
洗头时,我放弃自己的习惯,完全效法加玛,连清带洗只用了小半
盆水。洗完后,洗发液当然是原封不动地糊在头顶上,从头发梢流下的 水蜇得人眼睛生痛。
加玛认为头发实在太脏了,非得用强效洗涤剂不可。于是第一遍用 洗衣粉……第二遍才用洗发液。洗发液是她的姐姐乔里潘送的,她用得 非常珍惜。
我呢,洗衣粉就算了吧……
总之,那半盆水洗得那个黑啊……作为女性我很羞愧。但还是安慰 地想:总比不洗好吧?虽然残留了大量刺激剂品,但晃晃脑袋,起码轻 了二两。
加玛又用洗过头发的水顺带洗了衣服。我没洗,怕把衣服洗脏。
28
居麻郑重地告诉我,他跟嫂子一直等到四月才洗澡。我听了默默无 语。后来才知道是玩笑话。怎么可能一直不洗呢?痒都痒死了。
我强忍住洗澡的念头也是因为痒的原因,想想看:抹了一身的泡 沫却只有一碗水给你浇……这种澡洗了肯定更痒。于是身上发痒时就 挠挠,挠不到的地方就靠在柱子上蹭。居麻快笑死我了,说李娟跟牛 一样 。
还好,我发现,痒到了一定程度后,再往下也就慢慢不痒了。
水脏也罢,少也罢,无论如何,我们这边好歹还有点水,北面三十 多公里处的牧场连更糟的水还都没有呢!
29
十二月中旬居麻在轮休的一天里去帮北面的亲戚挖地窝子。骑马两 小时的路程,真够远的。可再远不也在同一片大地上吗,为什么差别这
么大?——居麻说,那里基本上就没有雪!
原来那边地势过于平坦舒展,起风时,少有可阻拦雪的起伏处。那 边的牧人只好雇汽车从更北面的乌伦古河里砍下冰块运来。那样的冰, 一袋子五十来斤,却得掏二十块钱……人勉勉强强还能生活,那么牲畜 呢?牲畜们实在太可怜了,只能啃食草根处拦截的一星半点的残雪(人 工没法收集)。每吃下一点点雪,得吞进大量的沙土。
居麻说这样的旱情是以往年份里较少见的。
30
我们雇车搬家过来时,也从乌河里砍了七八袋冰块来。在非常冷或 非常忙碌的日子里,就不出去背雪了,直接化冰块。尽管我和嫂子(那 时加玛已经走了)每天努力找雪,大家也非常节省,但最后的冰也即将 用完。已经十二月底了,还是没下雪。
居麻放羊非常辛苦,好几次放羊回家,爬到沙窝子北面的沙丘上就 再也走不动了似的。下得马来,一屁股坐到沙堆上平摊开两条腿,又捶 又打,大约冻僵了。我无从安慰,只能说:“没事,再有一天就该休息 了,该轮到新什别克放羊了。”他叹道:“休息啥?坐在家里也不好,
没事干,就知道喝茶,水也不多……”听着心酸。
31
一天早上,居麻骑马到牧场西面巡查了一圈,回来后告诉我们,那 边沙梁处的雪厚一些,让我和嫂子忙完当天的家务活后,去那里多装几 袋子,等他轮休时赶骆驼过去驮回来。
于是那天中午,我和嫂子挟着六只巨大的编织袋出发了。我们穿 过一大片平坦的荒野,渐渐进入那片沙丘地带,大约走了两三公里。
果然,沙丘迎风处有许多完整、硬瓷的雪地,最厚处有五公分!我乐坏 了,这得装多少雪啊!真想分给北面的邻居几袋子!
我们顶着呼呼啦啦的寒风,埋头苦干了两个多钟头,所有袋子装得 满当当、硬邦邦。又用细铁丝拧紧袋口,将它们堆簇在一起。离开时我 频频回首,它们像害怕似的紧紧靠在一起,荒野中那么突兀……夜里, 会不会有野生动物好奇地靠近,拱它,踢翻它?
32
两天后的一大早,夫妻俩就赶着骆驼去拉雪。我觉得很神奇,那么 远,茫茫荒野,到处似曾相识。没有路,没有地标,嫂子怎么找到那几 袋雪的?
这次驮的雪让我们用了足足三四天。虽然小有丰收,但也太费事费 时了。不到最迫切的时候,是不会用这个法子的。
因为期待雪,我开始观察云。每当暖和的日子里,有怪云出现在天 空,便跑去请教居麻:“是不是要下雪的意思?”他抬头瞟一眼,总是 懒得理我。
既然不是下雪的预兆,那些云为什么长得那么怪?有时候是一大团 占据了整整半个天空的放射云,放射源在北方。壮观极了。有时候像一 大锅元宵从北方涌出来, 一团一团圆滚滚的。而傍晚时分,云总是会突 然聚积在晴朗无物的天空,并且声势越来越浩大。到最后汇聚成几条并 行的巨大河流,从东往西流,尽头是落日。
33
那些堆积如山的浩荡朝霞,有月晕的混沌夜空,阴沉沉的清晨 …… 雪不知藏在哪里慢条斯理地酝酿着,还在左思右想……足足有一个月没 下雪了!只在一些阴霾天里飘一点点轻薄的六角形雪片,有时会在深夜
里就着星空漫不经心地撒一阵。就那么点雪,稍稍吹点风就没了,真是 小气 。
直到一个阴沉的清晨,不甚均匀的云层蒙住了整面天空。我爬到 东北面沙丘上,看到从北到南的地平线滚着一溜漫长的金光,看不到太 阳。我回去兴奋地说:“肯定要下雪了!”
这回居麻终于也肯定了!但又说:“不会下太大的。” 果然,晚上十点时开始飘起了浓密的雪粒子。
果然,很快停了,还是没能铺起来。
34
第二天居麻放羊回来告诉我们,西面十公里处下的是大雪,都盖住 脚脖子了!
我问:“啊,不会这样就完了吧?晚上还会再下吧?” 他大笑:“不会了,雪都走了。”
我以为他是说雪转移了,大惊,连忙问:“走到哪儿去了?!”
却答:“到乌鲁木齐去了,看病去了。”原来瞎逗呢。不过看得出 他心情愉快。
这总算是个很好的开始。天空终于打开了一道口子。此后天气一直 暖和而阴霾,雪的意味浓重。终于,十二月底,在过寒流之前,连着下 了三场雪!积了有十公分厚!
天 一 放晴我就兴冲冲去扛雪,半个小时内扛了三袋子回家。 居麻说:“啧!李娟高兴得很嘛!”
35
我能不高兴吗?眼下到处都是雪,离家几步路就可以装了,不用走 一公里甚至几公里的路了。而且雪这么多,这么干净,化开的水从来没 这么清透愉快过。而且新雪蓬松柔软,装满满一大袋子,玩儿一样就扛
回家了,多么轻松!之前这么一大袋的话,回到家两眼都发黑了。
而且雪停后的晴空,明朗灿烂得无从形容,似乎天上真的全都 空了,真的把雪全都交给了大地。从此天空不再沉重了,不再那么 辛苦了。
就这样,在最冷的日子到来之前,我们告别了旱情。再回想一番, 这一个月其实也不算特别难挨,因为老是想到我们北面的邻居 ……
36
而且对我来说,最大的受益是从一开始背半袋雪都给压得要死 不活,到后来的某一天,突然发现自己正扛着一整袋雪走得大步流 星……这样的进步才叫“不知不觉”!
想到从此肯定再也用不上最后那几块冰了,我就把它们全化开。我们 三个人各自关起门大洗一通。嫂子还洗了所有的餐布和毛巾,第二天洗了 全部的被套和枕套,第三天洗了全部的外套和毛衣。——多么阔绰!
顺便说一下,嫂子自制的羊油肥皂也非常阔绰——有脸盆那么大! 圆圆厚厚一大饼。用时,就整个儿搬进盆里,用衣物在上面反复地擦。 她也不嫌麻烦,也没想过分割成小块后再使用。
37
终于有雪了,然而这雪一时竟下个没完。白天还好,只有零星碎雪 在阳光下时有时无地飘一阵子。到了夜里,天窗上的塑料布每隔一段时 间就簌簌作响,一听就是较实沉的雪粒子。
没雪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焦虑,有雪了,渐渐地又开始担忧。居麻望 着天对我说:“去年也是这样,老天爷下两天,休息一天…… ”——可苦 了牧人和牛羊……去年是罕见的雪灾。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担忧错了,也就过寒流那段时间下了大大小小 几场雪,之后天气一直非常晴朗。总的来说,今年还算是个好年份吧!
再说几件关于雪的事:
有了新雪后,嫂子每隔一段时间就把床榻上的花毡抱到外面, 一 床一床抡起来在平整的雪地上用力拍打,打得干干净净再抱回家重新铺 起。唉,大家总是穿着鞋子上床,居麻还总是往床上弹烟灰。
38
下雪天最大的麻烦是清理羊圈。大家得赶在羊回来之前用铁锨把羊 圈里的积雪铲去(要是有个大竹扫帚该多好!),再铺上 一层干粪。如 果干完了这活,羊一时半会儿还没回来的话,就得再展开几面阔大的塑 料布铺在羊圈里挡一会儿雪,待羊进圈时再连雪一起收去。羊是卧着睡 觉的,不能让它们腹部受寒,否则会拉肚子。
雪盖住了电池板后,大家会因储电不够而早早熄灯睡觉。这点我倒 很喜欢。
由于我实在很怕没雪的日子,天气稍一暖和就念叨个没完:“再这 么热下去,就没水了!”居麻听了便大笑。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