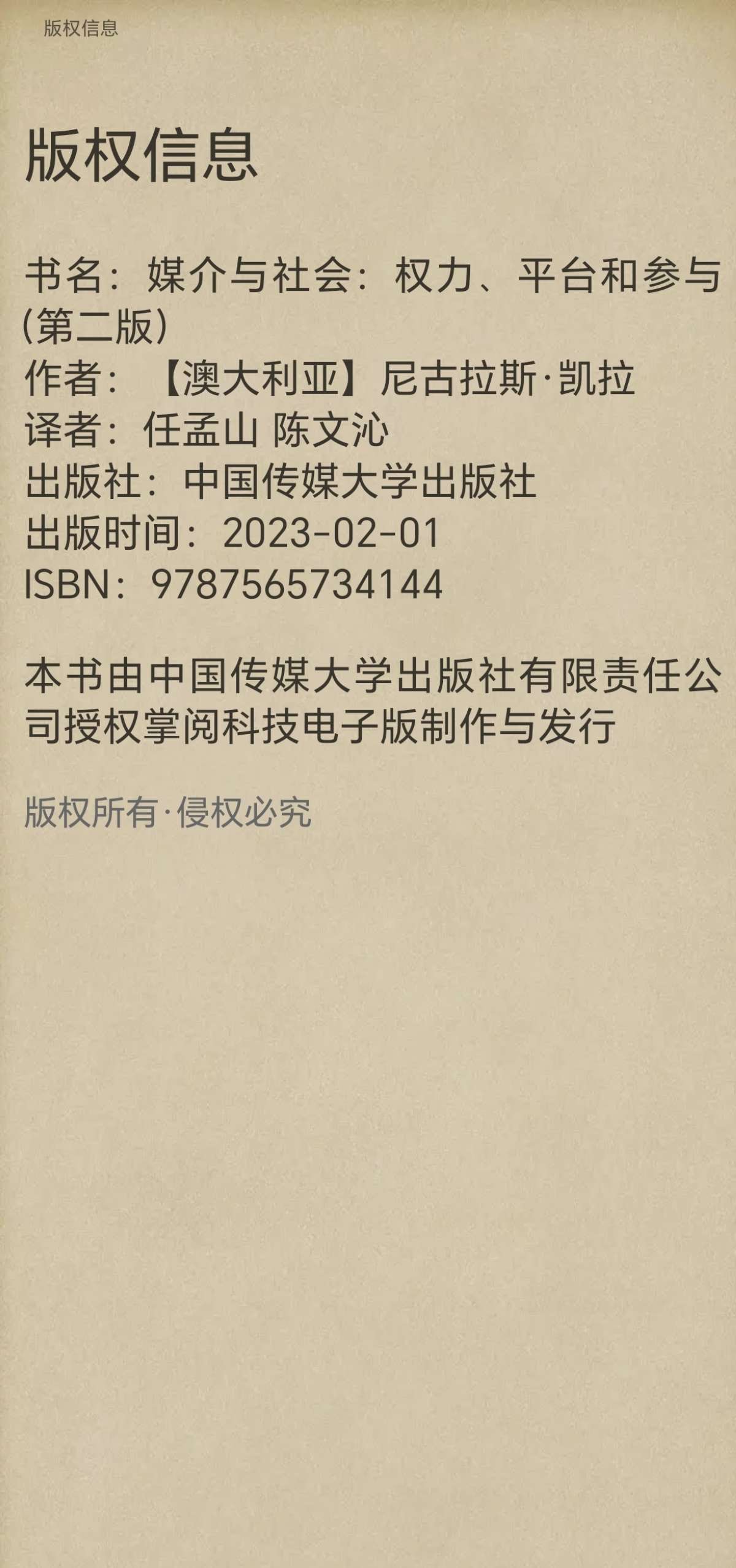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习考试科目,阅读参考书籍(883人文社科基础)(13)
《媒介与社会:权利、平台和参与》(第二版)
著者简介
[澳大利亚]尼古拉斯·凯拉(第二版)译者:任孟山 陈文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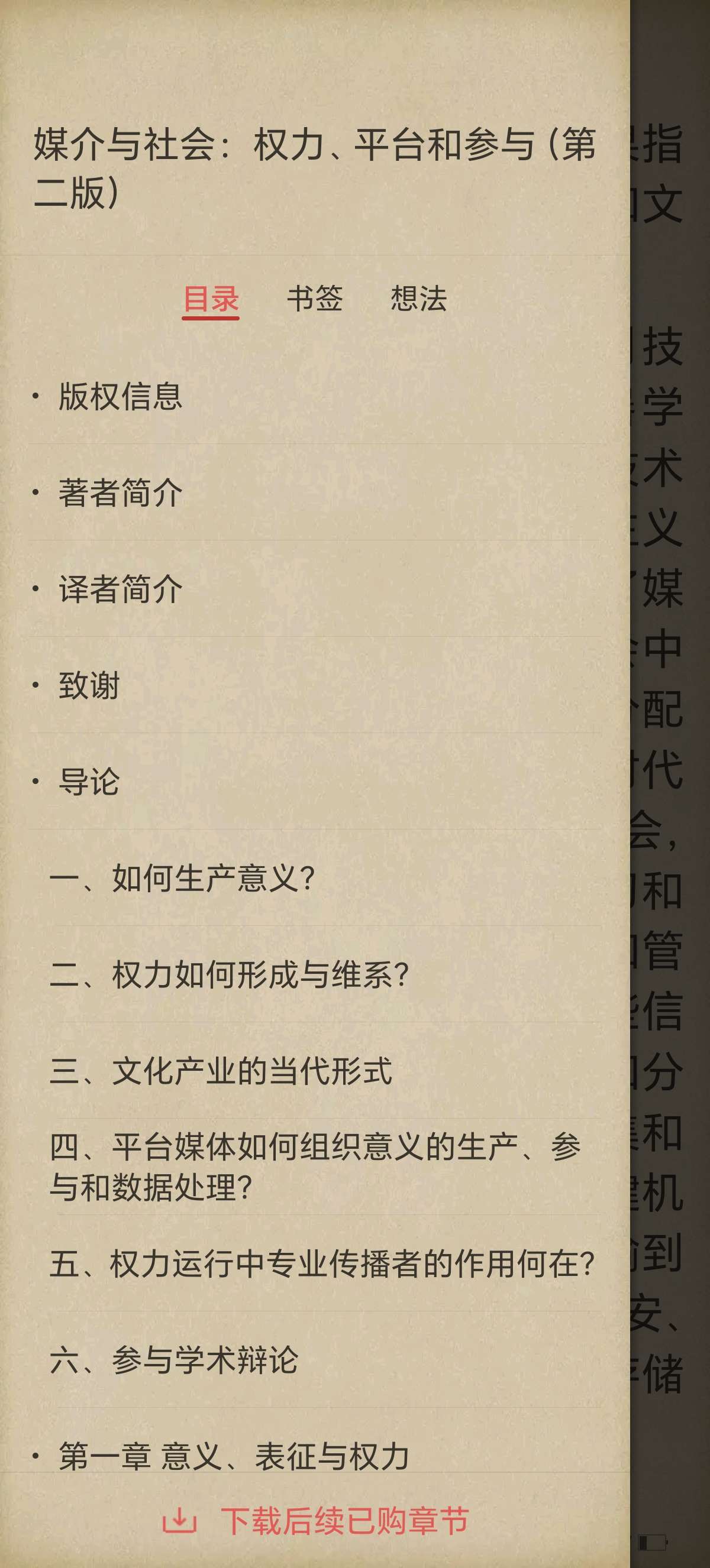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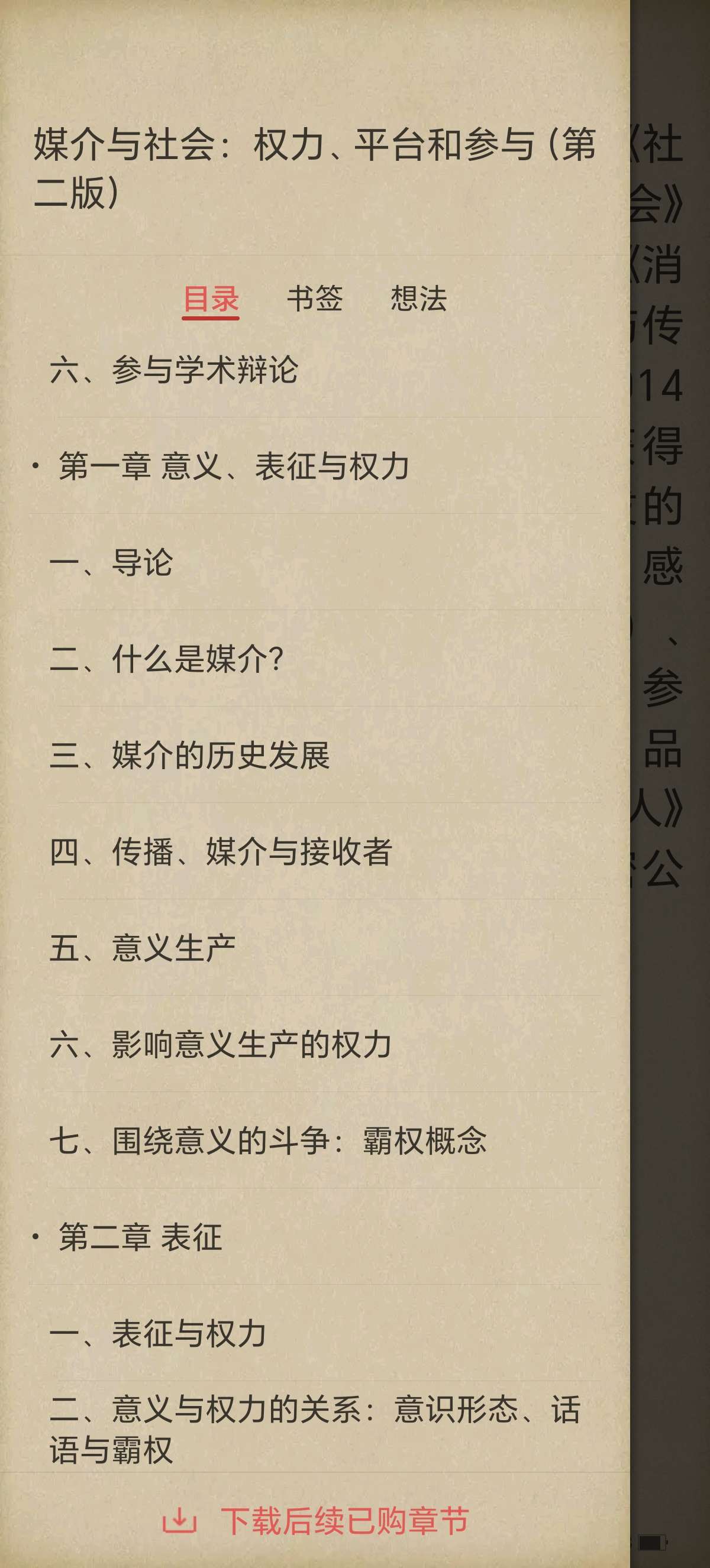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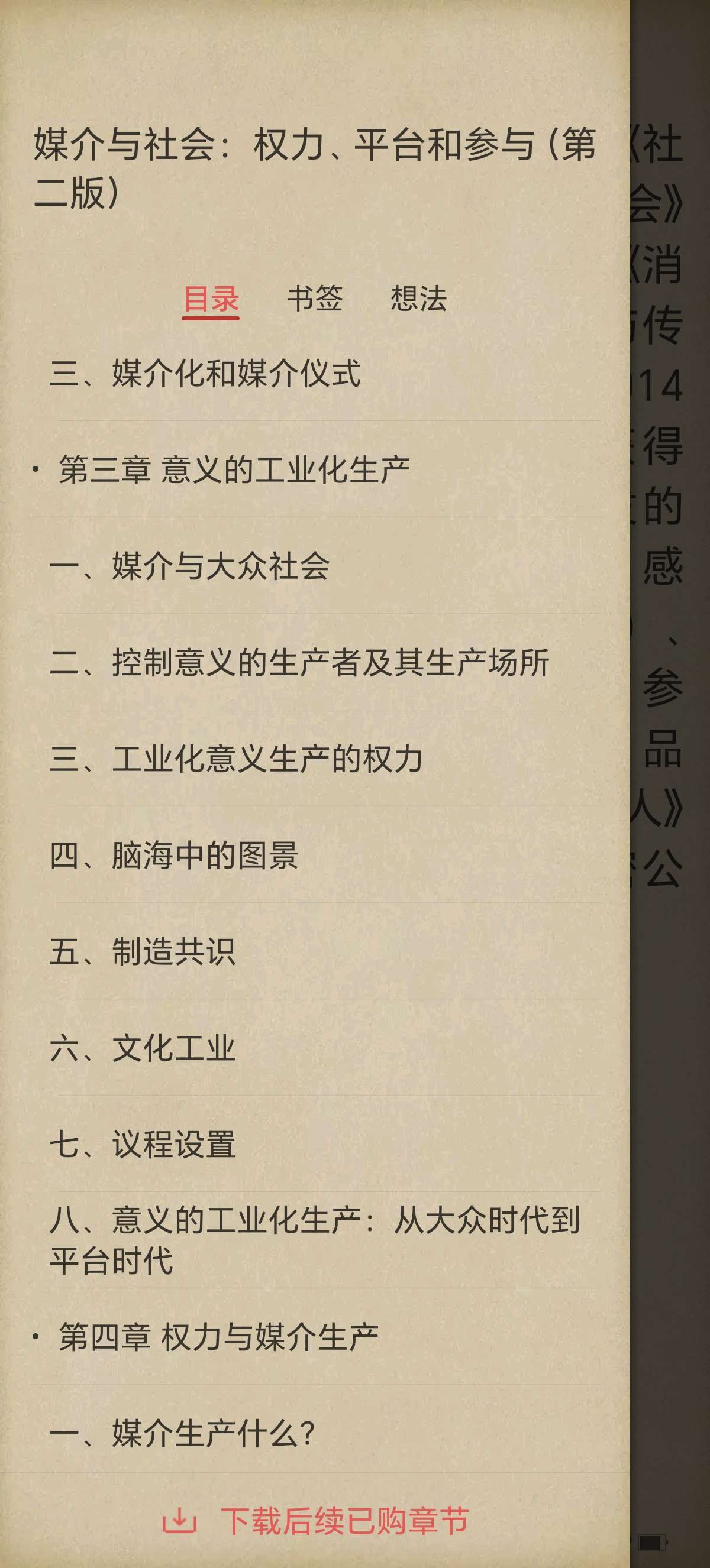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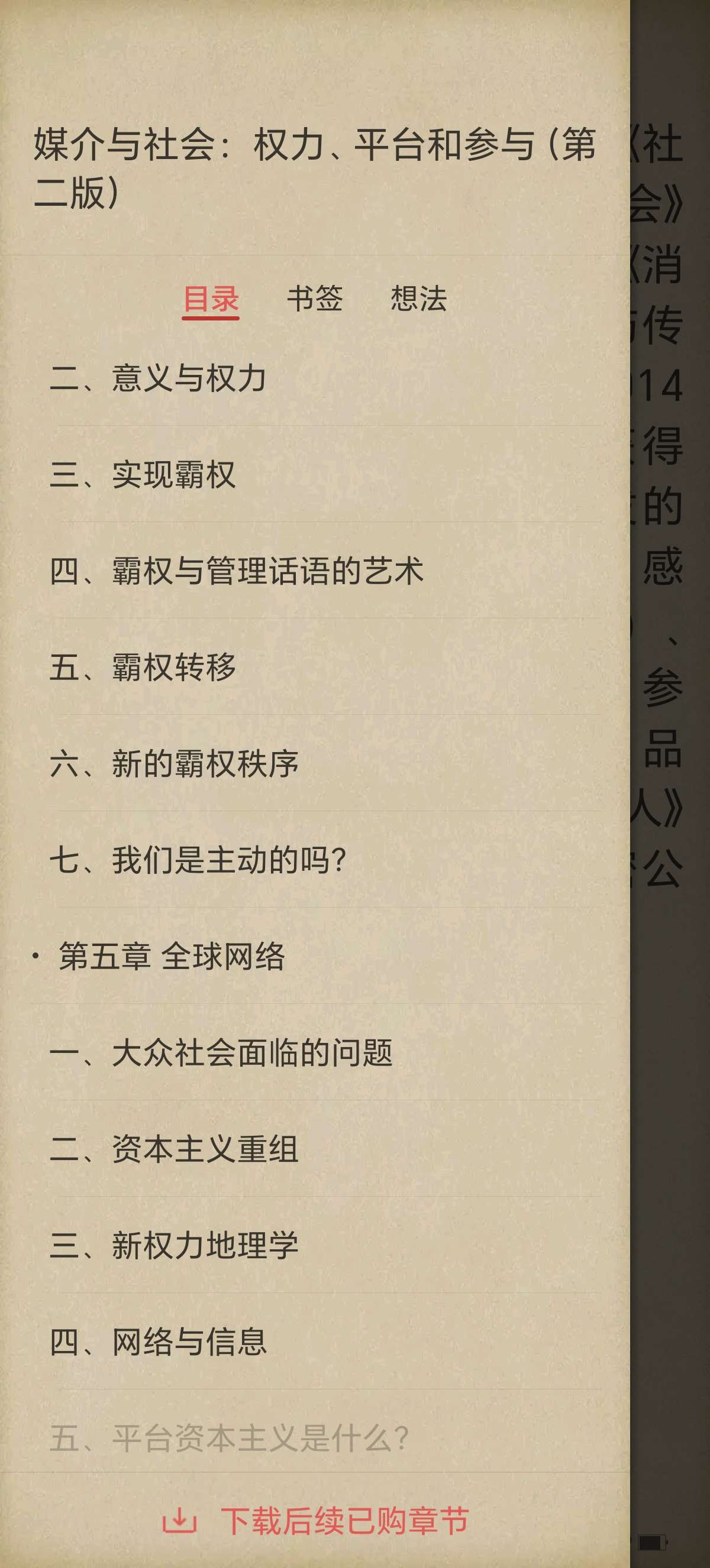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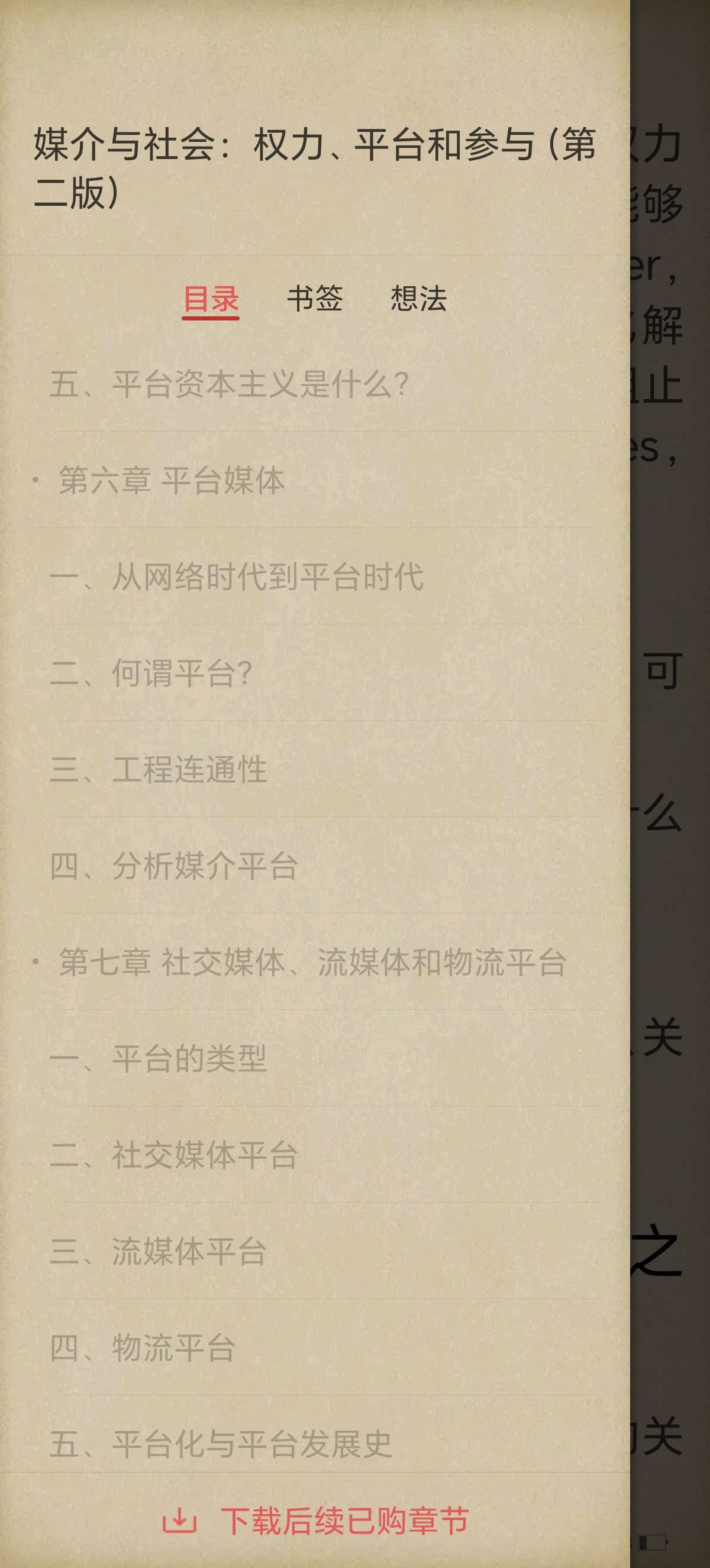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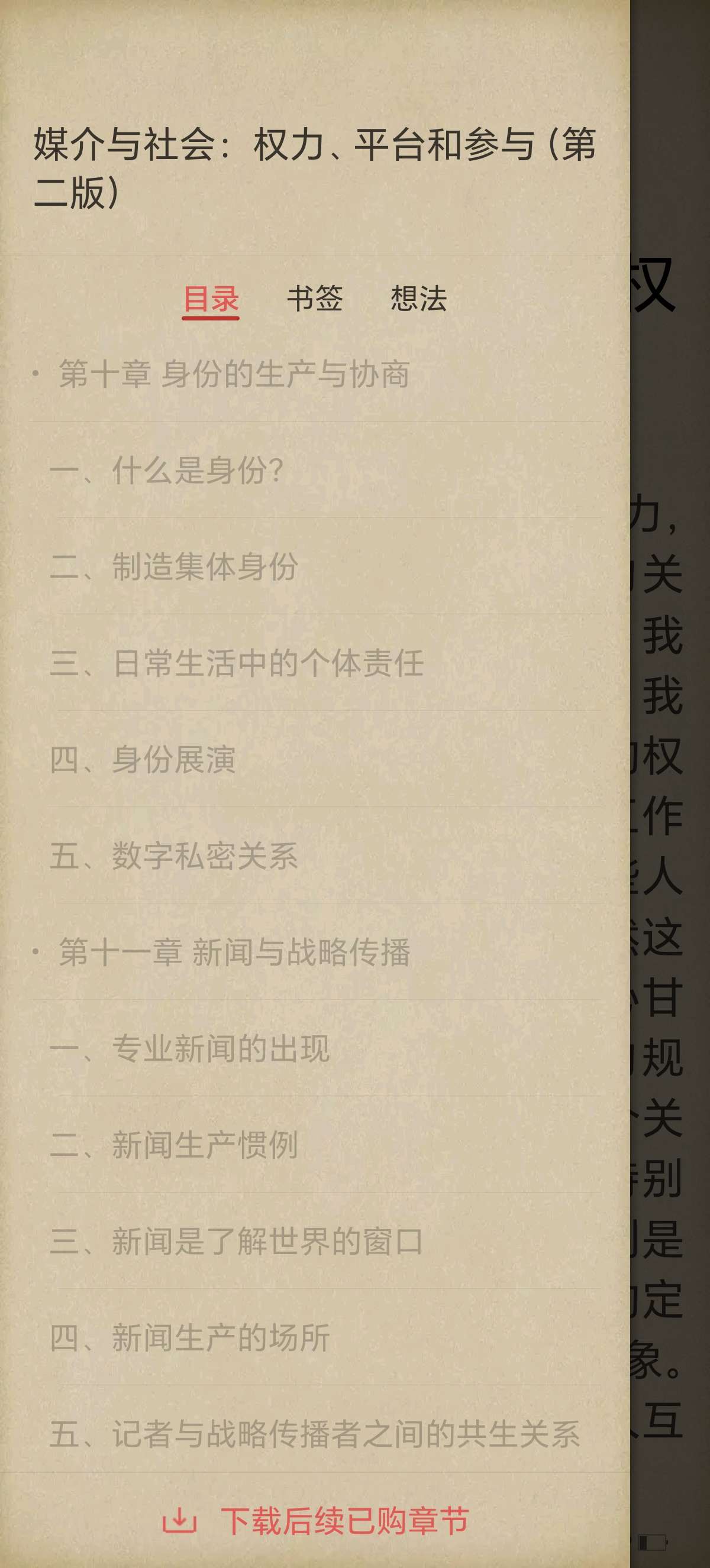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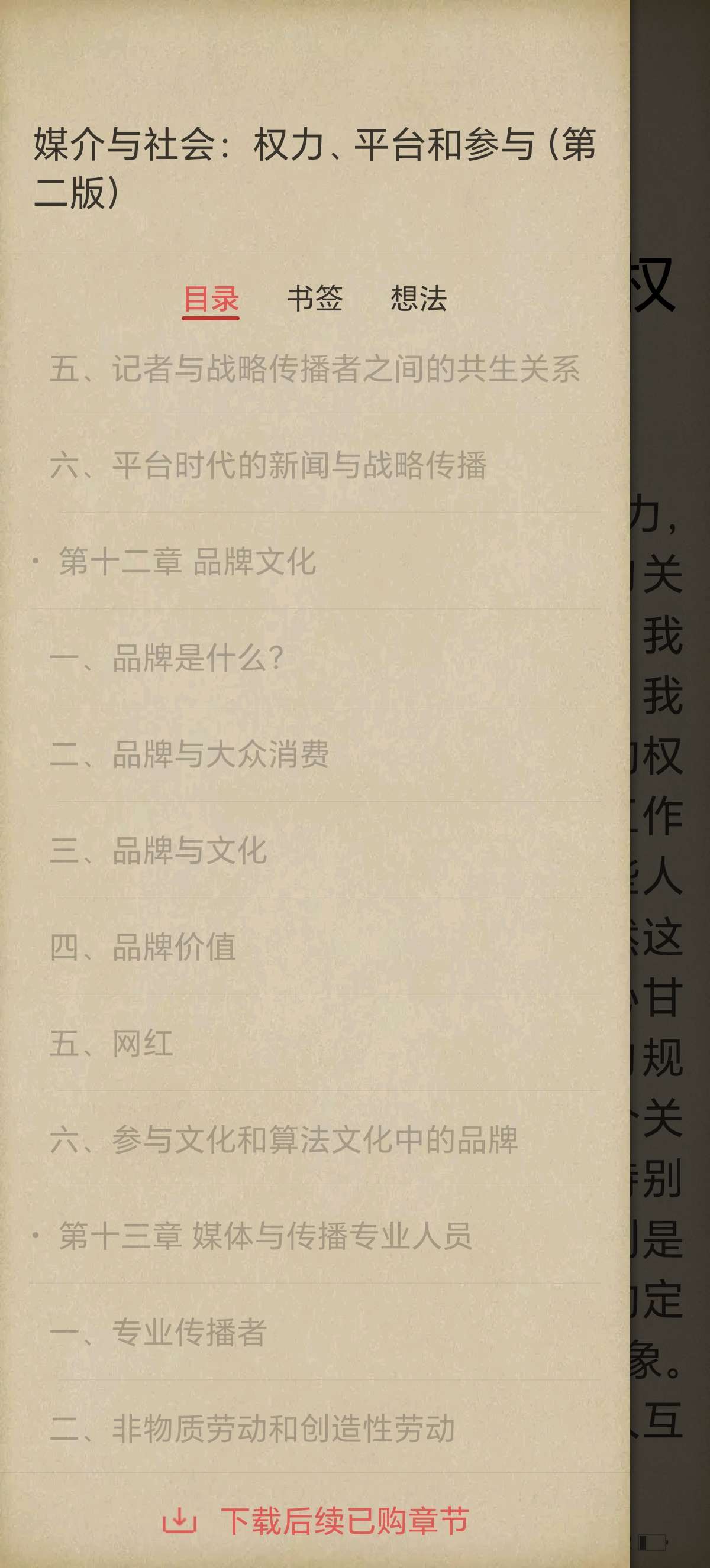
213
案例2:YouTube的算法文化
文/艾拉·唐纳德(Ella Donald)
在刚开始运营的那几年里,YouTube看起来已经是互联网时代《美国家庭滑稽录像》的完美替代品,早期的热门内容包括“查理咬我的手指”(Charlie bit m y finger)(HDCYT,2007)和“舞蹈的演变”(Evolution of Dance)(Laipply,2006)。YouTube上最受欢迎的视频不仅有21世纪头十年中期的热门视频,也有机器人创作的儿童内容,还有视频博主创作的有关政治和生活方式的视频。这反映了一个重要的趋势。现在如果查看YouTube的音乐视频排行榜,会发现许多视频都是面向儿童的简单动画,例如“学习颜色—农场上的彩蛋”(Learning Colours—Colourful Eggs on a Farm)、“洗澡歌”(Bath Song)和“蔬菜歌”(Yes Yes Vegetables Song)。这些视频中的大部分都是半自动或机器创建的,它们之所以点击量高,是因为博主利用了YouTube的内容推荐算法(Bridle,2017)。如果儿童开始观看一首动画童谣,推荐算法就会源源不断地找出类似的简单动画和歌曲,播主就会据此创建一些会被纳入推荐列表的内容。内容创作者、观众和平台之间的这种关系是由平台的内容推荐算法组织起来的。这个复杂的动态模型会根据用户的观看偏好实时调整并推荐内容,其主要的目的是让用户尽可能长时间地停留在平台上。因为用户停留在平台上的时间越长,YouTube就越能向他们播放广告、实现创收。
YouTube与其内容创作者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创作者希望最大限度地提高视频的观看次数,而YouTube则希望最大限度地提高平台整体的参与度。YouTube在2012年宣布计划实现每天10亿小时的观看时间,并为此重新调整了推荐算法,而且在2016年实现了这个目标。根据鲁斯(K. Roose,2019)的梳理,2015年YouTube进一步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并于2017年进行改进,以期通过推荐相关度低的视频来维持更长的观看时间。
214
YouTube在达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调整了内容推荐算法来推荐那些能让用户观看更长时间的视频,但这些视频更多的是有争议的内容或有害内容。YouTube聘请了人工审核员对这些视频设置年龄限制,将它们从推荐播放列表中删除,甚至彻底删除了部分视频(Bergen,2019)。但由于种种原因,例如内容量大,难以在全球平台上协调言论自由的原则以及YouTube自身的商业和法律利益等,这些审核工作既不充分也没有效果。
有些疯传的视频不仅有争议,还比较极端。如果创作者知道做一些无耻的勾当能够获得更高的观看次数和收入,就会“玩弄”算法逻辑。当YouTube调整内容推荐算法,以便支持那些能够留住用户的创作者时,有害内容激增,其中包括饮食失调、疫苗、政治阴谋论、仇恨言论等内容,甚至出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热潮,例如“吃洗衣胶囊挑战”和“安全套挑战”,这些播主都在滥用平台的直播功能。自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以来,YouTube受到了大量批评,不仅因为它上传有害内容,还因为它公开推广此类内容。据称,YouTube上的大V亚历克斯·琼斯(Alex J ones)对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Goldm acher,2016)。
在《纽约时报》对YouTube首席产品官尼尔·莫汉(Neal M ohan)的采访中,记者凯文·鲁斯(2019)指出YouTube的内容推荐算法产生了“兔子洞效应”,这种算法可以帮助用户选择接下来看哪些视频,因此只要看一个视频,就会被“极端程度一点点不断提高的推荐视频淹没,最后才突然发现自己在看一些非常极端的东西”。正如鲁斯所说,观看一段唐纳德·特朗普的视频之后,用户“看到的推荐内容里的偏见也越来越多”(Roose,2019)。莫汉对此的回应是,最近平台的推荐功能开始用点赞来代替观看数量,并否认“兔子洞效应”的存在:
莫汉说:“我的意思是,当人们看完一个视频后,会看到许多推荐视频,其中一些视频可能会有偏向,或者也可以说那是更极端的内容。但还有其他的视频是相反的方向。再说一次,我们的系统没有那么做,推荐算法里没有这种逻辑。那只是你从表面观察到的结果。”(Roose,2019)
但鲁斯调查过迦勒·卡因(Caleb Cain)的案例并检验了自己的理论。卡因在大学辍学后就“掉进了极右翼的兔子洞”。他一开始看的是自己挑的视频,然后接收到越来越多的极右翼内容推荐。其他人也调查了Buzzfeed等媒体的情况(O’Donovan et al.,2019)。有5名记者从2019年1月开始在Buzzfeed上搜索新闻中的流行语(他们在调查时没有历史记录,每次查看都没有登录账号),然后播放第一个搜索结果并点击最顶部的推荐视频。他们得出的结论是:
215
结果几乎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但我们发现,YouTube的用户如果要在这个平台上获取新闻,那么根据皮尤研究中心(Smi t h et al.,2018)的数据,超过半数的用户没有从这种随意的推荐算法服务中获得良好的体验,因为这种算法似乎是由“参与度高于一切”这种标准驱动的。(O’Donovan et al.,2019)再如,在YouTube上搜索“弹劾母亲”这个关键词,它与美国国会女议员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弹劾混蛋”的言论有关,也就是弹劾特朗普(Villa,2019)。这个视频从CNN生成,素材是特朗普的新闻发布会录像。在点击观看这个视频之后,就会“突然进入右派的天下,包括一个来自保守派网站Newsmax的视频,名为‘比尔·奥莱里(Bill O’Reilly)解释为什么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是个失败的众议院领袖’。由此,YouTube开始推荐越来越多的右翼频道,例如YAFTV、亲特朗普的媒体专家迪内希·迪索萨(Dinesh D’Souza)的频道,最后是‘真正的自由’(True Liberty)和‘真正的美国保守派’(TRUE AM ERICAN CO N SERVATIVES)等频道”(O’Donovan et al.,2019)。
YouTube开始承认其推荐模式的确存在问题。根据一项来自彭博社的调查(Bergen,2019),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的几天里,一名员工提出了担忧,因为观看次数最多的选举视频来自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sart News)和亚历克斯·琼斯(Alex J ones)的信息战(Info wars)这种组织,而不是公正的主流新闻媒体。YouTube曾经打算把创作者报酬的标准改为观看次数和观看时间,而不是广告,但这可能会让亚历克斯·琼斯成为YouTube收入最高的一位播主。在这项计划流产后,YouTube开始打击错误信息。2020年2月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初选,YouTube宣布将禁止“深度造假”视频(篡改视频),以及任何包含可能影响政治进程的虚假信息和误导信息的视频(Bensinger,2020)。但专家认为这些措施的影响微乎其微,难以实施。正如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计算机视觉实验室主任吕思伟(Siwei Lyu)对《华盛顿邮报》提道:“检测这种视频在技术上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没有非常有效的算法来在这种规模的视频当中找出篡改视频”(Bensinger,2020)。而YouTube曾在2019年12月的博客中宣称,其算法有利于“权威内容”的传播,并且把“边缘”内容(例如阴谋论)的平均观看时间减少了70%(YouTube,2019),但博文中没有报告当时的收看数据。
216
专家依然认为,YouTube需要进一步阻止错误信息的传播。记者卡西·纽顿(Casey Newton,2019)为美国科技媒体Verge撰稿,她批评了《纽约时报》对YouTube首席执行官苏珊·沃西基(Susan W ojcicki)的报道,称其没有“承认‘灰色内容’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因为YouTube鼓励用户这么创作。因为平台上的视频资源无限,只有最引人注目的原创内容才会脱颖而出;但YouTube上最引人关注的视频,一直是那些让人感到震撼、愤怒和被冒犯的内容”。Vox媒体记者大卫·罗伯茨(David Roberts,2020)指出,YouTube的情况要更加复杂,因为该平台需要在不卷入“政治意识形态争议”的前提下打击错误信息,既要留住为平台带来利润的广告商和创作者,又要回应人们对有关内容的批评,以“捍卫自己的声誉”,他说,“我认为他们做不到”(Roberts,2020)。
思考题
1. 登录YouTube,搜索一个主题,点击一个视频并查看下面的推荐内容。你能看出推荐的模式吗?能找出推荐播放列表中存在争议或不可信的视频吗?
2. 思考你在YouTube上的体验,该平台推荐的视频能否让你留在平台上继续观看?该推荐系统为什么有效?
3. 你是否看到过YouTube推荐的奇怪视频?这些视频是什么,从哪个账号发出,为什么向你推荐?
4. 社交媒体平台有其推广内容的方式,请列举在这种推广模式下出现的流行观念或政治观念的案例。
5. 你认为YouTube等平台应该如何推荐和审核视频?这些平台可以在不采取政治立场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吗?
小结
本章探讨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平台媒体支持参与、赋权和民主的传播方式,但另一方面,它们采用了更密集的监视手段和控制措施。算法文化和参与文化环环相扣,恰恰是社交性产生的地方:社交被编码成有意义的文本、视频和图像流,同时也形成了数据。数据生成与平台处理数据的能力相伴相随,协同发展。平台的分类算法和推荐算法有其工具性的目的,亦即增加人们的参与度(Carah and Angus,2018)。今天,文化参与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成为数据库的编码员。我们是调整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训练平台算法是一种历史过程,是让算法感知、处理和优化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的人性、情感和感觉可以被机器读取。Facebook和Instagram等平台的基本任务是优化人类的感情和注意力,通过对软硬件工程的战略性投资,让机器对人类生活作出更及时、情境化和可操作的判断。算法文化的特点是开放性、实验性和持续的机器训练。其重点在于,我们要向媒介平台的信息处理开放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身体。 参与文化和算法文化中的权力来自那些组织、控制意义及数据流动的平台。
217
延伸阅读
延伸阅读所列文献探索了数字媒介平台算法文化中的政治参与。博格斯与格林(2018)介绍了YouTube的参与文化。本杰明(2019)和诺布尔(2018)批判了数字平台再生产、强化种族主义和不平等结构的方式。比舍普(2019)、科特(2019)和格拉德(2019)阐述了社交媒体用户如何学习想象、谈论平台算法,并总结了理论基础和操作方法。斯特理法斯(2016)对算法文化概念进行了基础的历史分析。
Benjamin, R.(2019).Race after technology:Abolitionist tools for the new Jim Code.Cambridge:Polity Press.
Bishop, S.(2019).Managing visibility on YouTube through algorithmic gossip. New Media & Soci-ety, 21(11–12), 2589–2606.
Burgess, J., & Green, J.(2018).YouTube:Online video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Cambridge:Polity Press.
Cotter, K.(2019).Playing the visibility game:How digital influencers and algorithms negotiate influence on Instagram.New Media & Society, 21(4), 895–913.
Gerrard, Y.(2018).Beyond the hashtag:Circumventing content moderation on social media.New Media & Society, 20(12), 4492–4511.
218
Noble, S.U.(2018).Algorithms of oppression:How search engines reinforce racis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Striphas, T.(2015).Algorithmic culture.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8(4/5), 395–412.
第九章
受众的生产与管理
媒体组织生产并管理受众。
★受众如何被生产出来?
★受众的工作是什么?
★平台媒体生产和管理受众的方式发生了何种变化?
219
本章内容
●考查生产受众的方式;
●解析受众的工作形式;
●探索在媒体聚集、监视和实时回应受众的过程中,受众如何变得更加碎片化和灵活化。
一、生产受众
媒体机构围绕战略性的受众生产来进行组织。专业传播者培养、引导、管理、细分并跟踪受众的注意力,这是媒体占据市场和塑造公共舆论的一个构成部分。其任务是让受众关注媒体、消费讯息并将媒介讯息整合进自己的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中去,管理受众参与观念创造和扩散。关于受众,可以提出四个基本问题:
220
1. 媒体对受众做了什么?
2. 媒体对受众意味着什么?
3. 受众如何使用媒体?
4. 媒体如何生产受众? “媒体对受众做了什么”这个问题,涉及媒体如何影响、塑造和培养受众的态度、行为、信念、行动等。 “媒体对受众意味着什么”或“受众用媒体做什么”这两个问题关注的是受众如何通过媒体的符号和文本来理解世界, 如何组织日常生活和构建身份认同。 运用媒体来形塑意义生产的活动是在受众的理性生产过程中展开的。
受众并非简单地存在于“那里”,而是由媒体制造出来并受其管理。生产受众需要大量资源,但正因为受众有用且有价值,媒体和专业传播者才去生产,把大量资源和创造力投入创造特定的受众类型。依靠广告盈利的媒体机构生产的是内容和连通性,但这并非最终产品,而是吸引人的注意力的筹码,借此才能把人打包成受众。商业媒体生产受众是为了将之出售给广告商。公营媒体、私营媒体、国有媒体和社区媒体生产受众是为了塑造文化和政治生活。
(一)媒体组织有哪些资金来源?
媒介系统是由许多群体的需求组装起来的。那些投入资源的人能够影响被生产出来的内容、形式和平台。媒体组织有以下几种资金来源:
●公共资助。政府资助媒体生产往往是为了构建国家身份认同,让观念和生活方式合法化,促进社会凝聚力。
●私人资助。富有的赞助者资助媒体生产,是为了更广泛的公共利益或特定的政治立场和抱负。
221
●受众直接资助。受众直接支付内容生产的全部费用 (例如书籍和音乐录制品)。
●受众间接资助。有些媒体通过广告盈利。这种模式的关键在于让广告商确信投资有回报,即受众会购买广告产品和服务。因此,媒体和广告商要证明受众正在看广告并会购买产品。而开展受众研究则是为了让受众的注意力和生产力产生有形的价值。
●混合资助。许多媒体企业会把上述模式里的要素混合起来,形成混合资助模式。例如,报刊通过受众直接付款和广告来获得收入。许多私营媒体则通过赞助商和广告盈利。
这些资助模式的共性是有目的地生产某种专注的受众,这种受众的价值在于能够服务于某些群体的商业利益或政治利益。
(二)测量受众与包装受众
通过广告盈利的媒体面对着两个产品市场:内容被出售(或提供)给受众,受众则被出售给广告商;受众在一个市场中是消费者,在另一个市场中是产品(Napoli,2016:261)。其商业模式有四个基本组成部分:内容、受众、测量和广告商(Webster,2014;Andrew,2019)。媒体生产内容是为了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因此需要测量受众,以便形成受众画像并出售给广告商。测量技术把无形的受众注意力转变为有形的特征,以便出售给广告商(Napoli,2016)。
媒体的竞争优势在于高效的内容生产、吸引有价值的受众以及打包受众的复杂测量技术。例如,体育直播和真人秀是成本相对较低但会吸引大量有价值受众的内容。大众传媒的测量技术由独立的收视调查公司和受众研究机构负责。社交媒体平台则是自己开发测量受众的技术,这种技术既能更加细致地打包受众,也能确保自己对测量过程的掌控。韦伯斯特(J. G. Webster,2014:76)解释道:
222
媒体测量技术从20世纪初开始发展,是广告商评估媒体价值的一种手段。报刊可以简单地通过印刷量来确定受众规模。但广播听众较为分散,隐藏在私人场所,就像传送广播信号的电波一样无法捉摸。因此,广播媒体要想打广告,就要知道听众是谁。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广播业在专门从事受众测量服务的新型公司那里找到了解决方案。正如我们后来所知道的那样,这些“评级”服务开发出抽样和统计工具来估计听众规模。有了这些信息,广播业蓬勃发展起来。电视出现后照搬了广播的测量方法。
受众测量和评级是一种“市场信息体制”。这些技术把观看和收听的社会实践转变为可以描述、估值和交易的产品。在平台时代,受众除了是内容的消费者和被销售给广告商的产品之外,还是内容和数据的生产者(Andrejevic,2002a;Napoli,2016)。受众本身开始在受众的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受众个体创作内容以供其他受众观看、生成注意力并将之打包售卖。受众生成数据,让媒体公司实时地测量、描述并销售其注意力。与之相比,在大众传媒的系统中,收视率根据历史数据进行预测,受众是用来描述和销售的标准化产品;广告商无法根据特定特征去定制受众,只能在不同媒体(电视频道、广播电台、杂志、报纸)所覆盖的受众范围里进行选择。广告商购买最适合目标市场的受众,但不可避免地要为许多“浪费的关注”买单。
随着媒体组织的发展及其制度化和商业化程度的提高,它们专门为广告商开发出了量化、描述和定位受众的方法。受众市场研究的技术和产业在与媒体合作中得以发展。收视率把受众打造为可以被出售给广告商的可靠的量化产品。受众的规模、位置和人口特征是量化的指标,方便广告商了解他们购买的广告时段或空间能获得多少特定类型受众的注意力。关于受众的质性信息和文化信息也很重要(Hackley,2002;Holt,2002)。媒体组织和广告商力求把受众的生活方式、文化兴趣、价值观和实践变成质性资料,同时为广告和媒体的内容制作提供信息。内容生产者想方设法地了解受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消费媒体内容,想知道诸如电视之类的媒体如何融入日常生活节奏。例如,早间电视节目满足了中产阶层家庭的晨间生活习惯,这些节目轻松简单,有较多的对话而且重复较多,适合观众早上准备上班或上学时收看电视的环境。虽然媒体制造受众往往是因为他们有商业价值,但这个过程也与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进程相互交织。在更广泛的层面,广告是媒体表征及媒体发挥社会作用的核心。广告和新闻、电影、书籍、电视节目一样,在塑造公共身份认同和社会形态方面发挥作用(Turow,1997:26)。把受众变为有价值的社会形态与创造公众以维持特定的政治形态和权力结构,这两者之间存在交叠(Livingstone,2005,2019)。
223
整个20世纪,媒体都在开发此类技术。比如,电视依赖家庭测量仪、日志和调查的组合技术(Balnaves et al.,2011:100)。但每种技术都有局限。只要人们打开电视,测量仪就会开始监测他们正在收看的节目,但无法确定家里的哪些人在看。有些研究公司设计出按钮测量仪,需要家庭成员在观看时按下按钮,这样就可以测出是谁在看电视。但如果人们不想透露他们在看什么,就不会按下按钮。日志提供了更多关于观众及其观看内容的详细信息,但人们一般很难准确记录这些内容,通常会低估花在媒体上的时间。此外,人们有时很难回忆起看了什么内容,也不愿承认看了哪种类型的内容,这也让调查受到了阻碍(Balnaves et al.,2011)。
测量技术的发展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例如,一些研究公司研发的屏幕能够识别观众,甚至可以辨识他们主动观看的程度及其生物反应(Balnaves et al.,2011:107)。但很少有人愿意参加这种测量研究。所有这些都表明,把受众打包出售是一种社会过程,因为这依赖受众的参与以及可用的资源、工具和方法。然而,受众研究方法对受众的商品化至关重要,传媒业正是运用这些方法来打包出售受众的。营销人员、广告商和媒体组织务实地创建关于受众的信息,采用包括人类学、统计学和神经科学在内的一系列方法,这些方法也能找出受众数据与其他人口数据之间的关联。
平台媒体在这些方法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可以持续且不让人察觉的监测技术,把人的观看习惯、社交网络和情感转变为数据。过去,我们一直站在受众的立场表达自己。如今,数字环境下的人类表达被收集起来,而且还能得到回应(Andrejevic,2013:42)。这些表达不仅是人类有意识的判断及意义生产,还包括他们使用媒体的模式和影响因素。例如,敲击键盘的速度、搜索模式、眼球运动等,都可能产生关于人的信息,甚至都不会让人察觉(Andrejevic,2013:96)。“情感经济的数据驱动控制”意味着“表达和传播的情感越多,就有越多的行为受到跟踪并得以累积,营销人员就越能引导、修复情感并将之转化为消费”(Andrejevic,2013:58)。构建越来越有价值、合理化和可定制的受众群体,有赖于让受众更加努力地工作,比如花费更多的注意力、生产更多的内容与更为频繁地互动,也需要建立一个全面的基础设施来捕捉受众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表达、观点和位置移动。
224
数字媒介系统把受众定制程序化,以便实时组装和销售(Andrew,2019)。当你访问网站或登录社交媒体时,你看广告的时间就已经被网站或社交媒体拍卖出去了。这种自动化序列要么是在平台广告模型中运行,要么是和广告程序交换机制一起运行。用户的个体信息会与特定用户的购买价格相互匹配。有一点可能特别明显:当你在一个网络商店浏览商品之后跳转到另一个网站或社交媒体,就会看到相同产品的推荐。广告交易程序会实时对你进行“匹配”,要么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广告模式,要么通过一种广告交易程序实现。在广告交易程序中,广告商自动出价购买那些看过、搜索过其产品或其他竞争产品的人的注意力。这种程序模型起源于大众时代用来优化媒体购买的计算模型;正如麦格根(L. McGuigan,2019:2367)的解释,“管理和利用数据早已是大众传播时代的紧要问题,当时对未来的设想是让计算机技术来协调信息和商业活动”。
虽然用户的“暴露”(exposure)依然重要,但有观点认为,平台只能向消费者提供更多精准的定制广告(即精细暴露,refined exposure)。如今,这种观点已经过时。因为数字平台营销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需要训练模型来聚合受众,也需要配置广告并优化受众与广告之间的关系。博格斯特与马德里加尔(I. Bogost and A. Madrigal,2020)指出:“‘Facebook广告服务’与其说是广告,不如说是制作广告的机器……Facebook的广告系统在获得起始信息之后,就会学习调整广告投放,并将之与其他所有广告商关联起来。简而言之,Facebook能够选择以什么价格向谁展示哪些广告。”
225
营销人员一般“了解”其目标对象,能够把精确的受众特征输入广告投放模型。这种高度规范的定位方式可能在早期的数字媒体中还有操作性,但现在这个过程变得更加动态化。例如,Facebook通常是先让广告商提供“客户受众”(Custom Audience)的特征,这是一种表现现有受众的数据集,能用来生成大量“相似受众”,亦即从“客户受众”向外延伸,把“相似受众”聚集起来形成“潜在受众”。平台会对这些“相似受众”进行实时测试,例如向他们展示不同的广告组合,监测其参与度和购买行为。品牌商则用分析面板、信号标和像素来跟踪消费者在接触广告后的行为。这些数据用于调整受众和广告,促成受众购买、推荐、点击、搜索、点赞或分享。在这个过程中,受众与广告之间的关系不断“精细化”。博格斯特与马德里加尔(2020:n.p.)指出:“Facebook上的‘广告’不仅仅是单独的图片或链接,而是把内容与潜在用户结合起来,从而引导潜在用户开展某种行动。”广告与受众之间的关联是由Facebook的广告模型自动生成、测试和完善的。这个过程开始时没有设定“目标”或“广告”,结束时也没有受众接触或受众测量;而是通过“客户受众”和一些资源来合成广告,不断优化受众与广告之间的关系。正如在Facebook的“广告库”里,许多品牌都有数百种几乎相同的广告,这些广告由“动态创意”广告工具(一种数据驱动的广告创作工具)合成,每个广告都针对特定的“相似受众”,是Facebook不断完善参与度的一部分。广告商上传资源(包括不同的视频、图像和文本),Facebook的广告模型测试各种元素的组合,通过不断迭代来找出最适合的投放目标。广告商在“市场”上调整广告类别和创意的时间越长,其参与度会变得越优化。
(三)受众为何有价值?
广告商和媒体组织协作无间,让受众的生产力最大化。而让受众更有生产力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他们看更多的广告。对媒体来说,受众看的广告越多,广告商可获得的收入就越多。但受众只会看有限的广告,只放广告的电视台最终只会门庭冷落。因此,媒体要优化受众规模、质量与广告量之间的关系。受众数量和质量的上升意味着他们更有价值;而广告增加则有可能让受众的数量和质量下降。因此,媒体在提高受众生产力方面存在局限性,这也是他们要不断创新管理受众的方式的原因。媒体发展的驱动力就是提高受众的生产力。
226
如果受众观看广告的数量是有限的,那么广告商和媒体就会提高总体观看时间的效率,从受众的注意力中榨取更多价值。他们有多种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
●精细化受众。集中那些广告商想要接触的受众,吸引具有一定收入和特定生活方式的人群的注意力。
●过滤掉广告商不想要的人。广告商不想为那些无用的受众付费,而且他们也希望可以区分目标对象,因为他们不想吸引那些用过其产品之后会降低其目标市场估值的受众。
●将广告整合到媒体内容中。从20世纪80年代的MTV到
今天
的真人秀和社交媒体,广告和内容相嵌的方式多种多样。这不仅增加了广告时间,也创造出了更多有质量保证的广告,让品牌不断融入人们的生活和身份。
●扩大广告形式和渠道范围。让媒体和广告更持续地融入日常生活。现在,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私人生活中,人们都会发现媒体内容。无论何时,我们的注意力都在被打包成商品售卖。
上面提到的每种策略无不扩展和深化了媒体内容的覆盖范围,创造了规模更大、参与度更高、更加细化且更有价值的受众。
(四)从控制表征到控制响应
在大众传媒系统中,控制受众建构的主要工具是内容和渠道,其中最重要的是表征控制。表征在身份和品位的结构中发挥作用,它们吸引一些人的注意力,并把其他人边缘化。表征是大众传媒吸引特定人群注意力,从而建构受众的主要工具。如果广告商想要接触年轻的中产阶层,媒体就会生产能够吸引这类人注意力的内容。除了内容之外,媒体还会通过形式和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内容的分配地点及分配方式。例如,一些期刊只会被投递给中产阶层社区或在优质商店出售(Turow,1997)。
227
正如表征传播着特定的意义,它也一直是一种关键的分类机制;表征在吸引一部分人关注的同时,也排斥了其他人。随着交互媒介的出现,响应性的控制机制开始被用来补充表征控制机制。这种媒介对受众的监控程度高度密集,能够根据许多变量来塑造内容(Andrejevic,2011;Turow,2011)。媒体组织可以用受众信息来塑造表征,并用日益复杂的方式来区分信息的接收者和内容类型,这进一步促进了受众的细分与定制化。
广告商不仅生产内容,也促进媒介系统的生产和文化生产(Turow,1997:186)。广告的媒体策划和财力影响着媒介渠道和媒介形式的发展。他们渴望把自己的讯息传递出去并将之嵌入特定的生活方式,这也影响了更广泛的媒介系统的整体形态(Jhally,1990),使得媒介的技术、内容和形式与广告共存(Hackley,2002;Bratich,2005;Turow,2011)。广告除了影响特定内容的制作以外(如真人秀),还会影响技术的发展以及那些实时管理和回应受众的媒体组织(如Facebook)。
媒体组织和广告商为了提高受众的生产力,开始创造出越来越细分的受众。如今,我们已熟知定制的社交媒体信息推送服务,但细分受众的过程在这种服务出现以前就开始了。图罗(J. Turow,1997:3)认为,技术力量和社会力量之间的结合给“社会整合媒体和细分媒体之间的平衡带来了重大转变。细分媒体指的是那些触及社会一小部分人的媒体,而社会整合媒体则是那些能够让所有细分群体相互对话的媒体”。20世纪的“广播”媒介系统,无论其产生是否只是出于偶然,都“将更大的民族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分享作为其关心的内容”(Turow,1997:3)。这部分是因为历史的偶然:当时的媒介技术(如报纸、广播和电视)只能生产有限的内容,且媒体组织的资源有限,缺乏技术和资源来为大量利基受众提供服务,而且即便广告商能够资助媒体,也无济于事,因为工业经济只能生产大量“一刀切”的产品。再者,媒体局限于追求社会凝聚力的政治形式。新兴中产阶层想要舒适的同质生活,政治阶层倡导的正是这些观念和价值。
228
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技术能力、工业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安排一直在发生变化(Turow,1997;Napoli,2010,2016;Webster,2014):
●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内容的生产传递可以触达多个利基受众市场。从有线电视到媒介平台,媒介渠道、设备和形式激增,越来越精细地为受众提供内容。
●宏观经济已经适应更多定制化的商品、服务和体验。即时而灵活的计算制造、全球零售经济的出现以及在线零售的增长,都极大地拓展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
●消费者具有多重利基市场的生活身份认同,而非大众阶层、文化身份或族裔身份。政治越来越围绕松散的身份组织起来,而非更广泛的阶层结构。
技术是产生利基受众的基础,已经成为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变化的一部分,创造出更灵活的经济以及更分散的身份、生活方式和政治。 商品生产和服务创新让市场对新的利基受众的需求大大增长。与此同时,新的受众及其生活方式和兴趣推动了商品服务增长,以满足其需求。于是,社会和市场同时碎片化(Turow,1997)。广告商的细分策略与西方社会更广泛的经济、种族、地区和生活方式的分裂相互关联。广告业和生活品牌不仅助推这些变化,也从中获利并对之进行回应。人们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新的郊区是为特定阶层及其生活方式而打造的;中产阶层不断吸收新的血液,成为强大的消费群基础。营销人员则视之为新的商业机会,同时也尝试利用媒介技术来创造更细分的受众。他们不仅在应对变化,也在进一步刺激和巩固这些变化。
(五)生产受众
在商业媒介系统中,受众是消费者:“消费社会的兴起有赖于激活媒介主体”,让消费者产生欲望(Bratich,2005:254)。对受众的生产管理需要各种行动者持续合作(Balnaves et al.,2011)。在媒体内容、产品和受众的生产过程中,营销人员、广告商、媒体组织和其他有影响力的社会机构相互促进、相互制衡。营销人员和媒体不断刺激和适应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变化;广告商则试图理解和塑造社会、生活方式、身份及对媒体的使用,并对其作出回应。他们对信息的利用有着务实的目的(Turow,1997:185),他们追求有商业价值的用户并据此来调整方法,但对其打造的社会并没有长远的积极的打算或规划。然而,他们需要与其他强大的社会机构和精英交流,因此其所在的媒介系统可能会务实地反映某些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而且他们也会务实地了解那些能创造更多有价值受众的特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229
广告商和媒体组织需要了解社会的运作才能开展业务(Turow,1997:186)。他们打造特定的受众,同时越来越多地观察和回应社会生活,以便不断组建最有效的受众类型。他们跟踪社会变化,对不断变化的技术、经济、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作出反应。广告商和媒体组织会观看、拍摄、记录、提问和跟踪受众,努力回应受众的文化身份和实践(Hackley,2002;Holt,2002)。他们“沉浸在消费者的生活中,在文化语境下更深入地认识、分析和理解消费者及其消费行为”(Hackley,2002:219)。广告反映并塑造了文化身份和实践。受众的发展也被嵌入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变革(Napoli,2010)。虽然公司可能会与其他强大的参与者一起回应和塑造受众,但他们无法控制这个过程,因为他们并不能完全支配那些创造新生活方式、导致新文化群体出现和改变经济政治权力配置的因素。不过,他们可以努力应对这些变化,让变化符合自己的利益。即便受众由媒体组织和广告商创造而来,但永远不会完全受其摆布,只不过受众生产具有不对称的特征,因为市场和媒体研究者一直在观察消费者,而不是反过来(Hackley,2002:220)。营销人员和媒体组织共同致力于定位和引导受众的生产能力。受众则是富有生产力的主体,他们形成欲望、传达欲望、相互影响并采取行动(Bratich,2005:254)。
二、受众与工作
2018年,Facebook在其“难题”(Hard Questions)系列下发布了一则帖子,解释了平台如何收集使用数据(Facebook,2018)。Facebook自问自答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230
问:如果我不为Facebook付费,那么我是产品吗?
答:不是。我们的产品是社交媒体,它能让你和你在乎的人联系起来,无论他们身处何地。这与免费的搜索引擎、网站或报纸一样。我们的核心产品是阅读新闻、查找信息,广告的存在是为这种体验提供资金。
问:如果Facebook不向广告商出售我的数据,Facebook会给他们什么?
答:我们出售Facebook上的广告空间,就像电视、广播或报纸一样。我们不会出售你的信息。如果广告商在Facebook上投放广告,我们会分享广告活动效果的报告。我们可能会告诉广告商的信息包括回应广告的男人多于女人、大多数人都在手机上点击广告。
这个帖子接着提出了Facebook经常提到的一个论点:数据能让平台“向你展示更好、更相关的广告”,这巧妙地掩盖了平台的“双重产品”本质。虽然“与人联系”可能是Facebook为吸引用户参与而提供的产品,但Facebook销售的真正产品是用户的注意力。此外,数据收集分析在创造、打包受众注意力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受众是一种社会建构。传媒业从受众当中提取的养分就是人的注意力。受众的社会行为具有生产性,他们是一种有价值的商品(Smythe,1981;Jhally,1990)。要理解受众价值,就要分析他们的行为。受众做的是两种工作:观看和被观看。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受众观看广告可以被视为一种生产性的工作,免费消费内容是给他们的回报,而且受众个体可以自由选择消费媒体的哪些内容和广告;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受众支付了两次,第一次是支付广告注意力,第二次是购买产品,其中包含了制作那些让他们“免费”消费媒体内容的成本。
(一)受众观看的工作
受众的观看活动涉及对表征的关注(Smythe,1981;J hally and Livant,1986;Jhally,1990)。其中不仅包括观看广告,也包括更广泛的、建构身份的媒体表征。受众从广告中获得关于品牌、产品和服务的知识,对此形成欲求,并学会对其进行分类。此外,受众还学习如何把这些内容融入自己的身份和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是,他们会去购买这些产品。此外,观看也具有更广泛的社会价值。看广告以及其他的商业媒体内容—如生活节目、戏剧或新闻—教会人们渴望特定的生活方式并形成特定的品位。当一个受众看到珠宝之类的奢侈品广告,或看到名人穿时装,或在好莱坞电影中看到昂贵的跑车时,他们可能永远都买不起这些商品,但他们知道这些东西很有品位且令人向往。受众对赋予这些商品社会价值和意义也有一定的作用。一定程度上,购买奢侈品的人想要获得别人的关注和渴望。正如一个有钱人买一辆昂贵的汽车,不仅是因为开车有趣,还因为这辆车让他与众不同。广告是一种社会系统,在根本上依赖我们的参与和交流。受众在观看广告时对此产生意义,从而令这种机制发挥作用。但毋庸置疑,广告无法保证受众能从中创造意义。例如,很多人都会观看奢侈品广告,但会与之保持距离。我们自以为能看穿广告的伎俩,会从自己的价值观、品位和社会地位进行判断,不理会广告的主张。然而,即便我们看透了广告的伎俩,但仍会关注、识别和理解它。就算我们看透了广告如何运作,它依然有效(Carah et al.,2012)。我们通过观看媒体和广告,根据其中的文化资源和观念来形成自己的身份、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大众传媒创造了有生产力的受众,受众运用这些文化资源而非固定的意识形态来创造意义。
231
(二)观看受众的工作
观看受众对灵活的互动经济至关重要(Andrejevic,2002a,2004)。媒介技术可以对受众进行排序和分类,而且能灵活地生产受众,因此其中的差异(例如定制商品和服务)是技术的必然结果。观看受众的工作包括两个关键要素:
1. 用户生成内容,指受众把自己及生活作为媒体内容供他人消费。受众参与真人秀和生活电视节目拍摄、在社交媒体上上传照片、评论新闻等,都是在生产和扩散媒体内容。受众的生活和社会世界也成为他们观看内容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用户生成数据,指向受众受到的监测和监视。人只要使用互动媒介技术,系统就无时无刻不在收集信息。受众在观看和生产内容的同时还产生数据,这些数据被用来合理规划受众的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