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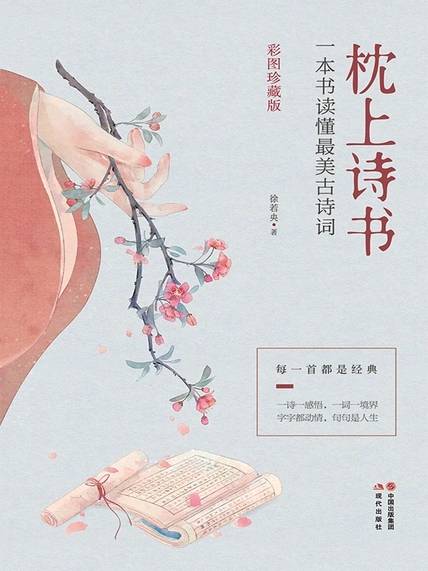 《枕上诗书》全文选用巫娜的音乐作品作为BGM
《枕上诗书》全文选用巫娜的音乐作品作为BGM
暮声电台:悠享读文
《枕上诗书》:一本书读懂最美古诗词
简介:精选《中国诗词大会》经典诗词,每一首都是经典,每一句都是情怀。字字都动情,句句是人生。一诗一感悟,一词一境界。诗是最美的文字,你是最好的自己。人生有许多的烦恼,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首诗词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首。

人生如梦,千古风流

1
北宋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苏轼写这首词时,他已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两年有余。
对于宦场沉浮、人生得失,他看得格外透彻,哪怕身处困顿,笔下的诗句也豪放不羁,宛如仗剑天涯的白衣少侠般潇洒。
黄州城外的赤壁矶,山水如画,苏轼与好友游于赤壁矶,清风吹拂着衣衫,望着那滚滚江水,大浪淘沙,他忽然想起乱世英豪——周瑜。
2
八百多年前,那位将军也曾站在赤壁之上,凝眸远望,指点江山。
舒城少年,出身士族,姿容俊秀,精通音律,擅抚琴。
一日,宴席之上,酒过三巡后,坐上之宾皆醉。
空灵的琴声缓缓响起,一弦一音,牵动着人的情绪。他们在琴声中,各自回忆着内心深处的旧事。
弹琴的女子也沉浸在琴音中,恍惚之间,指尖一颤,弹错了曲调。
女子慌乱地看向四周,生怕被主人责罚。好在旁人没有察觉,唯有周瑜转过头,深深地看向她。他的目光中没有责备,而是谅解。
周瑜对她淡淡微笑,如月光洒下一地清华。女子面色泛着微微红晕,娇羞地低下头,接着弹琴,音虽对,心却乱了。
3
后来,女子们时常故意弹错曲谱,只为博得周郎一顾。
自此,留下“曲有误,周郎顾”的典故,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
少年将军,雄姿英发,随孙策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江东初定,身为江东之主的孙策时时处于危险之中,幸有周瑜时刻守在孙策左右,不离不弃,护江东安宁。
两个人既是君臣,也是知己。江东双璧,一同出生入死,征战四方,在乱世风云中为百姓争夺太平之地,打下自己的天下。那时的他们不过二十左右,少年英雄,旷世奇才。
这乱世就好像棋局,棋盘便是江山,君君臣臣,每个人都是棋子,只有彼此信任,将一颗真心捧出,方能成就天下大局。
4
在江东,周瑜不仅找到了明君,还遇到了此生的伴侣。
都说“河北有甄洛,江南有二乔”,庐江乔公有两个女儿,风华于乱世,倾国倾城。然而,乱世中的女子命运从来由不得自己,还好她遇见了他。
小乔比姐姐幸运,姐姐成了孙策的妾,而她成了周瑜的妻。乔公府邸,姐妹两个促膝而坐,小乔抚琴作歌,大乔暗自神伤。同样的江南美人,甚至姐姐的容貌要比妹妹出众一些,此时却差距如此之大。
“小乔初嫁了”的完美姻缘不知迷倒了多少人,就连大乔也羡慕妹妹的红妆花嫁。鸳鸯盖头被掀起时看到的那张温和笑着的脸,小乔知道自己嫁对了人。眼前这个人就是传闻中的周郎,不似武将那般粗野,他行事细腻,又温和待人,乱世中能遇到如此郎君,当真是幸事。
她以为他常年征战沙场,一定是个嗜血的人。没承想,他待她如此温柔。她是幸福的,嫁对了人,爱对了人。
5
周瑜自见小乔的那一刻,便钟情于她。她美得温婉可人,一颦一笑都牵动着他的心。他爱极了小乔,恨不得把世间一切的美好都给她。她是流落乱世的红颜,他是乱世的英雄,他对她执着专一,娶了她后终身没有纳妾。这样专情的男子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在,都很难得。
他只愿与小乔一人白首不相离。他们是知己,是知音,琴瑟相和,不惧生死。即使是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心心念念的还是她。得此有情郎,人生又有何憾?他常常不在府邸,忙于征战。
她不后悔,有的人喜欢朝夕相伴的日子,但那些人大多过着平淡的生活。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她只愿点起一炷香,祈求神灵保佑他。
江边,残阳如血,周瑜望着江水东去,心中感慨万千。乱世中,他能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江山、美人,心中已然没有遗憾。
6
忽然,有仆人慌张地跑到他身旁,低声道:“孙将军打猎时遇刺,中箭身亡。”
长年的战乱,让孙策累积了不少的仇家,这样的结果周瑜早已猜到,只不过,没有想到这一日来得如此快。
孙策才二十五岁啊!他的抱负、理想还未实现,上天怎么忍心夺去他的性命?
灵堂内,周瑜伏在木棺前,泣不成声,可恨自己未来得及见他最后一面。对于旁人来说,过世之人是江东之主,可对于周瑜来说,那可是他此生的挚友。
孙策过世,孙权继位。周瑜依然留在江东,不负孙策临终重托,尽心辅佐孙权,守护着江东黎民百姓。
赤壁之战,周瑜主动请战。身为三军统帅,他博采众议,先用黄盖的诈降火攻之计,凭借江风,火烧赤壁。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在苏轼的笔下,战争不是只有兵刃与鲜血,还有一颗勇者之心。这场战争让周瑜一战成名,名震江东。
7
然而,天妒英才,他终究难逃英年早逝的命运。一颗星就这样陨落,历史没有留下过多的语言,只知道那是建安十五年,周瑜正准备出征,路上却患了重病,病逝于巴丘,年仅三十六岁。
江东豪杰,就这样离开乱世,着实让人惋惜。曾想过,若周郎没有英年早逝,这三国的天下可能是另一幅局面。
后人为周瑜写下无数的诗篇,还是换不回他的琴声。再也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儒雅,那样谦和。周瑜,还是成了史书上的一个名字。
一首《念奴娇》,成了千古绝唱。
赤壁有文赤壁和武赤壁两处:文赤壁在黄州城外,因苏轼的《赤壁赋》而得名;武赤壁在蒲圻县,东汉末年赤壁之战就是在此发生。
虽然名字相同,却绝非一处。所以,苏轼在词中强调“周郎赤壁”。
8
苏轼笔下的赤壁之战,万丈豪情,让人情不自禁地想重回乱世,与周瑜并肩而战。千载周公瑾,仿佛就在眼前,英风挥羽扇,烈火破楼船。
周瑜在乱世中收获了名与爱,可苏轼身处太平盛世,仕途却几经波折。他这一生最大的劫便是乌台诗案,只因写下《湖州谢上表》,便遭人诬陷,扣上了讽刺朝廷的罪名,无辜入狱。
在狱中,苏轼自知九死一生,早已为自己准备好了毒药,只等圣上的旨意。所幸官场还有真情在,经过好友搭救,总算被释放,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虽有官职在身,却没有实权,更无自由。不得签署公事,不得擅离安置所,过着如犯人般被拘束的生活。
苏轼羡慕周瑜的能力与机遇,更羡慕周瑜遇到了明君。被贬黄州后,他知道自己的仕途已然没有希望,从此,他只能做个闲散之官,领着朝廷的俸禄,却不能为百姓、为天下尽心。这样的他比那些落榜的考生还凄惨。
9
他寄情于山水,对于赤壁,他有种情有独钟的喜爱,面对着白露横江,水光接天,难得的云淡风轻。想到自己的处境,他从郁愤变得坦然,心中有愁,又一次次自我排解。
即便官场失意,对于生活,他还是充满希望。
赤壁,让他领略了千年的历史沧桑,也让他明白了生命的真谛。万物皆在变化,唯有日月星辰亘古不变,倘若身处困顿,就不必强求,倒不如与自然为伴。
很喜欢《赤壁赋》中的一段话:“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10
世间万物,不属于自己的不该去取,得不到的不能强求。江上的清风,听到了便成声音;山间的明月,看到了便成了形色。唯有这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此乃自然对人的馈赠,无穷无尽。
人生如梦,何必沉浸在苦闷当中?从始至终,他想要的不过是清风明月罢了。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苏轼品着清茶,此茶是甘苦还是清甜,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爱这茶纯粹的味道。天地苍穹,也不过是这浅浅杯中茶,弹指悠悠千载,瞬息万变,品不尽的是茶中的味道,道不完的是复杂的人生。
当心回归自然处,得也好、失也好,人生不过数十年,来去匆匆;成也罢、败也罢,转眼一切皆如烟,何必强求?尺寸之间,股掌之上,两千年的沧海桑田褪却了繁华,剩下的便是如水的平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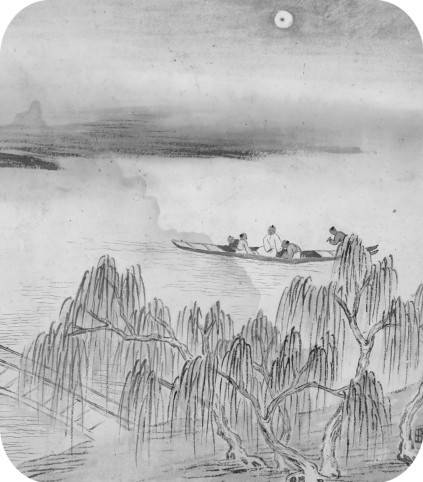

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1
北宋雨霖铃·寒蝉凄切——柳永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这一年,宋仁宗临轩放榜,看见柳永的名字,觉得甚是熟悉。
忽然想起柳永那首《鹤冲天·黄金榜上》:“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依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2
作词之人全然不将朝廷放在眼中,甚至宁愿把青春消磨在烟花巷,也不愿追求功名,对于科举制度,满是牢骚与抱怨。
想到这里,宋仁宗心中更是恼怒,斥责道:“且去浅斟低唱,何要功名!”
既然如此喜爱吟诗作曲,何必考取功名!不如就此归去,从此不要进京赶考。
柳永又一次落榜,并且仕途一片黑暗,宋仁宗的一句话,朝廷从此便不会录用他。
对于那首词,心中满是懊悔。当初,他不理智地写下“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酿成今日无法挽回的局面。若没有意气用事,或许他此时已经为官。
柳永失意地走在京都中,望着熟悉的街市,如此繁华,却与他无关。继续留在这里只会招来更多人的嘲笑,是时候离开了,去追寻自己的远方。
3
清秋时节,他决定离开京城,独自在客栈收拾着包袱,眼神暗淡无光,提不起半点精神。此时的心情极为复杂,不舍离开,又不得不离开。
原本简单的包袱,收拾了整整半个时辰。
临走前,又深深地望了眼自己住过的地方,虽是客栈,但他早已把这里当成了遮风避雨的家。
走出客栈,外面正下着雨,他与船家约定了时辰,不能耽搁,只好迎着风雨往长亭跑去。冰冷的秋雨落在他的身上,湿了衣衫,冷得彻骨,寒得入心。
他本以为不会有人来送自己,可长亭之上,却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
4
那女子穿着藕粉色的衣衫,窈窕又纤细的身姿,美目流盼,自有一股超凡脱俗气质,宛若皎皎明月。
她望见雨中狼狈的他,急忙撑着油纸伞迎了上去,口中责备他粗心大意,忘记带伞,可眼中满是关切。
他们来到长亭中,她拿起手帕,轻轻地擦拭着他额头的雨水。
这一举动,引起了周围人的不适。人们纷纷用鄙夷的目光望着她,大庭广众之下,举止如此轻浮,定然不是良家女子。
这些人猜得不错,她的确不是寻常人家的女子,很久之前,她便堕入青楼,每日搽脂抹粉,与文人饮酒作诗,早已习惯了旁人轻蔑的目光。她知道柳永离开京城有不得已的苦衷,自己无法挽留,只能来此送他最后一程。
她从来不在乎旁人如何看待她,她只想顺从本心,做真正的自己。她爱他,所以她来了,既然来了,又何必拘束?
5
他们相对而坐,听着雨声,深情地凝视着彼此。不需要过多的言语,此时无声胜有声,他们只想这样静静地待一会儿,想着往事,想着未来。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湿气,让人觉得有一丝伤感。傍晚时分,外面的急雨刚刚停下,雨声骤停,秋后的寒蝉叫得格外凄切、急促,仿佛在催促着离人远行。
饯行本该饮酒,一醉解千愁。二人看着眼前的酒杯,没有半点痛饮的心绪。昔日,他苦闷之时,总会与她对酌几杯,将心中的愁说与她听,此刻,他心中依旧万分愁苦,却不敢说,怕留给佳人难过。
毕竟,他是要离开的人,她是送行的人,怎么可以让留下来的人痛苦?
蝉声越来越凄切,船上的人已经等得不耐烦,催促着出发。留给两个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他们互相紧握着彼此的手,眼中含泪,依依不舍,谁也不愿放手。
6
这一别,可能就是永远。千言万语都哽在喉中,说不出,也不能说。此时,哪怕说一个字,便会泪如雨下,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要去南方,走过千山万水,与她天南海北各一方。长路漫漫,千里迢迢,从此以后,他只能独自望着楚地的天空,身边再无她的陪伴。
自古以来,最让人伤心的事情就是离别。人们不得不去经历,这种经历与苦难不同,人不会在经历中变得坚强,只会变得痛苦。
正逢萧瑟清秋,这离愁的苦让人如何承受!他拿起酒壶,将那整整一壶酒饮尽,可心中却没半分畅快,酒入愁肠,愁更愁。
他缓缓松开她的手,一步步离开她,上了船,不再回头。他怕自己回眸看见她的泪,便不忍离去。
她站在江畔,目送着那船越行越远,泪水模糊了双眼,无声地滑落……
7
船上,柳永坐在角落里,他不知道自己酒醒时身在何处。或许是杨柳岸边,陪伴他的只有清晨的微风、黎明的残月。
此去经年,若无知己在身旁,良辰美景,也如同虚设。心中的情,又能对谁说?
怕离别,更怕离别后的日子,没有她,一切又有什么意义?他写下这首词,是想将那夜的离别永远留在心中,将那段感情珍藏于心中。
这个女子究竟是何人?词中并没有写出她的姓名,想来必定是陪伴柳永多年的红颜知己,看着他寒窗苦读,屡屡落榜,却依旧不相离。同时,她也是可怜人,无人为她赎身,没有自由,无法跟随柳永一同远走。她只能留在这里,默默为他祈福,愿他一世平安。
柳永离开汴京,他去了许多地方,如同一个无家的浪子,沉迷于烟花巷,醉生梦死,不理世事。
8
他本出身官宦之家、书香门第,只可惜过分沉溺旖旎繁华。其实,这一生他并未放下功名,他一直辗转于各地,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通达仕途。在漫长的追寻中,他也留下大量羁旅行役之词。然而,他本身又是纠结的,既迷恋烟花巷,又放不下仕途,鱼与熊掌岂能兼得?正如宋仁宗所言:且去浅斟低唱,何要功名!
若一直这样矛盾下去,即便为官,也不会造福百姓。倒不如就此做白衣卿相,一生任性潇洒,无拘无束。
直到垂暮之年,柳永才及第,历任县令、判官等职,皆是芝麻小官,潦倒一生。临终之时,无家室,无财产,如此凄苦。最后,是一班名伎凑钱将他安葬。
相传,出殡那日,半城的名伎都去吊唁,红粉佳人褪尽脂粉,白衣素缟,为这位浪子垂泪。
9
古往今来,为歌伎作诗填词的人数不胜数,但终归是逢场作戏,没有尽心。唯有柳永,能将她们的情与爱描写得那般细腻动人。从“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到“故人何在?烟水茫茫”,每一首都是流传千古的情话,字字相思。
依然记得《金粉世家》中的一个片段,金燕西用一首《雨霖铃》缓缓地道出了冷清秋的名字,从此,一段故事开始。
一个富家公子,遇上了单纯的学生,不要以为王子爱上灰姑娘是浪漫的事情,那只是在错误的地点遇上了错的人。
在浪漫与爱情过后,留下的便是无尽的苦恼。金燕西负了清秋,两个人被婚姻折磨得遍体鳞伤,连相拥的力气也没用。
10
故事的最后,他们离开了彼此,这结局对二人来说是一种解脱,葡萄藤上开不了百合花。
爱不等于相守,一段婚姻,除了爱情,还有许多的东西,说不清,道不明,可能是柴米油盐,也可能是七年之痒。
遥想千年前,柳永离开汴京是否同样无奈又疲惫?他无法为那个女子赎身,无法给她幸福的生活,他似乎能预料到自己留在汴京,两个人以后要面临的压力。正因如此,他才选择离开。
他了解自己,他这样的人颓废半生,已经不可能成家。但那个女子不同,她的路还很长,她可以遇到良人,余生无忧。两个人会在各自的路上越行越远……
没有承诺,便没有责任。在彼此没有刻骨铭心地深爱前分离,这就是最好的选择,所以,那一晚,他离开了。
此生太漫长,长到他不敢去爱。红尘千丈,人的选择各有不同,不问对与错,只求无愧于心。


乱世佳人梦

1
南宋满江红·太液芙蓉——王清惠
太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曾记得、春风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馨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忽一声、鼙鼓揭天来,繁华歇。
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驿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碾关山月。问嫦娥、于我肯从容,同圆缺。
元兵的铁骑已经攻破襄阳城,一路南下,所到之处,满是鲜血与杀戮。山河破碎,国不成国,家不成家,纵然大宋有文天祥这样的英雄,此时也无力回天。
临安宫中,白衣素缟,嫔妃皇子跪在福宁殿前,神色哀伤。这一日,宋度宗驾崩,年仅四岁的太子赵显继位,全太后垂帘听政,风雨飘摇的江山交到了孤儿寡母的手中。
2
宫人们似乎感觉到大宋气数已尽,整日愁眉不展地望着天空,麻木地等待着国破家亡。
一个身着月白色衣衫的女子走出寝殿,独倚斜栏,手中拿着一卷泛黄的史书,愁眉不展。
这个女子是宋度宗的昭仪,王清惠。自从宋度宗过世后,便郁郁寡欢。宫人都以为她是忧思先帝,却不知她是在为国担忧。
忽然,远处传来一阵空灵的琴音,如幽谷中的泉水声,唤醒心底的禅意。
弹琴之人是汪元量,宫廷乐师,入宫多年,深受皇族之人的喜爱,每一弦、每一音,仿佛都在诉说着故事。
王清惠放下书,寻着琴音,一路来到回廊处,只见他席地而坐,低头轻抚着琴弦,一曲《高山流水》划过她的耳旁,如此熟悉。
这一刻,琴声让她忘却烦恼与战乱,仿佛置身于山野之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是她最向往的生活。
3
一曲过后,汪元量抬起头,恰好撞见她怅惘的目光,他心头一紧,想上前宽慰几句,却碍于身份不能过去,恐遭人口舌。
如果他们身在民间,或许会成为知音,毕竟,王清惠是这宫中唯一能静下心来听琴的人。
他们什么话也没说,彼此深深地望了一眼,便转身离去。
王清惠依旧每日独坐在宫中,听着宫人说一些外面的消息,隐隐觉得不安。
那年正月,没有任何一人沉浸在过年的喜悦中。金戈铁马,元军已经将临安城包围,国将破。
王清惠早知道会有国破之时,只是没想到这一日来得如此快,新帝登基不满两年,元军便兵临城下。
城内的将士已跟随文天祥拿起兵器,决定殊死一战,她虽是女流,心却如男儿般坚韧,早已为自己准备了三尺白绫,若战败,她便以身殉国,留一世清白在人间。
4
可惜,还未战,太皇太后便带着六岁的皇帝出降,如此懦弱胆怯地跪在元军统帅面前,丝毫没有皇族的尊严。
元军攻入临安城,掠夺宫中宝物,她目睹着国不成国,家不成家。
三千宫人做俘北上,其中便有王清惠。
她听闻汪元量也跟随北上,他一个琴师,原本可以逃出临安,不必随他们做俘,为何他要如此?王清惠想不通,却也没有问。
他们忍痛离开烟雨如画的江南,离开那充满回忆的地方。一路北上,路越走越远,风越吹越寒,望着身后被风月掩埋的脚印,王清惠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
杭州万里到幽州,一路上,她目睹了官吏残酷,百姓贫苦,半壁山河惨遭蹂躏,古道无人,满地狼烟,寒鸦的悲鸣传遍荒野,萋萋枯草在寒风中飘零。
5
她不敢相信这就是昔日的大宋,原本旖旎风光,此时却化为一片焦土。故国,家梦都不在。
脸颊一丝冰凉滑过,她落泪了,这泪为国而流,为民而流,为自己而流。
一方手帕递到她面前,她看了眼递帕的人,正是汪元量。这些日子,都是他在照顾她,她经历过男女之情,自然懂得汪元量对她的感情已经超越了主仆,但这份情,她实在不能接受。
命运未卜,她也许明日便会被元军赐死,所以,她不能给他希望。
元军途经汴梁,在驿站停留。夜里,王清惠梦到自己回到了宫中,与宫人们扑蝶赏花,正欢喜之时,忽然听到厮杀声,元军的刀剑已经落到了眼前。
6
忽而惊醒,再难入眠。她起身走到院子中,想到自己一路的所见所闻,在墙壁上题词《满江红》:太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曾记得、春风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馨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忽一声、鼙鼓揭天来,繁华歇。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驿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碾关山月。问嫦娥、于我肯从容,同圆缺?
皇宫太液池中的芙蓉花已失去往日的颜色,曾经,她陪伴帝王左右,春风雨露,玉楼金阙,羡杀多少人。一夜之间,繁华便戛然而止,亡国之恨,凭谁说!对着大宋江山,只能黯然落泪。
她想到梦中的情景,心中更是疼痛。如今,她沦为俘虏,命运已经注定。要么受辱求荣,要么守住贞洁。她望着月光,感叹道:于我肯从容,同圆缺。
嫦娥啊!请容许我像你一样,去过同圆缺的生活。国破山河在,让她一个女子何去何从?她要活着,也要守住自己心中的清明。
7
次日,汪元量看到墙壁上的词后,以词相和,《满江红》:天上人家,醉王母、蟠桃春色。被午夜、漏声催箭,晓光侵阙。花覆千官鸾阁外,香浮九鼎龙楼侧。恨黑风吹雨湿霓裳,歌声歇。人去后,书应绝。肠断处,心难说。更那堪杜宇,满山啼血。事去空流东汴水,愁来不见西湖月。有谁知、海上泣婵娟,菱花缺。
他的词除了怀念曾经的国,还怜惜现在的人。那一瞬间,他发誓要默默守护着她。
汪元量陪伴宋室王族在北方生活了十三年,王清惠时常会看见他独自站在城楼上,目光忧伤地望着南方,她知道他心中一直眷恋着故土。
江南,此时应盛开着九里香,不知九曲回廊处才子可还在等佳人,不知旧时堂前燕是否飞入百姓家,不知古巷里是否还能听到桂花糕的叫卖声。江南成了他们心底的痛,不敢回忆,不能回忆。
8
像汪元量这般风雅的琴师,本不该随他们来到这里,受尽北国风霜。如今,他已年近五十,该去追寻属于自己的生活。
王清惠数次劝他南归,汪元量深知她的苦心。他继续留在这里,并不能改变什么,也无法救她脱离苦海,无奈之下,他只能妥协。那年寒秋,汪元量上书元帝,请求归南,元帝应允。
此次分离再难相见,秋风萧瑟,雁南归,人亦归。
她的身份不便亲自送行,只能赠诗一首——《送水云归吴》:朔风猎猎割人面,万里归人泪如霰。江南江北路茫茫,粟酒千钟为君劝。
归途路漫漫,从此后,愿君安,愿吾安,愿岁岁年年不相见。
她的有生之年,再也无法看青砖黛瓦,再也无法赏临安初雪,再也无法听江南细雨。只希望汪元量可以代替她走遍万里江山,过潇湘,入蜀川,救济挣扎在苦难中的百姓。
9
汪元量回到江南,暗中结交志士,只为有朝一日,光复大宋江山,可以将她带回江南。
然而,王清惠终究没能等来汪元量。
他走后不久,她便远离世俗,褪下绫罗绸缎,抛却繁华,出家奉道。这是她最好的结局,洗尽铅华呈素姿,一心不问红尘中事,将前尘往事都看作过眼云烟。
陌生的北国,她始终一个人,独守着心中的眷恋。
在一个安静的夜里,她躺在榻上,想着记忆中江南、雨燕、故人,静静地合上双眼,永远地离开了尘世。
汪元量闻得她客死北地的消息,伤心欲绝,他后悔没有将心中的情思告诉她,恨自己没有能力将她带回江南,一切都太晚了。他并没有放弃,直到年迈,双鬓白发,再也走不动时,才隐居杭州。
10
晚年时,他时常会念着那首传遍中原的《满江红》,怀念着故人的音容笑貌。
王清惠的这首词还被人送去狱中,交给了当时被元军囚禁的文天祥。他与王清惠只有数面之缘,从未想过昔日那个醉卧帝王侧的王昭仪竟能写出这样满含悲痛的句子。
这首词,字字都是血泪,透过这些文字,他仿佛能感受到王清惠在国破时的无奈与悲伤。盛世如烟花般,转眼便消失,他们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岁月,宋已亡。
11
文天祥提笔,为王清惠翻作《满江红》:试问琵琶,胡沙外、怎生风色。最苦是、姚黄一朵,移根仙阙。王母欢阑琼宴罢,仙人泪满金盘侧。听行宫、半夜雨淋铃,声声歇。彩云散,香尘灭。铜驼恨,那堪说。想男儿慷慨,嚼穿龈血。回首昭阳离落日,伤心铜雀迎秋月。算妾身、不愿似天家,金瓯缺。
当时,不少文人都以词相和。一个柔弱女子的词唤醒了多少人,又让多少铁血英雄坚持到最后。
她的故事渐渐被人遗忘,千年后,又有谁记得这阕《满江红》?又有谁记得她的名字?
不求名垂青史,只愿天下长安。


问世间情为何物

1
金摸鱼儿·雁丘词——元好问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许多人初次看见这句话,应该都是在金庸先生的《神雕侠侣》中,当杀人如麻的李莫愁命丧绝情谷时,临死之际,唱的竟是这首《摸鱼儿》,凄婉绝望的声音,让人心生怜悯。
2
小说中的李莫愁面若桃李,话音轻柔,与小龙女一样容颜不老,若非知她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定以为她是位带发修行的富家千金。
其实,她本是单纯善良的女子,可一遇陆展元,便误了终身。
终南山上,李莫愁不顾男女之嫌,为陆展元疗伤,她将一片真心付出,瞒着师父与他偷偷订下婚约,并送他一方锦帕。
师父要她立誓不离古墓,可她一意孤行,被师父逐出师门。她以为可以等到陆展元归来,可落花有意,流水却无情。
陆展元,一个风流少侠,花言巧语俘获了少女的芳心,而后,又拈花惹草,遇到何沅君,移情于她,弃李莫愁而去。一念成魔。李莫愁因爱生恨,从此,性情大变,杀人如麻,她不再是那个温婉的邻家姑娘,而是无情的“赤练仙子”。
3
她听闻陆展元要娶何沅君,便去大闹婚宴,结果被高僧阻止,与他们定下十年之约,让那对新婚夫妻平安度过十年的时光。
十年,李莫愁可以等,她要亲手了结这段背叛的爱情。她在相思与仇恨中度过了整整十年,可当十年过后,再去陆家,陆展元已经病逝,而何沅君也自刎殉情。
深爱之人离世,她心里最痛,可越痛便越恨,她恨所有姓陆的人,恨所有与何沅君有关的事物,这恨伴随了她一生一世,没有随着时间而消失,反而刻骨铭心。
李莫愁,莫愁,心底的愁怎能消?她此生做过许多错事,已无法回头。绝情谷中,所有人都要她死,可她心性如此高傲,绝不会让别人了断自己的性命。
于是,她纵身跳入火海,在烈火中,凄声唱道:“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4
她对陆展元的爱,并不输于杨过和小龙女,只可惜,她爱错了人。情究竟是什么?让多少痴情人深陷其中,明知痛苦,却还是苦苦追寻。
元好问写这首词时也不过十六岁,还未到弱冠之年,却将爱情写得如此透彻。
那年,他赴并州赶考,路上遇到一个猎人讲述故事:猎人将捕到的大雁杀了,另一只逃走的大雁却迟迟不肯离去,不断发出悲伤的雁鸣声,最终坠地自杀。
元好问听后,心中很是感动,花钱买下这两只大雁,将它们埋在汾水岸边,垒石为记,名为“雁丘”,而后,又写下这首《摸鱼儿·雁丘词》,以此词纪念这段生死相许的爱情。
第一句便是对尘世的问,问世间,情是何物。纵观古今,多少文人雅士被情所困,一生无法参透情之真谛。生死相许,这四个字让人心生感动,也让人望而却步。唐玄宗李隆基对杨玉环如此深情,却也没有陪她共赴黄泉,到最后空留余恨在人间。
5
如今,十六岁的少年目睹了双雁的爱情,他不知如何歌咏,仿佛任何文字都无法将爱情表达,他只能发出深深的感叹:直教生死相许。
他无法用诗句表达爱情,却可以用事实证明爱情。“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这句话写的是大雁之间的日常生活,天南地北,从寒至暑,始终双宿双飞,不曾分离。他们一起享受喜悦,承担痛苦,经历过风风雨雨,心中的爱越来越深。他们就像人间的痴情儿女,其实,他们比人更痴情。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这句话是大雁殉情前的心理:看着那万里层云,千山暮雪,若没有挚爱在身旁,活着又有何意义?孤雁最是可怜,不会进食,不会饮水,只知低飞哀鸣。前路茫茫,孤雁无法展翅飞翔,唯有坠地殉情。
6
元好问将这对雁侣埋葬在汾水之上,遥想当年汉武帝曾率百官巡幸于此,箫鼓喧天,何等热闹。而今,这里已是一派萧索。雁死不能复生,山鬼为之悲鸣,双雁如此深情,连上天也会嫉妒。他们绝不会像莺儿燕子那样葬于黄土,他们的爱将会与世长存。他希望以后会有同自己这般的文人,来此寻访雁丘,祭奠这段爱情。
埋葬完双雁,元好问便启程。这一次,他并没有考中。
二十岁那年,元好问再次入京赶考,途中又听闻一桩事,河北大名府有两个男女,彼此相爱,却被家人拆散,两个苦命的有情人愤而投河自尽。那一年,河中的莲花并蒂而开。
7
元好问不禁想起了昔日自己亲手埋葬的双雁,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他写下《雁丘词》的姊妹篇,《摸鱼儿·问莲根》:问莲根、有丝多少,莲心知为谁苦?双花脉脉娇相向,只是旧家儿女。天已许。甚不教、白头生死鸳鸯浦?夕阳无语。算谢客烟中,湘妃江上,未是断肠处。香奁梦,好在灵芝瑞露。人间俯仰今古。海枯石烂情缘在,幽恨不埋黄土。相思树,流年度,无端又被西风误。兰舟少住。怕载酒重来,红衣半落,狼藉卧风雨。
依旧是对爱情的感悟,海枯石烂,生死相随。万物皆有情,双雁如此,人亦如此。
他仕途坎坷,一生漂泊,幸而有妻子张氏陪伴在身旁,风雨不离。
8
张氏离世后,他曾写下一首悼亡词《三奠子离南阳后作》:怅韶华流转,无计留连。行乐地,一凄然。笙歌寒食后,桃李恶风前。连环玉,回文锦,两缠绵。芳尘未远,幽意谁传。千古恨,再生缘。闲衾香易冷,孤枕梦难圆。西窗雨,南楼月,夜如年。
也许,张氏在世时,元好问曾带她去过雁丘,祭奠过那两只生死相许的大雁。如今,爱妻离世,元好问独留世间,孤枕难眠,夜夜如年。
晚年的元好问早已看破了官场风云,他辞官归隐,四处游历,只愿在山水之间寻求到真正的爱。
9
其实,爱情并非一定要生死相许,倘若人间还有值得留恋的东西,那么活着的人必须好生守护。然而,偏偏有人不懂这个道理,白居易就曾用“以死殉夫”的传统风俗逼死过一个女子。
那个女子名叫关盼盼,出身书香之家,长袖善舞,后来,家道中落,不幸流落风尘。徐州守帅张愔对她一见钟情,重金娶回家中为妾,甚是怜爱,为她兴建一处楼阁,名为燕子楼。
关盼盼与白居易曾有过一面之缘,张愔设宴,盼盼献舞,白居易也被那倾国倾城的舞姿所倾倒,为她写下诗句:醉娇胜不得,风嫋牡丹花。
两年后,张愔病逝,他生前的姬妾们纷纷离去,唯有关盼盼独守着燕子楼,回忆故人。虽是物是人非,可爱还未消散。
10
白居易听闻关盼盼独留人间,写下一首七言绝句:黄金不惜买娥眉,拣得如花四五枚。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
“一朝身去不相随。”分明是在以诗劝盼盼殉情,仿佛她不殉情,便是不节。人言可畏。关盼盼读诗后,含泪解释:自夫君过世后,她并非不想生死相许,只是怕后世之人议论夫君重色,让爱妾殉身,为了夫君的名誉,她才苟且偷生。
她回了白居易一首诗:自守空楼敛恨眉,形同春后牡丹枝。舍人不会人深意,讶道泉台不相随。
她没有选择,唯有死亡一条路。最终,绝食十日,魂断燕子楼。
生死相许是爱,相濡以沫是爱,难忘逝者亦是爱,爱有许多种,只要彼此心中欢喜便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