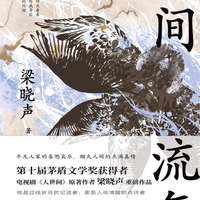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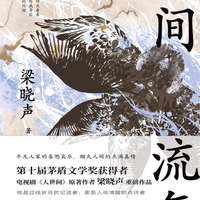
【梁晓声散文·人间流年】贰 分房那些事
1. 1949年以前的中国,也是有“福利”分房一说的。当然,能享受到此待遇的人,皆各级政府官员——并非一律有资格,以职务高低和贡献大小而论。
进言之,自从有国家以来,分“福利房”的现象,在许多国家便都存在着或变相存在着。不分房,也分地。而分地,意味着一片土地上所存在的森林、河段、地下的矿、地上的大宅,皆为受封之人所有,并且可以世袭。
许多人都知道的,英国相府唐宁街10号,便是某世英王赐给有功之臣的。只不过对方高风亮节,没要,建议当成议会的永久办公之地,后来成了首相府。
1949年以后的中国,从城市到农村,在接管各级政府,组建政权机构的同时,兴高采烈地所做的事之一也是“分”。
2.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这是农村之“分”的景象。民以食为天,分田分地乃革命向农民的首诺,便也是革命胜利后全面开展农村工作的首务。解决了农民拥有土地的问题,同时要解决农民的居住问题。连年不断的战争,造成了大批大批的农民失地。农民而无土地,自然亦无居所。如鲁迅笔下的阿Q,生前每在破庙中过夜。分田分地虽是首务,解决起来反倒相对容易。没有居所的农民众多,单靠将地主富农家的住宅分给他们是解决不过来的,于是寺庙、宗堂、经过改造的戏台,便也成为分给农民的居所。
如果说当年在农村进行的分房也算是一种“福利”分配,那么毋庸讳言,1949年迄今,中国农民仅经历了一次分房。当年的土改工作队,往往也没地方可住,只能在破庙里工作。
3. 1970年代时,中国农村有一位可敬的“支书”,叫王国福,是当年中央认可的模范“支书”。他的一句名言是“小车不倒只管推”,体现在他要带领农民过上幸福生活的恒心。当年没有“脱贫致富”这种口号。“脱贫”的提法,可能会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之成果的否定;而“致富”思想,尤其会被当成资本主义思想予以批判。当年的官方文字表述是——改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这一长句子,是断不可以缩短为“脱贫致富”四个字的。
而王国福的感人事迹之一是——要使全村人都住上新盖的房子(可以肯定,村民们的房子都不成样子了),在实现这一愿望前,自己家绝不搬出土改时分给他家的长工屋。
另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是——在1970年代的中国,只有少数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某些方面的改变,大部分农村的农民,仍像王国福那样,住在土改时所分到的居所里。
4. 一个相关联的问题随之而来——二十年过去了,为什么不建砖场,鼓励农民自行烧砖盖住房呢?
不可以的。
农村建砖厂,烧砖还只为盖住房,将被看成典型的带领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现象。
即使是王国福,他带领村民们所盖的也不是砖房,而是土坯房。并且,是顶着压力那么做的。关于应不应树他为模范,北京高层是有分歧,有斗争的。他的事迹终于得以被宣传了,是高层理性思想战胜极左思想的一次胜利。
某些过来人之所以对曾经主宰中国的极左思想深恶痛绝,原因也恰在于此——当年某些奉极左思想为圣经的人,他们对人民的愁苦生活是视而不见,极其漠然的。
5. 也正是在1970年代,周恩来视察延安地区的农村时,被眼见的贫穷景象所震撼,泪洒为他举行的送别宴上,泣曰——延安人民曾养育过我们,他们如今的生活竟是这么的贫穷,我们太对不起他们,拜托了!……
而邓小平,则在全国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上坦言——在有些农村,农民的生活与旧社会没什么两样,这种情况必须尽快改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到了2010年,又四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绝大部分农民,吃饱穿暖不是个事了。农民们的居住情况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要感谢水泥和砖两样东西,除了少数特贫地区的农村,此时中国大地上的农村住宅,已基本实现了砖瓦化。南方经济繁荣省份的农民,甚至住上了令城里人羡慕的“大别墅”,有的还盖得相当漂亮。
6. 城市周边的农民自家根本住不过来,于是出租,月月坐收数目可观的租金,那一般是城市上班族的工资的数倍,每令后者自叹弗如。然而,这绝非分配性质的福利房,而是农民们靠自家财力所建。若非言福利不可,也只能说沾了改革开放的光。
尽管如此,特贫地区的农民们的生活,仍令有所了解的人们感慨唏嘘。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栗战书在对贫困农村进行考察时,曾大动其容地说:“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也不算夸张,对农村的扶贫力度必须加强!”
综上所述,我们便明白了这样一点,所谓“福利房”之福利,虽是一个中国概念,与中国农民们却是从来不沾边的——它仅是一个与城市人有关的概念。
当然,此点人皆明了,但有强调之必要。
那么,“福利房”分配,在城市又是如何进行的呢?
7. 新中国成立后,分配住房首先面向的是各级干部,这一点也无须讳言。他们要开始管理和建设国家了,那就得先在城里有各自住的地方——现建是来不及的,房屋都是城市里原有的,无非易主一下而已。
如当时被选为国家副主席的张澜先生,在被敦促举家从四川迁入北京之前,国务院有关部门便要为他一家选择住宅。先生高风亮节,几次推拒,不肯入住较大宅第。后经周恩来亲自动员,以工作需要为劝词,才住进了一处不算太大,自觉住来会心安一些的宅院。
我的岳父是抗日时期参加工作的“红小鬼”,随部队进入北京后,率人接管了前门箭楼,之后因一时没分到住房,居然有几年以箭楼为家,后来定了行政级别才分到了正式住房。
8. 故可以这样说,新中国的第一次分房,主要是分给各级干部的,房源无一不是原有的。即使科长,也大抵会分到住房。只不过权属归公,仅有居住权。
当时之中国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没有稳定居所的流民甚多。为了便于城市管理,被一批批地劝回或遣送回原籍了。
当时的普通城市老居民,大抵住房狭窄。有的街区,环境脏乱差。新政府一时无力改善,仅能对恶劣的环境进行一定程度的治理——电影《龙须沟》反映了这一举措。在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中,也有反映当时上海底层人家居住条件令人同情的片段。故,可以如是想——话剧《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和小福子等底层民众,解放前所住的那处拥挤破败的院子,解放后他们必然还住在那里,直住到1990年以后的房地产业兴起,大拆迁时代来临。而《七十二家房客》中的那些人家,也不可能在1990年之前搬离该幢危楼。
9. 工厂里的工人,虽然总体上被定义为“领导阶级”了,但终究不是革命干部。任何一名具体的工人,也就绝对不可能享受到只有干部才能享受到的任何待遇。在分房一点上,更无例外。
何况,当时之中国,工业落后,真正的工厂工人为数不多。在有的省,有的市,属于“小众”群体,还算不上是城市人民中的多数。政府关怀的温暖,也不可能优先向他们倾斜。
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工资,从此有了稳定保障。即使某一个月或几个月欠发,补发不成问题。
10. 1958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大力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机械制造业提上国家发展日程,工人群体迅速扩大,中大型工厂多了,中国工人的居住状况相应地获得了改善——但新建的中大型工厂一般不在市内,而在市郊。即使出现于市内,也是建在人口相对稀少的非重点区。
于是,中国此后出现了城市工厂区、市郊工业基地。以东三省为例,先后建起了沈阳重型机械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黑龙江省的富拉尔基工业基地。再以哈尔滨为例,列车制造厂挂牌了,轴承厂挂牌了,量具刃具厂挂牌了,拖拉机制造厂挂牌了,锅炉厂、电机厂也挂牌了。在市郊,出现了香坊工业区、平房工业区、“哈一机”工业区——它实际上是造坦克的军工厂。
又于是,一片片工人宿舍区产生了。
11. 另一方面,教育、科研、医药医疗、新闻出版、文化艺术等单位也长足发展,便不可能不解决骨干队伍的居住问题。
在各行各业全面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特色的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特色的“福利房”分配拉开了帷幕。
工人宿舍,普遍是砖瓦平房。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也普遍建得简陋粗糙,绝大部分没有上下水系统,更不可能有室内卫生间——几十户人家共用一处公厕,公厕尤其简陋粗糙,与今日之城市公厕完全不可相提并论。北方的工人宿舍也无取暖设备,分到宿舍的人家皆砌火炕。面积大抵三十平方米左右;一间二十平方米的里屋和十平方米的外屋,外屋兼做厨房。以当时的国力和应急做法,只能建成那样。
12. 即使在北方,也非所有的工人宿舍都是砖瓦房,所谓“板夹泥”的更简陋粗糙的宿舍不少。当年的分配原则是——四口之家且无大儿大女只能分到一处宿舍;五口以上人家可多分半间小屋,当年的说法是“一间半”。小儿小女总是要长大的,长大了而又迟迟轮不到二次调房,居住情况就特别尴尬。通常是长大了的孩子住到外屋去,故“50后”普通工人的儿女,许多人是每晚睡在厨房度过青春多梦期的。而若一户工人之家有一儿一女,儿女之间又只不过相差一两岁,那么或儿子或女儿,每晚就只能与父母同炕而眠了——尴尬就尴尬在此,对父母和儿女,都多有不便。
事业单位因为普遍在市区,所以事业单位的宿舍多是楼房。但也不是每户人家都有室内卫生间,一个单元有一处公厕就不错了,上下层人家共用。好在当年的宿舍楼都不高,一般三四层,最高五层,六层甚少。
13. 在那样的楼里,常见令人难以想象的现象——如厕往往也排队。若家有卧床不起的老人、病人或孩子,便也须备有屎盆尿盆。还有的楼房,因为建时做不到配备暖气设施,便也只能靠烧煤做饭取暖——楼道堆满家家户户的煤球;冬季里,楼顶的烟囱终日冒着煤烟。
事业单位知识分子们的分房标准,与工厂的分房标准相一致。
粥少僧多,事业单位和工厂的分房原则,都不可能不论资排辈。而如果事业单位是处以上单位,工厂领导是处以上干部,头头脑脑大抵不参与本单位本工厂的分房,另有条件好的住房分给他们,曰“组织部门分房”。
14. 当年,关于分房的故事或事故,每在民间口口相传,是人们喜谈爱听的话题之一。事故自然是不好的故事,不好的故事往往传播广泛,如跳楼的,好同事好工友之间反目成仇的,持刀威胁领导干部的,精神受刺激疯掉的……从社会心理学上分析,人们喜欢传播那样的事,其实意味着对“公平”二字的重视。
而普遍的情况是,当年的分房基本上是公平的。不论在工厂还是在事业单位,只要分房,必成立各级分房小组,也必走群众评议的民主程序,众目睽睽,而且有论资排辈的种种详细规则在那儿摆着,想搞分房唯亲并不容易。
但同等条件之下,几个人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人中,房源有限,分给谁了没分给谁,一碗水端平亦非易事。这时候,分房小组领导对谁的印象如何起决定性作用。而某领导最后一拍板,自己也就陷于引火烧身之境了。
15. 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某人该分到住房实际上没分到,领导保证下次一定优先考虑某人;某人也颇顾大局,没闹,觉悟很高地期待下次分房。终于盼到了下次,领导换了,比某人更具备分房资格的竞争者产生了,新领导不理前任领导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了,某人岂能不大光其火?于是矛盾激化了。
在涨工资的事上,不乏师傅为徒弟争,徒弟为师傅争,不少人为一个人争的例子。那时,“公平”还体现为正义。但,在分房问题上,人人都为自己争,争不到替自己倍觉委屈成为常态;为他人争,替他人鸣不平的事不能说完全没有,有也不多。毕竟,涨工资所争,无非每月多七八元钱少七八元钱的事。而住房,关乎一家人更基本的生活质量,不由人不争。此次争不到,下次再分是猴年马月?也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了——这是很多中国人当年在分房时所产生的心理恐慌。情形好比如今上班打卡的人们挤向地铁或公交车——想想看,若眼前是最后一班地铁或公交车,自己挤不上去,须有多么强的心理素质才会处之泰然?
16. 当年,在分房问题上,劳模、先进生产者,这种那种标兵,有突出贡献者,一向是被优先考虑的。即使不优先,也必加分。而当年的中国人,对劳模特别尊敬,几无攀比之人。
故像王进喜、孟泰、马永顺这样的全国劳模,都是较早住进“福利房”的人。当年的劳模,自我要求甚严,绝无在个人福利方面提任何优待要求的现象。关于他们的一切资料显示,他们的住房标准,与本单位本企业普通工人的住房标准毫无区别。此三位全国著名的劳模中,唯马永顺活到了房改之后。因为他家当年的住房情况就极一般,房改后便无个人益处可言。何况他家所住一直是林区工人的宿舍,如今也根本不值钱的。
因为我父亲是三线工人,母亲和我们几个子女不是随迁家属,我家便从未经历过“福利”分房,所住一向是房产属于私人房东的破败老屋;1960年经历了一次动迁,面积大了几平方米,仍是贫民区简陋粗糙的住房。
17. 1968年我下乡后,连队的老战士多为1966年集体转业的军人,他们所住应算是“福利房”——连队统一建的土坯房,每户一间住屋一间厨房,总面积三十几平方米。指导员参加过抗美援朝,唯他家住屋大几平方米。指导员的儿子和副指导员的弟弟都已是成年人,住在我们男知青宿舍。连长与家属两地分居,所以没住房,与知青通讯员同住连部里间的小屋。
我曾问过指导员——咱们兵团不像农村,可供农民盖住房的土地十分有限;咱们的连队四周是广袤旷野,人们为什么不勤劳一点,将住房盖得大一些呢?你看家家户户的老战士,如果有了儿子,也将父母接来了,都住得多不方便啊!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号召大家义务劳动大家也愿意嘛。
18. 指导员的回答是——不是勤劳不勤劳的问题。国家每月给我们发工资,如果我们为了都住得宽敞点儿,把劲儿用在住房方面,那肯定不对,会受批评受处分的。
确实如此。有的连队,因为将住房盖得大了几平方米,指导员连长双双受处分,还通报批评,以儆效尤。
问题是——我们是在北大荒,不是在城市,不存在公地私占的性质。在极左思潮统治人们头脑的时代,任何提高个人生活品质的做法,即使并不侵占国家或集体或他人利益,那也是不允许的。
我从连队调到团部后,见团里干部们的住房条件也不比连里强多少,所住是砖瓦化的平房罢了。我们宣传股股长是现役军人,他家小孩子多,分到的也是一间住屋的住房。他有时嫌家里闹,宁肯在我们知青宿舍借宿。副政委是原农场老干部,三个女儿都已成年,也只不过住在有两间住屋的平房。
19. 如今想来,即使在“广阔天地”,当年那种严格限制住房标准的制度,也不是完全没有其合理性——我们毕竟是生产建设兵团,存在的使命是多收获粮食,倘都比着将个人家园建得好些,全兵团就可能会在一个时期内变成“住房建筑兵团”了。何况,那时是备战年代,兵团地处北疆,战争一旦爆发,再好的家园也会毁于炮火之中。这一点,也决定了人们对住房的要求是——能凑合着住就行了。
我上大学后,我复旦老师们的家,也都是一室半的矮层楼房,面积都不超过四十平方米。当年一半左右的老师分不到住房,只能四处租房子住。
那时上海的大龄未婚青年多多,十之八九因为没有婚房结不成婚。有不少对恋人相爱久矣,最终还是因住房问题解决不了,彼此依依不舍而又明智地分手,这一点与如今工作在“北上广深”的外地青年们的处境十分相似。
20. 如今的青年租房已非难事,当年则不同,年轻人的工资普遍才三十几元,而在市区租一处小住屋也得三十元左右,若再有了孩子,日子没法过了。租郊区农民的房子自会便宜些,但当年交通又不发达,班也就上不成了。
当年,只要算是一座城市,都有类似现象——不分男女的某人正上着班,却忽然吞吞吐吐地要请两三个小时的事假——后来当头的心领神会了,特别痛快地同意——夫妻双方约好了,各自按时请假,好赶回家去弥补一次性生活的缺乏。夜夜与非是小孩子的儿女同室而眠,只得白天请假回家满足一次夫妻双方的生理需要。据说,在上海,在夏季,在某些公园,有夫妻双方带了小帐篷留宿于公园里的事。但,须揣上结婚证。否则,被巡逻的公园管理员发现了,也许会被双双扭送到派出所去。
21. 我从复旦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因没有宿舍床位安排我住,我只能在招待所住了半年。半年后,破例分给了我一间十一平方米的小屋,在筒子楼内。所以破例,乃因我占了招待的一张床,影响招待所收入。
多年内,那小屋成为我的家,儿子在那个小家一直成长到上小学。
我在北影经历了第一次分房,我家由筒子楼的这一头搬到了那一头,面积也由十一平方米扩大到了十四平方米。此次分房,得益于老艺术家们。此前,谢添、陈强、于洋等老艺术家,也都住在小西天太平胡同的大杂院的老平房里,那些平房潮湿阴暗,终年缺少阳光;而且,他们的住房面积也都不大。北影遵照文化部指示,首先为他们盖了一幢“老艺术家楼”。而于洋由于当年还不老,竟无那幸运,仅搬入了一套七十余平方米的小三居旧楼中。
22. 老艺术家们的住房条件一经改善,他们腾出的住房便可分给别人。于是,小范围内的北影人进行了一次住房周转,我成了那次周转的既得利益者。
当年,有两位中年导演是我的朋友——许雷和都郁。他们的爱人,都是芭团主力演员。北影没分给他们房子,他们沾妻子的光,住的是芭团分给她们的结婚房。两位朋友的家我都去过,都十四平方米左右。除了张窄双人床,一张小桌两把椅子,再就摆不下别的家具了。那种窄双人床,也可以用如今宽单人床的概念来说。若夫妻双方一方较胖,夜里另一方会经常被挤到床下。
我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走南闯北与工友们建过许多楼,退休后又住回到我家在哈尔滨的老房子里了,那房子已下沉了将近半米,窗台快与地面齐平了。
23. 父亲第一次到我北影的家时,感慨良多地说:“儿子你有福气呀,刚参加工作就分到了福利房,这是多大的幸运啊!”
我也承认自己很幸运,但却是多么脏乱差的筒子楼呀!公共用水池那儿,脏得简直令人望而却步。以至于访问我的日本老翻译家要解手,我带他去到公共厕所后,他在门口往里看了一眼,不肯进入。没辙,我只得再带他走十来分钟去往办公楼——办公楼的厕所相对干净些。
1988年,北影又盖起了两幢没电梯的六层楼,专为中年艺术骨干盖的。这一次,周转的范围大了,竞争也激烈了。握着菜刀拎着斧头闯领导办公室的事确实发生了——某些势在必得的工人为了多争到一间周转平房失去了理性。而好友都郁恰在那一年病故,没能在新楼里住上一天。
24. 就在那一年,我调入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童影当时是新单位,1982年盖起了一幢六层宿舍楼。我去时,七八对年轻夫妻两家合住一个单元,五十四平方米;住小间的人家优先使用小小的饭厅,共用厨房厕所。为了对我表示欢迎,童影将留作招待所的一个单元分给了我。而我从北影调往童影,是为了住房相对大点儿。当时我父亲患了癌症,我要将他接到北京治病,并要实现他希望生前与我共同生活一段日子的想法。
我的父亲于1989年秋病故。
童影于1994年又盖起了一幢高层宿舍楼,但只有几层属于童影,是童影出地皮,别的单位投资的互利互惠性质的“合盖”。虽然又有了几层宿舍,仍不够分。
25. 当时我还是分房委员会委员,为了化解分房僵局,我竟亲自将童影交给电影局的一把宿舍钥匙要了回来——当年广电总局有规定,各电影厂盖了新宿舍,理应支援电影局几套,帮助局里改善同志们的住房困难问题。当年局里的同志都说——那种事只有梁晓声敢做。
2002年,我调入了北京语言大学。
人事处负责为我办手续的同志问:“有住房要求吗?”
我说:“没有。”
他说:“其实你可以提出要求,趁现在学校还有房源。上次分房保留下来几小套,专为后调入的教师保留的,估计保留不了多久了。”
我仍说:“没住房要求。”
26. 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有一部获奖电影《邻居》,内容是反映高校教师住房窘况的。十四五年过去了,虽然中央加大了解决高校教师住房困难问题的力度,各高校一盖再盖宿舍楼,但高校教师队伍也扩大了几倍,总体情况仍是粥少僧多。
情况是我所了解的。
当时我想,童影厂分给自己的住房已属于厚爱式的待遇了,岂可脸皮太厚,在北语再插一脚?
果不其然,不久便有教师们纷纷找到我,向我申述困难,以种种理由要求增加住房。因我当时已是全国政协委员,他们希望我能替他们主持公平与正义。他们的眼,全都盯着那几套保留房呢。幸而我没要,否则肯定刚一入校就成为众矢之的。
27. 其实,我将他们的申述听下来,所得却是这么一种印象——什么公平啊,什么正义啊,还不是因为粥少僧多吗?在此前提之下,神仙也无法分配得绝对公平合理啊!做不到绝对的公平合理,当然也就遑论绝对正义了!
现而今,所谓“福利分房”早已成为历史,房改也已实行多年。更确切的说法应是——房改终结了“福利分房”这回事。屈指算来,此事曾在中国的城市里断断续续地实行了四十余年,是留在几代中国人头脑中的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深印象之一。
对房改的是非功过,至今众说纷纭,但一个事实恐怕是——今日之中国,城镇人口已超过农村人口,有七亿几千万之多了。对数量如此庞大的人口依然实行福利分房,中国还做得到吗?
28. 某些对中国持今不如昔之看法的人,每将从前的时代描绘成理想时代,似乎中国人曾经历过比今天幸福指数高的岁月——他们每以福利分房为依据。
然而他们成心避开了这样一点——在1980年代前,究竟有百分之几的人享受过福利分房的福利?又有百分之多少的人至死也没享受过那种福利?两者之间哪种人多,哪种人少?当年的福利房,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又只不过是什么样的房?更多的中国人,是否在1990年代后,才逐渐分到了较像样子的福利房?而1990年代的中国,是从前的中国呢,还是后来的中国呢?
29. 估计全国平均一下的话,当年可能百分之一都不到的中国人才有幸分到的福利房,是不是后来都成了垃圾房、危房,被一大片一大片地铲除了?再后来,更多的中国人家,是不是在棚户区拆迁中才住进了有上下水和供暖供气设施的楼房?
至于商品房房价根本超出了普通百姓人家的购买能力,那是另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要由另外的措施来解决,不能成为今不如昔的论据……
--持续更新--
【梁晓声散文·人间流年】系列:①779494
【梁晓声散文·人间处方】系列1–8文本号:
①164067 ②580909 ③404913 ④352975
⑤429399 ⑥634739 ⑦421933 ⑧420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