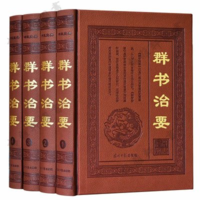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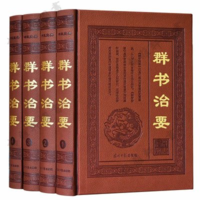
02
原文道径(1)众,民不知所由也;法令众,人不知所避也。故王者之制法也,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旷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隐远方,折(2)乎知之,愚妇童妇,咸知所避。是故法令不犯,而狱犴(3)不用也。昔秦法繁于秋荼(4),而网密于凝脂(5),然而上下相遁,奸伪(6)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烂捌(7)焦不能禁,非网疏而罪漏,礼义废而刑罚任也。方今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群国用之,疑惑或浅或深,自吏明习(8)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乎?律令尘蠹(9)于栈阁(10),吏不能遍睹,而况愚民乎?此断狱所以滋众而民犯禁滋多也。亲服之属甚众,上附下附,而服不过五(11);五刑(12)之属三千,上杀下杀,而罪不过五。故治民之道,务笃于教也。
注释(1)道径:道路。(2)折:判断。(3)狱犴:亦作“狱豻”,牢狱。犴,音暗。(4)秋荼:荼至秋而繁茂,因以喻繁多。(5)凝脂:凝冻的脂油。因无间隙,比喻事之严密,多指法网。(6)奸伪:诡诈虚假。(7)捌:同“扒”,破裂;分开。(8)明习:明了熟习。(9)尘蠹:被尘土污染,蠹虫蛀坏。形容陈旧破烂。(10)栈阁:存放东西的屋子。(11)服不过五:超不过五服。五服,封建社会规定的丧服制度,依照亲疏关系,分五等孝服和守孝时间:斩衰,服三年丧;齐衰,一年;大功,九月;小功,七月;缌麻,三月。(12)五刑:五种轻重不等的刑法。秦以前为墨、劓、剕、宫、大辟;秦汉时为黥、劓、斩左右趾、枭首、菹其骨肉;隋唐以后为死、流、徒、杖、笞。
译文道路多了,人们就不知道该走哪一条;法令多了,百姓就不知道怎样避免触犯法禁。因此,圣明的君主制定法律,如同太阳和月亮一样昭明,所以百姓不会迷惘;如同大路一样宽广,所以百姓不会疑惑。即使是再隐蔽、再偏远地区的人,通过判断也能了解法令;愚昧无知的妇女儿童,也都知道怎样回避犯法。这样,没人违犯法律和政令,监狱也就没有用处了。从前,秦朝的法律比秋天的茅草还多,法网比凝结的油脂还细密,然而上下都能逃过制裁,奸诈虚伪的事层出不穷,有关官员惩处这些,就像挽救腐烂之品、分开烧焦之物那样困难。这并不是法律松弛、罪犯漏网造成的,而是废弃礼仪、滥用刑法的结果。现在制定的法律和政令有一百多篇,章目繁琐,罪名众多,就是各郡施行起来,多少也会感到一些疑惑不解,定罪时或轻或重,就连通晓法律的官吏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何况那些无知的百姓呢!法律与政令的典籍被尘土覆盖、被蠹虫蛀坏,放在阁楼上,连官吏都不能全部过目,又何况无知的百姓呢?这就造成要决断的案件越来越多,百姓犯法也日益增多了。穿丧服的亲属很多,按亲疏关系分别穿不同的丧服,但丧服的种类最多也不会超过五种。五刑的条例多达三千余条,但上下比较、归类,也不过五种刑法。所以,治理百姓的根本方法,在于务必加强礼仪的教育感化。
申 韩
题解本篇实质上依旧是关于“法治”和“礼治”问题的辩论。贤良文学指出,治国者当以礼制、良吏为要。良吏如良医,败吏如毒草。良医明察体气盛衰而针石刺肉,败吏构法陷害忠良,祸国殃民。指出为政者应以仁义为本,善用法制,勿使之成为禾田中之毒草。
原文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贵良医(1)者,贵其审消息(2)而退邪气也,非贵其下针石(3)而钻肌肤也。所贵良吏(4)者,贵其绝恶于未萌(5),使之不为非,非贵其拘之囹圄(6)而刑杀之也。今之所谓良吏者,文察(7)则以祸其民,强力(8)则以厉(9)其下,不本(10)法之所由生,而专己之残心(11)。文诛假法以陷不辜(12),累无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13)惊骇;十家奔亡,若痈疽(14)之相漫;色淫之相连,一节动而百枝摇。诗云(15):“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沦胥以铺,伤无罪而累也。非患铫锄(16)之不利,患其舍草而芸(17)苗也;非患无准平(18),患其舍枉而绳直(19)也。故亲近为(20)过不必诛,是锄不用也;疏远有功不必赏,是苗不养也。故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也。
注释(1)良医:医道高明的医生。(2)审消息:审,详察。消息,征兆,端倪。(3)针石:用砭石制成的石针。古代针灸用石针,后世用金针。(4)良吏:贤能的官吏。(5)未萌:指事情发生以前。(6)囹圄:监狱。(7)文察:深文苛察。(8)强力:威力;武力;暴力。(9)厉:虐害;欺压。(10)本:根据。(11)残心:谓残害人的心;残忍的心。(12)不辜:无罪之人。(13)州里:同乡的人。(14)痈疽:毒疮名。《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痈疽总论歌》:“疽由筋骨阴分发,肉脉阳分发曰痈。”(15)“诗云”以下四句:语出《诗经·小雅·雨无正》。辜,罪。沦胥,相率牵连。铺,通“痡”,病苦。(16)铫锄:锄草翻地的农具。铫,锹锸之类。锄,锄草翻地的农具。(17)芸:通“耘”,除草。(18)准平:测量平面的仪器。(19)枉而绳直:枉,不正,不直。绳作动词用,纠正。(20)为:有。“为过”与“有功”,互文见义。
译文法律可以惩罚人,但不能使人廉洁;可以把人处死,但不能使人心怀仁义。医道高明的医生之所以可贵,在于他能明察气脉盛衰,使邪气消退,而不在于他用石针去刺皮肉。贤能的官吏之所以可贵,在于能把坏事消灭在没有发生之前,使人不去为非作歹,而不在于他把犯人逮捕到监狱,并处以死刑。可是现在所谓贤能的官吏,深文苛察来祸害百姓,使用暴力强权来残害下民,不根据法律制定的本意,而是凭着自己一颗残忍的心独断专行。深文罗致,假借法令,陷害无辜,连累无罪的人,儿子牵连父亲,弟弟连累哥哥。一人受罪,整个乡里都惊慌害怕,以致许多家的人都逃亡了。好像毒疮一样互相传染,像好色和淫乱互相联系,一个枝节动摇,牵连百根枝条都晃动起来。《诗经》上说:“赦免那个有罪的人,因为他已经服罪;如果此人无罪,那便是受到牵连而受苦难。”这是在哀伤其无罪而受连累啊!不怕锄头不锋利,只怕留着杂草不锄,反而把禾苗锄掉了;不怕没有测量平直的仪器,只怕放过凹曲不平直的反而去纠正平直的。所以执政者对亲近的人,虽有过错而不处罚他,这就等于见到杂草却不将它锄去;对关系疏远的人,虽有功劳而不奖赏他,这就等于见到禾苗生长出来了,却不用心去培育。所以,国家不怕没有法律,怕的是没有真正能够切实可行的法律。
周 秦
题解本篇用“周秦”作为篇名,通过对秦朝实行严刑酷法的描述,就“礼治”和“法制”问题展开讨论,主张应该效仿周朝实行“礼治”,继续宣扬“礼周教明,不从者然后等之以刑”,其目的是攻击汉武帝推行的“法治”。
原文古者,周(1)其礼而明(2)其教。礼周教明,不从者,然后等之以刑。刑罚中,民不怨矣。故舜施(3)四罪(4)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轻重各伏其诛,刑必加而无赦,赦维疑者。若此,则世安得不轨之人而罪之乎。今废其德教而责之礼义,是虐民也。《春秋传》曰:“子有罪,执(5)其父;臣有罪,执其君。听失(6)之大者也。”今以子诛父,以弟诛兄,亲戚相坐(7),什伍(8)相连,若引根本而及华(9)叶,伤小指而累四体(10)也。如此,则以有罪反诛无罪。反诛无罪,则天下之无罪者寡矣。故吏不以多断为良,医不以多刺为工。子产杀一人刑二人,道不拾遗(11),而民无诬心。故为民父母,似养疾子,长恩厚而已。自首匿(12),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废,而刑罪多矣。闻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匿之,其不欲服罪尔。子为父隐,父为子隐(13),未闻父子之相坐也。闻兄弟能缓追以免贼(14),未闻兄弟之相坐也。闻恶恶止其人(15),疾始而诛首恶(16),未闻什伍而相坐也。
注释(1)周:周密,周全。(2)明:宣扬。(3)施:判罪。(4)四罪:谓舜治共工、欢兜、三苗、鲧四凶之罪。(5)执:拘捕。(6)听失:谓听狱的错失。(7)相坐:谓一人有罪,连坐他人。(8)什伍:古代户籍编制,五家为伍,十户为什,相联相保。(9)华:同“花”。(10)四体:四肢。(11)道不拾遗:谓路有失物,无人拾取。此处用以形容民风淳厚。(12)首匿:谓主谋藏匿罪犯。(13)隐:隐匿;隐瞒。《论语·子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14)兄弟缓追以免贼:典引《汉书·邹阳传》:“阳见王长君曰‘庆父亲杀闵公,季子缓追免贼,《春秋》以为亲亲之道也。’”说的是春秋时鲁国庆父杀人后奔逃,其弟季友纵而不追,以免其贼乱之罪的故事。(15)恶恶止其人:语出《春秋公羊传·昭公二十年》:“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子孙。”“其人”“其身”,字异义同。恶恶,憎恨邪恶。(16)首恶:元凶,罪魁祸首。
译文古时候,君王制定周全的礼义,继而宣扬教化。礼义完备,教化严明,不顺从的人再按其轻重的不同程度,处以不同的刑罚。刑罚恰当,百姓就不会有怨言。所以,舜惩办了四个罪人而天下人都信服,这是因为惩办的是没有仁爱之心的恶人。根据罪行的轻重,分别处以不同的刑罚,必须判刑的绝不宽赦,宽赦的只是由于证据不足、一时无法准确定罪的疑犯。这样下去,世间哪能找到不守法规的人来判罪呢?现在废除了仁德教化,却要求百姓要懂礼义,这是残害老百姓啊。《春秋公羊传》上说:“儿子犯罪,抓捕他的父亲;臣子犯了罪,追究他的国君。这样处理案件的人错失就太大了。”现在因为儿子犯了罪,制裁父亲;因为弟弟犯了罪,惩办兄长,亲戚和邻居也都牵连有罪,这就像拔树根而连及花和叶子、伤一小指而牵连四肢一样。这样做,就是以一人犯罪而加罪于无罪之人啊。归罪于无罪之人,那么天下的无罪之人就很少了!所以,官吏不以多断案为高明,医生不以多施针为本领。子产治理郑国,只是杀掉一人、处罚二人,便使郑国出现了路不拾遗的景象,百姓也没有了欺诈的念头。所以做官的人对待百姓,就像父母对待自己有病的孩子一样,只要更多的施与恩惠就行了。自从施行“首匿相坐”之法以后,人与人之间连骨肉亲情也被抛弃了,于是违法犯罪的现象也就随之越来越多。从前听说父母对待自己的儿子,虽然明知道他犯了罪还是要替他隐瞒,因为不忍心看到他伏法受刑;只听说儿子为父亲隐瞒罪恶,父亲为儿子隐瞒罪恶的,从来没听说过父子互相连坐的事情;只听说过兄弟之间明知对方犯罪却故意放走他以免其罪咎的骨肉相怜之事,从来没听说过兄弟互相连坐的道理。只听说憎恨恶人只恨恶人本人、痛恨带头作恶的人而惩办那些罪魁祸首,从没有听说十家连保、五家相坐的事。
原文纣为炮烙(1)之刑,而秦有收孥(2)之法。赵高(3)以峻文(4)决罪于内,百官以峭法(5)断割(6)于外,死者相枕席(7),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8),不寒而栗。方此之时,岂特冒火蹈刃(9)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嫚,至于骨肉相残,上下相杀,非刑轻而罚不必,令太严而仁恩不施也。故政宽则下亲其上,政严则臣谋其主。晋厉(10)以幽(11),二世以弑(12),恶(13)在峻法之不犯,严家(14)之无挌虏(15)也。圣人知之,是以务和(和作恩)而不务威。故高皇帝约秦苛法,以慰怨毒(16)之人,而长和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恩施无穷,泽流后世。商鞅(17)、吴起(18)以秦、楚之法为轻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没其身。或非特(19)慈母乎(或以下六字本书同。疑有误)。
注释(1)炮烙:传说是商纣的一种酷刑,用烧红的铁烙人的刑罚。(2)收孥:古时,一人犯法,妻子连坐,没为官奴婢,谓之收孥。孥,音奴,妻子和儿女。(3)赵高:秦朝二世皇帝时丞相。(4)峻文:指苛细的法令条文。(5)峭法:严峻的法令。(6)断割:裁决。(7)枕席:同“枕藉”,物体纵横相枕而卧。言其多而杂乱。(8)侧目重足:侧目,不敢正视,形容畏惧。重足,叠足不前,形容非常恐惧。(9)蹈刃:踏刀锋。喻不顾危险。(10)晋厉:即晋厉公,春秋时晋景公子,名寿曼。曾西败秦,南败楚,威震诸侯,后被大夫栾书和中行偃二人捉捕囚禁而死。(11)幽:囚禁。(12)二世以杀:指秦二世胡亥被赵高所杀。(13)恶:疑问词,怎么,哪里。(14)严家:家规严厉的人家。(15)虏挌:挌,同“格”。强悍不驯的奴仆。(16)怨毒:怨恨,仇恨。(17)商鞅:约公元前395年至公元前338年在世,卫国(今河南濮阳)人,汉族。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孝公死后,被贵族诬害,车裂而死。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18)吴起:公元前440年至公元前381年在世,中国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军事家。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人,拜鲁国的曾子为师,学习儒术。曾为鲁、魏两国的大将,为魏国拒秦,屡立战功。魏武侯十五年,受小人陷害,出奔楚国,任令尹,辅佐楚悼王变法。公元前381年,悼王死,楚国贵族便杀害了吴起。(19)非特:不仅;不只。
译文商纣王设有炮烙的刑罚,秦国立有收孥的法律。赵高在朝廷内以苛刻的法律判决罪人,百官们在各郡县以严酷的刑法惩治罪犯。死尸纵横相枕,受刑的人一个接着一个,百姓不敢正眼相看,害怕得连脚都不敢移动,真是让人不寒而栗。当此之时,人民所受的苦难,岂止是在刀山火海上行走所能形容的啊!然而,父子互相背弃,兄弟之间互相轻侮,甚至骨肉之间互相残害,上下之间互相残杀,这不是因为刑罚轻和该惩罚的没有惩罚,而是法令严苛、不施仁德和恩惠的缘故。所以,刑法宽恕,百姓就亲近君主;法律苛严,臣子就谋害君主。正是因此,晋厉公被囚禁而死,秦二世被杀。怎么说在严峻的刑法之下就没有犯罪的人,严厉的人家就没有强悍不驯的奴仆呢?圣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致力于教化,而不用刑罚威慑。所以,汉高祖简化了秦朝的苛刻刑法,安慰那些心中充满怨毒的百姓,长养大家的和睦之心。这样做是因为怕刑罚太重而恩德显得太薄,所以高祖在位之时施恩没有穷尽,德泽一直流传到后代。当年商鞅、吴起认为秦国和楚国的刑法太轻,而不断地加重刑法,结果对上危害自己的君主,往下则断送了自己的性命。或许这不只是慈母没教育好而造成的后果吧!
诏 圣
题解诏,告。“诏圣”,就是告以所谓圣人之道的意思。本篇从“时世不同,轻重之务异”的历史进化观点出发,认为“礼让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强调执行法治,“故能长制群下,而久守其国”。本篇旨在批判当时社会的混乱。
原文民之仰(1)法,犹鱼之仰水。水清则静,浊则扰,扰则不安其居。静则乐其业,乐其业则富;富则仁生,赡(2)则争止。是以成、康(3)之世,赏无所施,法无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赏而不赏,民莫不仁也。若斯(4),则吏何事而可理乎?今之治民者,若拙御之御马也。行则顿之,止则击之,身创于捶(5),吻伤于衔(6),而求其无失。何可得也。故疲马不畏鞭捶(7),疲民不畏刑法。虽增而累之,其有益乎?
注释(1)仰:依赖。(2)赡:满足。(3)成康:周成王姬诵与周康王姬钊的并称。史家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康王在位期间,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安定。后世将这段时期和成王末年的统治,誉为“成康之治”,史称“成康盛世”。(4)若斯:如此。(5)捶:鞭子。(6)衔:马嚼子。(7)鞭捶:鞭打。
译文老百姓依赖法律,就像鱼儿依赖水一样。水清澈,就生活得安静;水混浊,就会受到惊扰。同样,社会秩序混乱,百姓就不能安居;社会稳定,百姓就安居乐业。百姓安居乐业,就能致富;生活富裕了,人民就会接受教育讲求仁义;家里富足了,过去因为求生存而发生的争夺也会渐渐停止。所以,周朝成王、康王的时代,没有施予什么赏赐,也没有施加什么刑罚。并不是应当判刑的没有判刑,而是百姓没有犯法的;也不是应当奖赏的没有奖赏,而是百姓没有不讲仁义的。如果这样,那官吏还有什么事情可干呢?今天的官吏,像一个笨拙的赶车人驾驭马车一样,马在行走,却要它停下;马停下了,又要鞭打它。马身上到处落满鞭痕,嘴角被马嚼子勒破,还要求它不出错,这怎么可能呢?极度疲惫了的马是不再害怕鞭打的,极度疲困了的百姓也是不再惧怕刑罚的,即使对他们不断地加重刑罚,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原文古者明其仁义之誓,使民不逾。不教而杀,是虐(1)民也。与其刑不可逾,不若义之不可逾也。闻礼义行而刑罚中,未闻刑罚任(任作行)而孝悌兴也。高墙狭基,不可立也;严刑峻法,不可久也。二世信赵高之计,深督责而任诛断(2),刑者半道,死者日积,杀人多者为忠,敛民悉者为能,百姓不胜其求,黔首(3)不胜其刑,海内同忧而俱不聊生。故过任(4)之事,父不得于子;无已之求,君不得于臣。知死不再,穷鼠啮狸(5)。匹夫奔万乘(6),舍人折弓(7),陈胜、吴广是也。闻不一朞(8)而社稷为虚,恶在其能长制群下而久守其国也。
注释(1)虐:残害。(2)诛断:诛杀。(3)黔首:古代称平民;老百姓。秦始皇更名老百姓为黔首。见《史记·秦始皇本纪》。(4)过任:超过力所能及的负担。(5)穷鼠啮貍:犹言困兽犹斗。逼得走投无路的老鼠也会咬猫。喻人被迫过甚,虽力不敌,亦必反抗。(6)万乘:帝王。(7)舍人折弓:舍人,官名,战国秦汉时王公贵官家都有舍人,和门客一样,如李斯为吕不韦舍人,就是一例。舍人折弓事,《吕氏春秋·适威篇》:“子阳极也,好严,有过而折弓者,恐必死,遂应猘狗而弑子阳。”又见《淮南子·泛论篇》。(8)一朞:一周年。《书·尧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朞,亦作“期”。
译文古时候的贤明君王,宣明以仁义修身的誓约,使百姓不僭越礼义;认为如果不先进行教育而犯罪就杀,就是残害百姓。与其制定刑法使百姓不敢触犯,不如提倡礼义使百姓耻于违反。只听说推行礼义,刑罚就能运用得恰当;没有听说过施行刑罚,孝悌之风就能兴盛起来的。高高的大墙,地基狭窄,是不能立得住的;用严厉的刑法治理国家,是不能长久的。秦二世听信赵高的计谋,用繁重的刑罚任意杀人,路上行人一半是囚徒,被处死的人日益增多。使官吏以杀人多者为忠,以刮尽民财者为能。其结果是百姓再也承受不了他们的苛求,平民再也无法忍受他们的刑罚,全天下的人都忧愁终日,感到再也无法活下去了。所以,父亲不能要求儿子做他办不到的事情,君主不能对臣子提出无止境的要求。如果到了必死无疑的境地,被逼得走投无路的老鼠也敢于啮咬狸猫,普通老百姓也敢和天子拼命,寄食的舍人也敢杀害主人。陈胜、吴广就是这样的人啊。听说从那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秦国就不复存在了,哪里是像有些人所说的,只要坚持不懈地用严刑峻法统治人民,就能永久保住政权呢?
新 序
题解《新序》是西汉著名经学家刘向编撰的一部以讽谏为政治目的的历史故事类编。刘向目睹汉王朝国势衰颓的趋势,对于执政者的奢侈腐朽和社会矛盾的尖锐,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所以编《新序》,以期讽君劝臣,达到整顿朝纲、匡救时弊的目的。其编撰思想,以儒家仁政为主,而杂以王霸大略。《群书治要》从《新序》中共节录了三十章,概括其思想,有以民为本、轻徭薄赋、禁欲戒奢、辨别贤佞忠奸、尊贤礼士、接受劝谏等,读来十分耐人寻味。
作者简介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又名刘更生,字子政。沛县(今属江苏)人。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治《春秋谷梁传》。宣帝时,为谏大夫。元帝时,任宗正。以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以反对恭、显下狱,免为庶人。成帝即位后,得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尉。曾奉命领校秘书近二十年。编有《新序》《说苑》《列女传》三部历史故事集。所撰《别录》,为我国目录学之祖。又据《汉书·艺文志》载,刘向有辞赋三十三篇,今仅存《九叹》一篇。
杂 事
题解本篇通过讲述楚恭王临终辨别忠奸、赵简子与虎会辨才、楚昭奚恤义迎秦国使者、钟无艳讽齐王等众多小故事,告诫汉皇要尊贤礼士,禁欲戒奢,辨别忠奸,劝讽纳谏,以民为本,轻徭薄赋。故事短小而寓深意,读之让人回味。
原文楚恭王(1)有疾,召令尹(2)曰:“常侍(3)筦苏(4)与我处,常劝我以义。吾与处不安也,不见不思也。虽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细,必厚(旧无厚字。补之)爵之。申侯伯(5)与我处,常纵恣(6)吾。吾所乐者,劝吾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与处欢乐之,不见则戚。虽然,吾终无得也,其过不细,必亟(7)遣之。”令尹曰:“诺。”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苏为上卿(8),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9)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10)。”恭王之谓也。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11)。”于是以开后嗣(12),觉来世(13),犹愈没身(14)不寤(15)者也。
注释(1)楚恭王:即楚共王。恭,通“共”。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560年,名熊审,楚庄王之子,时年幼,由重臣令尹(相当于丞相)子重专政。楚共王十六年(公元前575年)六月,在鄢陵地区(今河南鄢陵西南),晋楚进行了一场大战,史称鄢陵之战,楚共王中箭负伤,公子茂成了俘虏,军帅子反自杀。楚共王三十一年(公元前560年),楚共王积郁成疾,临死之前,曾令臣下尽皆退走,独留令尹交代后事,要臣下给予恶谥,请谥为“灵”或“厉”。(2)令尹:春秋战国时楚国执政官名,相当于宰相。(3)常侍:官名,国君身边的侍从近臣。秦汉有中常侍,魏晋以来有散骑常侍,隋唐内侍省有内常侍,均简称常侍。(4)筦苏:人名。(5)申侯伯:人名,楚恭王的宠臣。(6)纵恣:亦作“纵姿”,肆意放纵。(7)亟:疾速。与“缓慢”相对。(8)上卿:古官名。周制天子及诸侯皆有卿,分上中下三等,最尊贵者谓“上卿”。(9)曾子:即曾参(公元前505年—前435年),字子舆,春秋末期鲁国南武城(今山东省平邑县)人,孔子的弟子,世称“曾子”。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相传他著述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同时,他亦为《二十四孝》中“啮指痛心”的主角。在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南建有曾子庙、曾林(曾子墓)。(10)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语出《论语·泰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11)朝闻道,夕死可矣:语出《论语·里仁》。(12)后嗣:后代;子孙。(13)来世:后世;后代。(14)没身:终身。(15)寤:醒悟;觉醒。
译文楚恭王生病了,把令尹召来,说:“常侍筦苏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常常用正义之言规劝我。我跟他相处时,感到心情不安宁,看不到他时也不会想念他。尽管如此,但我却有所收获,他的功劳不小,一定要赐给他更高的爵位。申侯伯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常常纵容我胡作非为。我所喜欢的,他都鼓动我去做;我所爱好的,他就会走到我前面去尝试。我跟他相处时,感到很快乐,看不到他时,心里就闷闷不乐。尽管如此,但我却一无所获。他的过失不小,一定要赶快把他打发走。”令尹回答说:“好的”。第二天,楚恭王去世了,令尹就马上拜筦苏为上卿,把申侯伯逐出国境。曾子曾经说:“人将要死去的时候,说出来的话也是善意的。”恭王就是这样。孔子也曾说过:“假如一个人早上听到了真理,即使他晚上就死去了,也不会有所遗憾。”楚恭王的做法可以用来启发后人,警惕来世,总比那些至死还不觉悟的人强得多了。
原文赵简子(1)上羊肠(2)之坂(3),群臣皆偏袒(4)推车,而虎会(5)独担戟(6)行歌(7),不推车。简子曰:“群臣皆推车,会独担戟行歌,是会为人臣侮其主。为人臣侮其主者,其罪何若?”对曰:“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简子曰:“何为死而又死?”会曰:“身死妻子为徒(原书为徒作又死),若是谓死而又死也。君既已闻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闻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简子曰:“何若?”会曰:“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为谋,辨者不为使,勇者不为斗。智者不为谋,则社稷危;辨者不为使,则使不通;勇者不为斗,则边境侵。”简子曰:“善!”乃以会为上客(8)。
注释(1)赵简子:即赵鞅(?—公元前475年),嬴姓,赵氏,原名名鞅,后名志父,谥号简。时人尊称其赵孟,史书中多称之赵简子,亦称赵简主。他是战国时代赵国基业的开创者,郡县制社会改革的推动者,先秦法家思想的实践者,与其子赵无恤(即赵襄子)并称“简襄之烈”。(2)羊肠:喻指狭窄曲折的小路。(3)坂:山坡,斜坡。(4)偏袒:解衣裸露一臂。(5)虎会:人名。(6)戟:古代兵器名。合戈、矛为一体,略似戈,兼有戈之横击、矛之直刺两种作用,杀伤力比戈、矛为强。(7)行歌:边行走边歌唱。借以发抒自己的感情,表示自己的意向、意愿等。(8)上客:春秋战国时期,贵族有养士的风气,即招揽一些有才艺的人,供其衣食,在用人时量才使用,称为门客。根据门客的见识、能力,把门客分为若干等级,给予不同待遇。“上客”就是享受最高待遇的门客。
译文赵简子要上一条既狭小又曲折的山坡路,他的臣子们都光着一只膀子给他推车子,只有虎会一个人扛着戟,一边走一边哼着歌,没有去推车子。赵简子就质问他说:“大家都来帮忙推车子,只有你虎会却扛着戟,边走边唱,你这是身为人臣而侮慢君主。做臣子的侮慢他的君主,该当何罪?”虎会回答说:“臣子轻慢其君主应该死上加死。”简子又问:“什么叫死上加死呢?”虎会回答说:“自己要被杀死,连老婆和孩子也都要被杀死,像这样就叫做死上加死。主上您既然知道做臣子的人侮慢其君主该当何罪了,那么您也听说过作为君主而轻慢其臣下的结果吧!”赵简子问:“结果会怎么样?”虎会回答说:“做君主的人,如果侮慢其臣子的话,结果是有智谋的人不替他策划大事,有辩才的人不给他做外交使节,有勇力的人不为他冲锋陷阵。有智谋的人不替他策划大事,那国家就会有危险;有辩才的人不给他做外交使节,那国家就无法和他国往来;有勇力的人不为他冲锋陷阵,那边境就会受到别国的侵犯。”赵简子说:“你说得有道理。”于是就把虎会尊为上客。
原文魏文侯(1)与大夫(2)坐,问曰:“寡人(3)何如君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黄(4),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对曰:“君伐中山(5),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长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出之。次至任座(6),文侯问曰:“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对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对曰:“臣闻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黄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复召翟黄。
注释(1)魏文侯:战国时期魏国的建立者。姬姓,魏氏,名斯。公元前445年继魏桓子位,公元前424年称侯改元,公元前403年与韩、赵两家一起被周威烈王册封为诸侯,公元前396年卒。(2)大夫:古职官名。周代在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等;各等中又分上、中、下三级。后因以大夫为任官职者之称。(3)寡人:古代君主的谦称。(4)翟黄:战国时魏国下郢人,魏文侯的大臣。(5)中山:古国名,春秋末年鲜虞人所建,在今河北省定县、唐县一带,后为赵所灭。(6)任座:人名,魏文侯的大臣。
译文魏文侯和大臣们闲坐时,就问大臣们说:“我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君呢?”大家都说:“君主您是一位仁明的国君!”轮到翟黄,他说:“君主您不是一位仁德的明君。”魏文侯追问说:“您凭什么这么说?”翟黄回答说:“君主您攻取中山国以后,不把它封赐给您的弟弟,却把它封赏给您的大儿子,我从这里就知道您不是一位仁君。”文侯听了大怒,就把翟黄赶了出去。接着轮到任座,魏文侯问他说:“我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君呢?”任座回答说:“君主您是一位仁明的国君。”魏文侯问:“您凭什么这么说呢?”任座回答说:“我以前听人说过,如果国君有仁德,他的臣子就敢于说真话。刚才翟黄敢说真话,我因此知道君主您是一位仁明的国君。”魏文侯说:“很好!”于是又召回了翟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