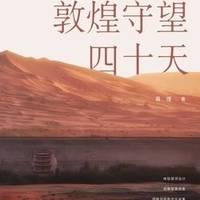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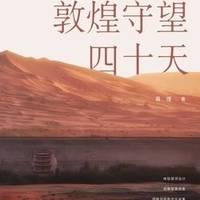
散文日记系列 之 敦煌守望四十天08
第七天|6月7日 江南诗人
01
在守望敦煌的四十天里,除了完成项目组安排的“规定动作”之外,我还交给自己一个任务——在敦煌寻找江南。这两个地方都与我有非常的联系:一个是心之所向,一个是身之所居。敦煌是大漠孤烟下的多元文化,而江南是小桥流水中的诗性生活。两者之间不仅相距数千里,其外在风貌与内在精神都显示着巨大的差异。在敦煌甚至流传有一句谚语:居塞北之人,不知江海有万斛之船;居江南之人,不知塞北有千里之雪。但我却始终相信,在这万斛船与千里雪之间,一定存在着无数微妙的联系,它们彼此呼应,也与我心灵相通。
02
今天是守望者开营之后的第一个休息日,我很想躺到地老天荒才起床,但脑海中突然浮现出昨天在榆林窟水月观音像当中看到的太湖石,于是不再继续赖在床上虚度时光,决定去禾园附近的敦煌图书馆寻找一下江南线索。
江南游客
沿着水渠,行走在林荫里,完全感觉不到自己身处大漠。周日的敦煌图书馆前来学习的人不少,这里设置了“敦煌文化书籍专柜”,另有一个环境不错的咖啡吧也摆放有大量石窟艺术类书籍。我要了杯咖啡,在这些书籍当中开始寻找江南。
03
由于这是个“冷门”话题,几乎很难找到直接讲述江南与敦煌关系的专著,我只能在各种敦煌主题书籍当中去搜寻那些有缘片段。一番速读之后,一本介绍莫高窟洞窟当中游人题记的书籍引起了我的兴趣。在没有文物保护意识的古老年代里,这些千年之间游人们一时兴起留在石窟崖壁上的只言片语,便成了我追溯千年之前生活痕迹的关键线索。
我惊喜地发现,莫高窟已知最早的游人题记,恰恰来自一位江南游客。它位于130窟,也就是敦煌第二大佛的脚下。题记中写道:“浙江东道弟子张逑魏博弟子石弘载,咸通七年三月廿八日。”话语简短,但我知道,唐朝的浙江东道大概相当于浙江省除浙北之外的所有地方,治所在越州,也就是今天的绍兴。而咸通七年(866年)的敦煌,已经摆脱了吐蕃人的统治,重归大唐版图,处于张氏归义军政权的实际控制之下。
04
我不禁掩卷畅想,这位江南游人跨越千山万水,是因为要看一眼这个被吐蕃人夺走了60多年,如今重回大唐怀抱的西部重镇吗?当他从小桥流水的江南来到了大漠孤烟的河西,心中的感受是否跟今天的我有几分相似?除了这满天的神佛,他在敦煌还与什么样的人和事相遇了呢?(注意:图片后本段继续)

▲莫高窟130窟窟门处的铁牌,上面写着:130盛唐(公元705年—780年)。

▲敦煌研究院办公区中悬挂的出自莫高窟130窟的《都督夫人礼佛图》,由段文杰先生临摹。
来到敦煌的这段时间里,130窟都在封闭维修,不知道离开之前是否有机会进入其中膜拜一下敦煌第二大佛,观赏一番著名的《都督夫人礼佛图》。但即便能够入窟,也很有可能看不到这条题记了,网上有人说它早已剥落了。我的一切发问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但知道“他”从江南来过,对我来说,或许就已足够。
05
诗人张球
告别了江南游客,我继续在书海中寻找线索。接近中午的时候,终于又在一本介绍敦煌当地名人的书中发现一个名字——“张球”。虽然书中对他的介绍只有寥寥几句,说他来自江南,是张氏归义军期间重要的文人,但通过网络可以查找到不少专家已经对这位来自江南的诗人有过深入的研究了,比如甘肃社科院的颜廷亮老师、敦煌研究院的李正宇老师、复旦大学的陈尚君老师、中国社科院的杨宝玉老师,等等。从他们的文章当中,晚唐时期寓居敦煌的江南诗人形象,逐渐浮现在我眼前。
06
张球是越州人,少时读书于江南,颇有才华,壮年行游西北,在河西生活了约三十年,最后终老敦煌。张球还曾开馆教学,在那个敦煌刚刚从吐蕃人手中回归大唐的特殊时期,深谙中原和江南文化的张球,协助这座城市重续了汉文化的火种。
从他留下来的一些诗篇当中,我读到了一个长居敦煌的江南诗人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比如“天山旅泊思江外,梦里还家入道墟”,这里的江外便是江南;比如“镜湖莲沼何时摘,柳岸垂杨泛碧朱”,诗中的镜湖便是今天绍兴的鉴湖,是贺知章等诗人的归隐之处。而我最喜欢的,还是那首《归夜于灯下感受》:“长思赵女娟,每忆美人舟。仰首江南子,因循北海头。连天唯白草,雁过又成秋。喜归无恐色,抛却暮云愁。”诗中的张球,并没有近乡情怯,他是那么发自内心地想要拥抱江南。
07
探寻至此,我忽然有了个大胆的联想:张球会不会就是在130窟当中留下题记的“浙江东道弟子张逑”呢?从地点上比对,唐代时越州正是浙江东道的治所;从时间上分析,敦煌遗书(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献的总称)中显示张球在咸通元年(860年)到过朔方(今宁夏银川附近),之后前往凉州(今甘肃武威),再来到敦煌任职,跟咸通七年(866年)的题记比较吻合;从信仰上调查,张球在敦煌遗书中曾自述,完成各种艰难任务,“此皆菩萨加持力也”,这无疑显示出他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因此也具备了在佛窟中题记,并自称“弟子”的可能。随着这些分析,那位江南游客和这位江南诗人的身影,在我心中渐渐重合。
也许,这只是一种巧合吧;也许,这就是真实的人生!不管如何,我找到了历史深处那位串联起江南与敦煌的诗人。我想今后当我路过130窟的时候,眼前一定会浮现出那个模糊而又清晰的身影:他风尘仆仆而来,虔诚敬心礼佛,然后拿出随身所带的笔墨,在崖壁上恭敬地写下那行字“浙江东道弟子张球”。
08
日落鸣沙山
下午,杨翻带来了大家非常期待的“敦煌壁画和矿物质颜料”分享会。他首先展示了用宕泉河中的敦煌土制成的泥板,我们上手抚摸泥板并仔细观察,对敦煌壁画的制作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古代的工匠们都是先用粗草泥涂抹在洞窟崖壁上,干透之后再用宕泉河床上的敦煌土平整涂抹在粗泥层上,最后在这细泥层上刷上极薄的高岭土或者石灰,完成地仗层的制作。而名闻天下的敦煌壁画,就是绘制在这样的地仗层上。
杨翻还给我们展示了多种矿物质颜料。大家亲自上手研磨,并将其混入动物胶当中,然后在杨翻的指导之下,拿起画笔,蘸上颜料,在泥板上像模像样地“创作”起来。虽然画作稚拙可笑,但也成了我们人生中的第一幅“壁画”。

▲莫高窟420窟中弟子阿难漆黑如炭,而紧邻的胁侍菩萨洁白如玉。
09
分享会上,我还在和大家的交流讨论中,解开了心中的一个疑惑。那就是在420窟的双层佛龛当中,弟子阿难和紧邻的胁侍菩萨,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漆黑如炭而另一个洁白如玉的情况。原来,420窟这样的大型洞窟绝不可能是一位工匠独立完成的。有的工匠会使用铅丹、铅白颜料来给人物上色,这种颜料中的铅极易氧化变黑,就出现了多年之后“阿难”变成了“古天乐”的情况;而其他工匠使用的颜料中不含铅,因此菩萨历经千年,依然面如白玉。
10 杀青段
谜题有了答案,心中非常舒畅。在分享结束之后,我约上几位中老年守望者,搭乘禾园少东家的车,前往三危山拍摄落日。车在接近莫高窟的地方拐进了一条崎岖小道,一路颠簸而上,停在山脚。我们开始徒步向三危山顶走去。但走到半山腰的时候,夕阳已经快坠入鸣沙山了。于是我们决定就在这里停下来,开始欣赏这转瞬即逝之美。背后的三危山岩石峥嵘,眼前的鸣沙山波澜起伏,身旁的古塔质朴沧桑。我们架好相机,打开啤酒,或坐或立,在清爽的晚风当中,看着夕阳绽放出最后华光,晚霞将莫高窟上方的天空染成绯红,九层楼逐渐隐入暮色,所有洞窟开始安眠,然后按下快门,举瓶痛饮,敬这闪亮的日子。

从三危山上眺望落日余晖中的九层楼。莫高窟窟顶是高大的沙丘,莫高窟的735个洞窟便分布在鸣沙山最东端的这片断崖之上。
相关链接:
01 山河小城 600809
02 初见莫高 501318
03 丝绸之路 911802
04 最美定禅佛 250675
05 明艳千年的秘密 603613
06 永葆青春的菩萨 253479
07 玄奘之路 585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