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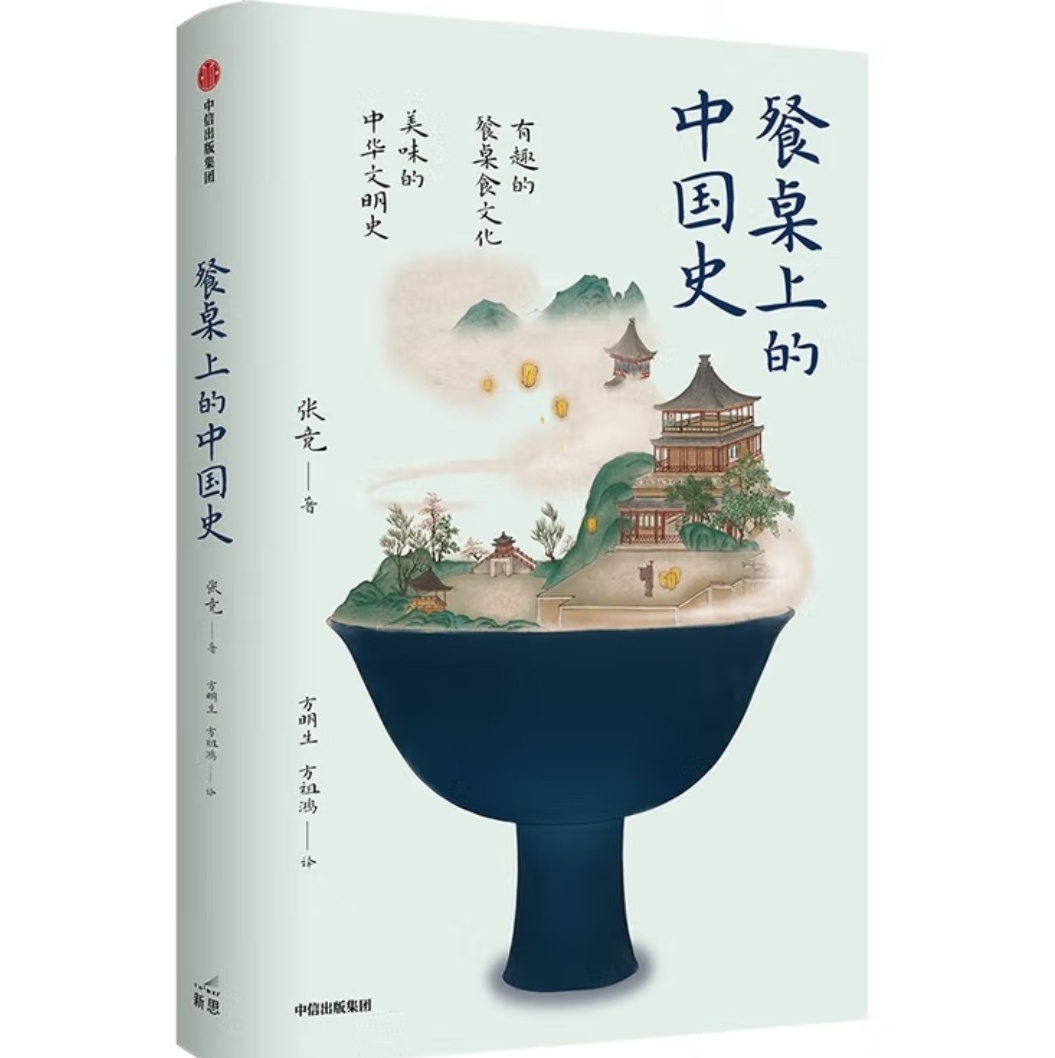
•饭是中国人的主食?其实连孔子也没得天天吃。
•儒学经典《论语》《礼记》不只教做人,其实也是美食教科书。
•张骞出使西域,一大贡献是带回了美食,还有制造美食的高科技。
•汉朝的街道上开始出现餐饮业,《盐铁论》痛批这些美食好吃到让人腐败与堕落。
•从春秋到唐朝,中国人其实是用勺子吃饭的,只有捞汤里的料才用筷子。
你吃了一辈子的中国菜,
其中的食材与菜式起源,
跟你以为的大不相同!
第二章 “粉墨登场”话面食
汉代
(上篇)
一、颗粒状食用的麦子
【“粒食”化的由来】
1.
采集文明、狩猎文明时期的情况尚不清楚,不过黄河流域自文字诞生以来,很长时期一直盛行“粒食”文化。小米也好,大米也好,麦类也好,都是颗粒状煮熟或蒸熟食用,无一例外。
中国大地上谷物的种类很多,各地区作为主食的谷物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地区,随着时代的变迁,也有各种变化。但要说到比较有共通性的“五谷”,即粟、黍、稻、麦、豆,都是颗粒状食用的。古代文献中时常出现的“麦”也不例外。
根据日本学者筱田统的研究,古代中国所说的“麦”是原产于中亚高原、从西方传至中国中原地区的大麦。这种麦子长期以来一直也是颗粒状食用的(筱田统,1974 )。关于大麦的原产地有各种说法,但颗粒状食用的说法大致是确凿无疑的。大麦之所以被称为“大”,并非颗粒大小的原因,而是对其品级的评价。由于大麦的外壳和糠皮容易去除,便于精磨成颗粒,古人认为其品级较高,故称为大麦。谷物中大麦的味道较差,并且面筋成分含量较少,不太适合磨成粉食用。这种颗粒状食用的习惯一直延续到现代。笔者还是学生时,家里经常煮大麦粥,在粮食不足的20世纪60年代前期也吃过麦子做的饭。现在市场上作为健康食品出售的,也是压扁的大麦。
【粟为主食的原因】
2.
古代的中原地区以颗粒谷物为主食,其原因与较多食用粟、黍有关。据考古发现,黄河流域8 000年前就已经种植粟了(闵宗殿等,1991)。以粟、黍为主食的历史延续时间很长,其间即使可以获得其他的谷物,一般也是以颗粒状食用的。
选择“粟”为主食,自有其原因。首先,粟生长期短,快的三个月就可以收获了,与要花半年时间才能收获的稻相比,粟种植的周期要短得多。而且它对气候的适应性很好,特别是耐旱,比较适合降水量较少的中国北方。再则,粟能在贫瘠的土地上生长,这使得自然条件较差、农业技术水准较低的地区也能种植粟。在只能进行原始农耕的古代,选择粟为主食是很自然的。
另一个原因是粟有丰富的营养。非精白的粟的蛋白质、类脂质、钙、铁、钾、维生素B2的含量均高于糙米。精白的粟与精白的米相比,除了以上的成分,在能量、纤维素、碳、磷、维生素B1、烟酸等含量上也较高。这些营养上的特点,当时的人虽然还没有在科学上认识到,但根据经验也是可以感受到的。
豆的种类各种各样,以大豆为例,从蛋白质、类脂质、钙、铁、维生素等含量上看要比粟高,但最大的问题是其吸收率只有65%。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选择粟而不是豆为主食是有其缘由的。
【小麦是何时开始种植的】
3.
这些年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在黄河流域以外存在着高度发达的文明。比如长江流域就存在着比黄河文明更为古老的农耕文化,只是因为没有文字史料的存在,这样的事实长期以来一直被埋没了。这些地区都是种稻的。南方与黄河流域不同,主食是稻米。从这种意义上说,古代中国文化比迄今为止了解到的更具有多样性。但从主食颗粒状食用还是磨粉食用的问题上看,稻米也是粒食的,在这一点上南北地区是一样的。
关于小麦何时传到中国众说纷纭。根据考古学者的发掘结果,西周就已经有小麦了(李长年,1981)。201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镐京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在填埋垃圾的灰坑里发现了碳化的小麦颗粒,这是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当时,主要媒体都进行了报道。据报道,在镐京遗址发现小麦颗粒还是第一次。这些小麦是西周中期的遗物,虽距今2 800年,但小麦的颗粒形状仍保存良好。此类考古发现对小麦的种植起始于汉代一说是个挑战。
4.
但从小麦食用史的角度来看,还是有许多疑问遗留着。颗粒小麦的发现并不能证明当时小麦是磨粉而食的。相反,颗粒状食用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中国最早的石磨是1968年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之墓中出土的。这是一个由石磨和铜漏斗组成的复合磨,技术含量非常高。由于迄今还没有实物可以证明中国的石磨是从初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所以高端石磨的制作技术被认为是随着小麦的播种及加工技术经由丝绸之路一起进入中国的。历史文献的记载也基本上与这种看法吻合。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小麦不是主要农作物,而是作为二茬作物被种植的。文献中没有看到麦广泛地成为主食的记录。大麦和小麦曾经是用不同的汉字来表示的,而后逐渐变为用“麦” 一个字来表示,这也表明小麦在当时不是主要的农作物。如果小麦是主食的话,记录、统计、登记都需要与大麦区分开来,才更方便实际操作。
二、与西域的交往及面食之东渐
【面类食品的历史脚印】
5.
在汉字中,用“面”这个字来表示小麦粉。另外,用“饼”这个字来表示揉捏小麦粉制作出来的食物。这两个字以前没有,在汉代的文献中才出现。现代汉语中“饼”字是用来表示用小麦粉制成的食品的,其制作过程中经过揉捏、烧烤,外形呈扁平状。但“饼”在汉代并不是这样特定的含义,而是指所有用小麦粉制作的食物。所以,“饼”并非特指像“馕”那样的扁平的面粉食物,“面条”“面疙瘩”等都叫“饼”。
在汉代学者史游公元前30年所写的一本启蒙读物《急就篇》中,出现了 “饼饵” “麦饭” “甘豆羹”三种食物。其中“饼饵”是“饼”这个字最古老的用例。当然“饼”这种食物本身还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时代。根据《汉书•宣帝纪》的记载,汉宣帝(前91-前49)在即位前,经常出入市井买“饼”吃。可以想见,在写作《汉书》的时代就已经有“饼” 了。如果被记录下来的情况准确的话,“饼”的出现还可以追溯到更早。
汉建元三年(前138)张骞出使西域,12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26年回国。面粉食物可能就是这个时候由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这一说法没有确凿的根据,但其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6.
根据《汉书,食货志》的记载,汉代中期,董仲舒(前179—前104)上奏皇帝,内容是关于农业生产的进言,其中这样写道:
原文:
《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
译文:
《春秋》这本史书里没有记录其他作物的生长情况,但麦和粟收成不好时却都有记录,这里可以看出圣人在五谷中最重视麦和粟。而现在关中地区的人不太愿意种麦子,这就丢失了《春秋》最重视的作物,给百姓的生活带来很大影响。为此,恳求陛下给相关官员传令,尽快让关中的百姓种植过冬的麦子,不要错过时机。
7.
麦在原文中用“宿麦”两个字记录,并没有明确指出是大麦还是小麦。但这两种作物都是越冬作物,是在主要谷物收获之后才开始栽种的二茬作物。当时在陕西省附近不太种麦,是因为作为粮食,麦子不太受人们喜欢。假设这里提到的“宿麦”包含小麦,从这一记述中可读到一个重要的事实:汉代中期的中国西北部,麦还是以颗粒状被食用的。
古代不管是大麦还是小麦,以颗粒状食用的麦都被作为粗粮来对待。价格低,没有经济价值,即使种植了也提高不了收益,农民们对此不感兴趣。如果小麦能以面粉的方式来食用的话,就会有各种食用方法。事实上,磨粉食用的方法出现后,人们开始喜欢吃小麦粉了。由此,小麦粉的需求量增加,价格肯定也提高了。农民们就不会再讨厌种植小麦了。
【与西域的交往及面食的引入】
8.
董仲舒的上奏与张骞出使西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汉书•武帝纪》中有这样的记载:汉元狩三年(前120 )秋,“遣谒(yè)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意为汉武帝派遣谒者,要求遭遇洪水的地区栽种越冬的麦子。由此可见,麦仍是作为贫困地区或灾害时的粮食而种植的。这里也没有明确是大麦还是小麦,假设包含小麦,则小麦仍然被认为是较贱的粗粮。或许当时还未知晓磨粉食用的方法,或仅有部分地区有所知晓,还未普及开来。
不过,公元前33年左右,出现了用小麦粉制作的叫作“饼”的食物的记录。这两件事之间仅隔90年左右的时间。如果参照前面提到的汉宣帝的例子,这一时间差更缩短到20 ~ 40年。也就是说张骞出使归来仅仅90年之后,小麦的“粉食”就推广开来了。以当时交通手段不发达、信息传递要花很长时间的情况来推测,带来这种变化的时间是极为短暂的。另外,考虑到改良磨具、牵引具所需要的时间,可以想象“粉食”技术在很短的时间里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
9.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归来是公元前115年。出使途中,他派遣副使出访大宛(yuān今中亚的费尔干纳)、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大夏(巴克特里亚王国)、身毒(古印度)、安息(帕提亚,今里海东南岸)诸国。这些副使回国之后,西域的那些国家都派使节相继访问了长安。
“粉食”在中亚已有很长的历史,这点已十分明确。中国有原生的小麦,但没有形成发达的“粉食”文化。与小麦粉的出现及普及的时期联系起来考虑,产量高的外国品种的小麦与“粉食”文化一起从西域传入的可能性很高。
【麦子种植量的增加】
10.
然而,小麦的面食并未立即推广。前面说到的“饼”字的最早记录是公元前30年代,但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以颗粒状食用麦子的情况仍然持续着。
从西汉夺取王位建立新朝的王莽,在听到长安遭遇饥荒的流言后,向管理长安市场的宦官王业询问情况。王业拿着长安市场上卖的“粱饭肉羹“,也就是精白粟饭和肉汤,向王莽报告“居民食咸如此(居民们吃的是这样的东西)”(《汉书.王莽传下》)。这是公元22年的事,已是“饼”在文献中出现后50年了。
同一年,之后成为汉光武帝的刘秀起兵要推翻王莽政权。在去讨伐王莽的途中,据《后汉书•冯异传》记载:
原文:
及至南宫,遇大风雨,光武引车入道傍空舍,异抱薪,邓禹热火,光武对灶燎(liǎo)衣。异复进麦饭菟(tú)肩。
译文:
到达南宫(现在的河北省南宫市)时,遇到大风雨,刘秀把车拉进空着的房子里,冯异拿来柴火,邓禹点起了火。刘秀在灶前烘着淋湿的衣服时,冯异煮了麦饭和兔肉,端了进来。
11.
这是紧急情况下的食物,能够搞到的粮食还是颗粒状的麦子。这样来考虑,至少在农村地区常备的并不是小麦粉,而是颗粒状的大麦或小麦。
东汉有个文人名叫井丹,以清高闻名。王公贵族们都想与他结交,但全都被他拒绝了。有一天,光武帝(前26—57)妻子的弟弟阴就玩弄计策,硬是找了理由将井丹请到自己家来,仗着皇亲国戚的地位,想侮辱井丹,一开始故意将仅有麦饭和葱花的食物端出来。井丹责问,我是因诸侯之家应供上等的食物才来造访的,(作为国舅,)为何只端出如此粗劣的食物?最终,阴就不得不将佳肴端了上来。(《后汉书•井丹传》)这颇有一点把用餐作为心理战的工具的意味。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庶民还是吃麦饭的,而上层阶级则把这种食物看作粗粮。及至东汉后期,情况逐渐发生变化,小麦的面食渐渐增加了。
【面食的推广】
12.
东汉中期以后,小麦粉制作的食品更迅速地推广开来,成为民间日常的食物。崔寔(shí)在《四民月令》中写下“立秋勿食煮饼及水溲(sǒu)饼”的说法。“煮饼”和“水漫饼”应该都是揉面而成,为何分述,尚无以考证。可能是根据外形命名。“煮饼”可能指块状的面食,“水溲饼”可能是面疙瘩之类的食物。作者崔寔于东汉顺帝在位期间(126—144)出生,灵帝建宁年间(167-172)去世。这表明面类食物在东汉已经渗透到洛阳一带民间了。但那时,小麦粉是否已成为一种主食,还不能断言。
据《后汉书•李杜列传》的记载,146年,东汉奸臣梁冀唆使手下毒杀8岁的皇帝质帝。质帝用餐后,立即感觉不适,急唤太尉李固入宫。李固询问了质帝不适的原因,还能说话的质帝回答,是吃了“煮饼”后积食,喝水可能会舒服一点。此时,一旁的梁冀则说,“恐吐,不可饮水”,不让其喝水。梁冀话还没有说完,质帝就气绝身亡了。毒药可能是放在“煮饼”里的。这些事都发生在公元2世纪中期。有人认为,汉质帝吃的“煮饼”以及后来的“汤饼”即今日的面条,这是个很大的误解。
13.
即使到了宋代,“汤饼”仍然不一定是指现在吃的面条。譬如《山家清供》记述了名为“梅花汤饼”的食物:
原文:
泉之紫帽山有高人,尝作此供。初浸白梅、檀香末水,和面作馄饨皮。每一叠用五分铁凿如梅花样者,凿取之。候煮熟,乃过于鸡清汁内,每客止二百余花可想。
译文:
泉州紫帽山的一位高人,曾做过这种食物。先把白梅和檀香末浸在水里,用此水和面粉做成馄饨皮一样的薄片。用梅花形的铁凿按出一片片梅花状的薄片。滚水煮熟后,放入鸡清汤里。每位客人大约200片。
这里“汤饼”并不是细长的面,而是片状的。这已是宋代的事,何况更久远的时代。就笔者迄今所查阅的文献范围来说,没有任何数据可以证明汉代已经有面条。有关这一点,第六章还会论及。
三、汉代饮食生活的林林总总
【中原地区的农作物】
14.
秦汉两代期间,中国文明有了飞跃式的发展。特别是汉朝,水利和灌溉技术提高很快,制铁业发展迅速,铁器在农业生产与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
20世纪50年代,河南省洛阳市附近发掘了数百个汉代的墓,其中出土了12种谷物。从出土的次数与数量推测,当时主要的作物是黍、麦、粟、稻、豆(洛阳区考古发掘队,1959),这一结论与汉代学者赵岐关于“五谷”的解释基本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中原地区也种植稻。原本这一地区降水量少,不太适合水稻的种植。但汉以后,中国北方农业灌溉开始使用井水,河南省南部的泌(bì)阳县曾发掘出多处农业灌溉用井(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958)。农业水利的发达使得中原地区的稻作成为可能。但出土的墓多数是贵族与官僚的,稻米普及到何种程度,疑点还是很多。考虑到当时除了稻以外,还种植麦、黍、粟等多种谷物,不吃稻米的人口可能占多数。
【马王堆古墓中所见的汉代饮食】
15.
与中原地区相比较,南方稻作盛行,米食所占比例是比较高的。20世纪70年代,湖南长沙附近的马王堆出土了一座大型古墓,是公元前2世纪左右的三个地方贵族的墓。在数量众多的随葬品中,包含粮食、已烹调好的菜肴等各种食品,提供了推测汉代饮食文化的重要证据和线索。
在被发掘的三座墓中,仅一号墓就发现了30种以上的食品,而在三号墓里有40个竹箱装有食品。粮食有稻、小麦、黍、粟、大豆、赤豆、麻等。粮食的种类与前面提到的河南洛阳所发现的基本相同。这里没有发现用小麦粉制作的饼,可见当时小麦的面食还没有传播到南方。
马王堆汉墓中也发现了许多肉类食品的随葬品。畜类有牛、羊、猪、马、狗、鹿、兔等,是通过骨骼的鉴定得到确认的。禽类有鸡、雉(zhì)、鸭、鹑、雀以及雁、天鹅、鹤等十数种。鱼类全部是淡水鱼,有鲤鱼、鲋(fù)鱼、鳜(guì)鱼等(何介钧等,1992)。
这些材料都由厨师烹调后葬入墓中,被发掘出来时已失去了原来的形状,但从随葬竹简的记载上可大致推测出其烹饪方法。
16.
竹简上记载,肉类是已加工过的干肉和肉汤。其他主要的烹饪法有炙(zhì)(肉直接在火上烤)、脍(kuài)(肉切细后用醋拌)、濯(zhuó)(把肉放飕菜汤里煮)、熬(把肉煎干)、濡(rú)(肉煮透后用汁拌匀)等(何楠等,1992)。
其中汤菜最多,有醢(hǎi)羹、白羹、巾羹、葑(fēng)羹、苦羹五种。醢羹是把干肉切细,用酒、盐、曲等调味以后做成的汤;白羹是用米粉与肉混合做成的汤;巾羹是芹菜与肉做成的汤;葑羹是芜(wú)菁(jīng)的叶子与肉做成的汤;苦羹则是用苦菜和肉混合做成的汤(何介钧等,1992)。根据所用的肉的不同,还有“牛肉醢羹” “猪肉白羹”等不同的种类。这些汤菜都是礼仪食品,也反映了汤菜在当时的菜肴中占据着主要的地位,这一点与先秦时期的食文化相比较,没有太大的变化。
鱼的烹调主要是用文火烤干,然后用竹签穿起来,稍有点特别。这究竟是为随葬品而特别烹调的还是当时的日常饮食方式,不太能确定。蛋是按原样随葬的,不太清楚当时的人是如何食用的。
再看其他的菜肴、烹饪方法,基本是当时的史书中已出现的名称,其中盐、酱、蜂蜜、酒曲、醋等调味品是西汉之前就开始使用的。但因为食物早已腐化变质,用量多少、如何搭配已很难搞清楚了。
【蔬菜的温室栽种】
17.
西汉的桓宽曾写过《盐铁论》一书。书中批评了汉代人的生活,认为与远古民风淳朴时代的日常生活相比,汉代已腐败堕落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但现代人却可将作者的意图反用之,从这些议论中推测出许多有关汉代日常生活的细节。《散不足》一章中提到了饮食文化的变化。通过这些描述,可了解到汉代不仅比以往朝代的饮食生活要丰富,而且饮食习惯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里的“以往”似指周代)。例如,以往的人们只吃成年的家畜,到了汉代,开始追求食物的柔软,开始食用幼羊、幼猪、幼鸟等,而且这种嗜好非常流行。
另外,以往的人们注意动植物的成长周期,而到了汉代,人们无视这样的过程,竟然在春天吃繁殖期的鹅,秋天吃还未成年的幼鸡。蔬菜放在温室里培养,冬天也可以吃到韭菜和葵。
2 000年前就已有了温室栽培,听起来有点夸大其词,而事实上这却是有根据的。汉元帝时期,即公元前三四十年代,掌管皇帝饮食的部门“太官”为在冬季也能栽培葱和韭菜等,便在屋顶上圈起一个棚,昼夜用炭火提高温度,促使蔬菜生长加快(《汉书•循吏列传•召信臣》)。这里提到的是宫廷中的事,而《盐铁论》中所说的是民间所进行的温室栽培。
18.
宴会上所用的食物也发生了变化。据《盐铁论•散不足》记载,以往村子里的酒宴上,年长者的桌上会摆放好几个盛着佳肴的器皿,年轻人只能站着吃酱和一个肉菜。但到了汉代,在招待客人的结婚筵席上,会出现豆汤和精白的小米以及醋拌或烹调的肉。宴会上还会摆放许多带骨头的肉,或烧烤的食物。野味和水产包括甲鱼、鲤鱼、小鹿、鱼子、鹑、河豚、鳗鱼等多种食物,水果有橘子、槟榔,调味品有醋、盐等。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各阶层之间的食物差异缩小了。以往,牛只有在诸侯祭祀时才使用,到了汉代,比较富裕的庶民在祭祀时也开始把牛作为供品,中层阶级的人们也开始宰杀以往士大夫只有在祭祀时才使用的羊和猪来祭神。以前贫穷的人只能使用鱼和豆来祭祀,现在连这些人也开始使用鸡和猪作为供品了。
【汉代也有“大排档”】
19.
自汉代开始,城市里出现了餐饮业。《盐铁论•散不足》中对餐饮店的情况及销售的食物做了一番描述:
原文:
古者,不粥饪(rèn),不市食。及其后,则有屠沽,沽酒市脯鱼盐而已。今熟食遍列,殽(yáo)施成市,作业堕怠,食必趣时。
译文:
以往人们不卖烹调好的食物,也不在市场上买吃的。到了后来,才有杀猪、宰牛、卖酒的,不过也就卖酒、卖肉干、卖鱼、卖盐罢了。但现在,街上店铺里熟食摆满了柜台,菜肴陈列成了一个市场。人们干活偷懒,饮食却热衷于追求季节的美味。
随着商业、手工业的发达,雇佣人员增加;而城市的扩大使得居住地和工作地之间的距离扩大。职业分工的细化刺激了餐饮业的产生和发展。此前,餐饮业做生意的对象是旅客,其后成了当地居民享乐或社交的一种方式。而从事建筑业或手工业的人员在外饮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促进了餐饮业的发展和规模化。
20.
四川省彭州市的古墓中出土了东汉时的画像砖,上面十分生动地描绘了当时餐饮业的繁荣。
从所销售的食物来看,使用了各种食材和烹饪方法。如猪肉放在火上烤,韭菜和蛋一起炒,煮烧好的狗肉切成片,用马肉做汤,等等。鱼在锅中放些油煎煮,肝煮熟后切成片。鸡先用酱煮,冷却后盛在盘里。羊肉则是用盐来腌制的,还有用家畜的胃做成的干肉、煮乳羊等。豆烧煮成甜的味道,幼鸟和雁可煮成汤。还有各种味道的干货、瓠(hù)子花、上等的谷物、烤全猪等。
从上面所提到的菜肴可以看到,街道各处饮食店、摊贩、熟食店制作出各种菜肴,已形成有相当规模的餐饮业。
与现代不同,汉代的饮食习惯是每人一膳,这一点与先秦时代没有两样。汉代人脱了鞋,进屋在席子上坐下。饮食的时候,使用叫作“案”的膳桌。膳桌上摆放饭和盛菜肴的碗碟等。食器多用漆器,也有漆器的勺和匙,勺是舀菜时使用的,匙是舀饭时使用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