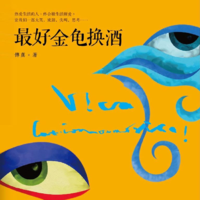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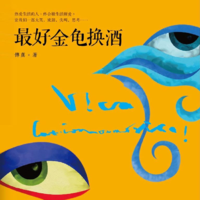
PART20 阿根廷为谁哭泣(1)
1.
世界尽头的想成为英国人的讲西班牙语的意大利人。
在英国的八年中,我认识和了解最多的人群,除了中国人和英国人之外,依次是法国人、印度人和阿根廷人。
法国是英国的邻居,印度是英国的前殖民地,这两个都好理解,可是天晓得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阿根廷人生活在伦敦!无论如何,这些年相处磨合下来,我自认为对阿根廷人有了相当的了解。这是一个国民性极其强烈的民族,而最大的特征就表现为他们如出一辙的忧郁和悲观。我的同事尼可拉斯会在任何应该或不应该的情况下陷入悲观的情绪当中——“We are in crisis!”工作中的任何一点变动都会促使他拧着眉头向大家发出警报。“我要崩溃了!”则是伊尼斯小姐的口头禅,苍白的脸色和颤抖的嘴唇暗示着她随时崩溃的可能性。
2.
还有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高傲。伊尼斯走起路来总以类似模特步的姿态行进,脚底像装了个小小弹簧,下巴抬得高高,你需要抬起头才能接触到她的目光。伊尼斯纤瘦得可怜,胃口也像只小鸟,她却从来不觉得自己瘦,甚至总觉得自己还不够瘦,对可口可乐的爱好是她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弱点”。我猜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女同事在她眼中可能都与猪猡无异……
大家都对此大惑不解,而我的阿根廷朋友盖比却见怪不怪地笑了:“去过布宜诺斯艾利斯你就知道了,那里的每一个女人都想变得更瘦,无论身材如何……你知道吗?阿根廷人在整容手术上花的钱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都要多,厌食症的发病率也是全世界最高的……”
我张口结舌地看着他。
“不过,”他又补上一句,“首都以外的阿根廷人其实挺正常的。记住,奇怪的事情都只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在阿根廷
3.
不知为什么,我认识的所有阿根廷人都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告诉我这个世界尽头大都会的种种千奇百怪之处,绝对令人匪夷所思——我从未想过这座城市会与整容手术和心理分析扯上关系。一直以来,我想象中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是繁华而浪漫的“南美巴黎”,是王家卫《春光乍泄》中有机会“由头来过”的天涯海角,是博尔赫斯笔下巨大的迷宫——房舍重叠不可企及,虚幻而又拥挤,到处都是战争英雄的鬼魂、动不动就掏刀子的小混混和探戈舞者……
4.
欣赏过巴里洛切湖区如瑞士般的青山绿水,把所有的烦恼都丢弃在世界尽头的火车站,穿着钉鞋徒步世界上最大的冰川感受过令人窒息的纯净与磅礴,在马德林港目睹了航空母舰般的南方露脊鲸以及不计其数的企鹅、海豚、海狮和海象……经过的地方大多地广人稀,一路见到的为数不多的阿根廷人果然相当正常。带着有限的认知和无限的好奇心,我和铭基终于来到了传说中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中文译作“好空气”。在刚刚抵达的那个下午,我的鼻子立刻识别出了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好空气——烘焙咖啡豆略带点焦味的香气混合着烤牛肉的浓郁脂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咖啡馆和烤肉店呢?每个街角总有一间,中间还有更多间,而且全都坐满了人。
5.
第二个巨大的冲击是 ——天哪!真瘦!布市的女性怎么全都如此苗条?!我几乎是在一瞬间就彻底地理解了伊尼斯对于“瘦”这件事的执着——peer pressure(来自同伴的压力)实在太大了!除了苗条,大多数女人的妆容服饰也是一丝不苟,中老年女性个个都好像刚从美发店出来,中产街区的太太们一身打扮更是无懈可击。走在大街上,我总忍不住惊叹于她们完美的外表,以及为了维持这完美所必须投入的精力与金钱。据说达尔文当年经过布宜诺斯艾利斯时也曾为之倾倒,感叹说他希望英国女人也能拥有此地女性那样“天使”般的优雅。我自惭形秽地欣赏着这些玲珑优雅的女人,觉得她们简直美得不太真实……话说回来,有些人的确不太“真实”——盖比不是说过吗?布市的富人一向热衷于整容手术和硅胶植入……
6.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们疯狂地崇拜美貌,据说一多半的青春少女都梦想着成为模特。虽然我觉得此地的男性也惊人的英俊有型,虽然他们也会在服饰和整形手术上花钱,但这仍是个大男子主义盛行的社会,这意味着——只有女人变胖或变老是不可原谅的。
盖比认为这一切都不正常。“事实上,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知道自己不正常,”他耸耸肩,“所以大家都去看心理医生。你知道吗?布市人对三件事最上瘾: 足球、牛肉、心理分析。在我们那儿,心理医生比人类还多。”
7.
心理分析?!我的第一反应是好笑和不可置信,可是此后每当我向其他的阿根廷朋友提起时,得到的都是肯定的答复和郑重其事的说明。他们告诉我,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世界心理分析之都”,人均拥有的心理医生人数排名全球第一!尼可拉斯的太太就是一名心理医生,可是来到英国后却找不到工作,只好在服装店当起了店员。在英国这并非属于普罗大众的领域,而布市人却并不觉得看心理医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很多人每周都去两三次,连普通人都可以熟练地运用心理学术语。伊尼斯说她从上小学就开始看心理医生了,很多人甚至认为心理分析对于形成健康的人格至关重要。
8.
当然,也有些人是为了赶时髦,还有些则把拥有一个心理医生当作身份的象征。然而更普遍的原因是:人们觉得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不看心理医生简直活不下去。
“穷人也看心理医生吗?负担得起吗?”我有点怀疑。
阿根廷朋友罗宾说:“有些公费医疗系统里的心理医生会提供免费的心理分析,很多工会的医疗保险也涵盖了每年几十次心理分析的费用。”
我无话可说了。这件事初听觉得有趣,渐渐地却有点叫人毛骨悚然——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每个人都病了吗?这怎么可能呢?我知道阿根廷人备受高通胀和经济衰退的困扰,可也不至于忧郁到不看心理医生就活不下去吧?阿根廷早已不再是独裁国家了,是什么东西仍在压迫着人们的心灵呢?
9.
“你根本就不明白,”伊尼斯用她一贯的忧郁眼神看着我,“我们被困在那里,那个世界的尽头。我们被整个世界遗忘了。”
当时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浪漫的解释。然而真的来到阿根廷以后,我发现对“自己正身处世界尽头”这件事的感受反而不那么真切了。达尔文在19世纪初参观火地岛时非常刻薄地说那里的居民几乎不能算是人类,是他所见过最原始的。可当我们来到世界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时,发现这里也早已充斥着“文明”社会的一切便利与弊病。旅游业发展得如火如荼,每一家餐厅和酒吧都打着“世界尽头”的招牌,城里到处都是即将出发去南极游玩的邮轮乘客,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冲锋衣涌进大街小巷,宛如一场来势汹汹的龙卷风。世界尽头并非想象中的冷酷仙境,反而充满了人间烟火的气息。
10.
可我仍能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伊尼斯的感受。她的意思是:他们并非心甘情愿地生活在世界尽头,而是“被困在那里”的。
在南美洲的其他地方如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差不多十个人里有五个是纯血的印第安人,三到四个是欧洲和原住民的混血,只有一个是欧洲血统的白人。然而当我们走在阿根廷的土地上,却发现这里的人们基本上都是欧洲人种。他们不像其他拉美国家的新移民那样与当地土著融合,而绝大多数印第安人都早已在蔓延的瘟疫和“征服沙漠”活动中被灭绝了。阿根廷的意大利移民为数甚众,我在英国认识的所有阿根廷人都是意大利人的后裔,他们凭借祖辈的血缘很容易地拿到了意大利国籍,也因此获得了在所有欧盟国家工作和居住的许可。
11.
“国多财则远者来。”19世纪中叶的阿根廷正经历着无比繁荣的黄金岁月,新法律为对外投资、贸易和移民打开大门,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移民纷至沓来寻找更好的生活。这个国家拥有几近无限的自然资源可供“挥霍”,辽阔的潘帕斯草原提供着世上最肥沃的土壤,不用怎么费力耕种就能收获奇迹。到了20世纪初,阿根廷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新移民中很多人一夜暴富,财富传奇令人如痴如醉。从那时起,阿根廷人就养成了出手阔绰的消费习惯,我曾在同时代不少欧洲作家的小说中看到对“阿根廷暴发户”来到欧洲疯狂消费的描写。他们想把欧洲的一切都运回阿根廷——油画、家具、汽车、建筑……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广场上矗立着从欧洲运来的雕像,道路以进口鹅卵石铺就。人们财大气粗,信心满满。
12.
“我们整个国家都是进口的,”博尔赫斯写道,“这里的每个人都来自别的地方。”
然而大多数人都只是来寻找easy money。阿根廷不像美国,建立并真正塑造这个国家的人们却并没有坚定的理想,没有与新大陆同荣辱共命运的信念。他们只是一群背井离乡的欧洲贫民,梦想发财却又思乡成疾。有些人很快暴富,但即便他们住在阿根廷,却仍把西班牙或意大利当成祖国,一年有好几个月都待在欧洲。
即使是现在,很多阿根廷人仍不愿意承认他们与这片大陆的关系。他们认为自己比其他任何拉美国家都要好。在他们看来,与其说阿根廷是美洲大陆最南端的某个第三世界国家,不如说是欧洲的一部分。盖比曾告诉我一个在拉丁美洲疯狂流传的笑话:一个阿根廷人是一个想成为英国人的讲西班牙语的意大利人……
13.
而黄金岁月转瞬即逝。从未有哪个国家经历过这样的大起大落。通货膨胀不断增长,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曾经比许多欧洲国家都要富裕的阿根廷经济持续衰落并几度崩溃,几乎要以第三世界的状态来请求财政援助。阿根廷人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但又不知究竟是哪里出了错,又该归咎于谁。
思乡的忧郁渐渐转变为宿命论式的悲观和对自我身份的憎恶,包括伊尼斯在内的很多阿根廷人都认为自己是历史的受害者,被困在世界的尽头,只能回头去看大洋的彼岸——他们的祖先曾经离开的地方,他们自己本应出现的地方。
14.
而事实上,我的这些阿根廷朋友们也的确“逃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到了他们“本应出现的地方”。
历史塑造了一个民族,也因此塑造了人民的个性。我原以为阿根廷人的悲观忧郁源自70年代残酷的军人政权,然而身处被浩瀚的南大西洋和广阔的潘帕斯草原所包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呼吸着空气中沉积的忧郁,我开始意识到它其实与这个国家本身一样老。
行走的母亲
15.
博尔赫斯说他很难相信布宜诺斯艾利斯竟有开端——“我感到它如同空气和水一般永恒。”据说这位文学大师痴迷于在夜晚漫步城中,感受这个城市,然后将那些陌生而相似的街道在笔下转化为迷宫的故事。
五月广场(Plaza de Mayo)则毫无疑问是这个迷宫的心脏。它是所有庆典和政治活动的中心,见证了这个国家跌宕起伏的历史。在这个圆形的广场上,革命爆发又被镇压,将军推翻了总统,然后又轮到自己被赶下台。贝隆夫妇站在总统府“玫瑰宫”的阳台上演讲,马拉多纳在一片欢腾中高高举起1986年的大力神杯。这里有胜利的欢呼和庆祝,也有骚乱、枪声和斑斑血迹。
16.
1945年10月9日,劳工部长胡安·贝隆在军队内部的反对声中被迫辞职,并一度被关进监狱,工会随即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一百多万人在五月广场聚集,要求释放贝隆。他们成功了——贝隆几天后就被释放,而四个月后他就当选为总统。从那以后,在国定假日来到五月广场就变成了一种传统。人们先是来看贝隆,后来又来看他的妻子,因为贝隆夫人也开始演讲了。她站在那个粉红色的小阳台上,两只拳头握成一个攻击性的姿态,号召她的人民“为贝隆战斗到死”。她去世以后,上百万人来到这里哀悼。镜头一晃,广场上的蜡烛变成了尸体,那是发生在1955年的惨剧——在这里庆祝国庆节的人群遭到炸弹袭击,一场推翻贝隆的政变即将上演。
17.
如今的五月广场风平浪静,我和铭基绕着广场中央的方尖碑漫步,却忽然看见一堆人密密麻麻围在一起,外圈还有好几个人在不停地拍照。我爱看热闹,马上蹦高了往圈内“窥探”——中间站着一群戴着白色头巾的老太太,每个人都神情凝重地举着一张放大的照片,每张照片上都是一个年轻人的脸。
今天是……星期四!我忽然反应过来——原来是传说中的“五月广场母亲”啊!
从1977年开始,“五月广场母亲”们每个星期四下午都在这里聚集,抗议阿根廷历史上最大的不公——他们的孩子在“肮脏战争”(Dirty War)中的“失踪”。
18.
1976年的一场军事政变将阿根廷推向了一个恐怖而残酷的历史时期,这个国家进入了它最黑暗的岁月。在军事独裁政府的统治下,1976至1983年间,阿根廷大约有三万个左派学生、知识分子、记者、工人丧生,至少九千人“失踪”,而拘捕和杀害的过程往往并不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因此被称为“肮脏战争”。大多数遇难者并非革命游击队,很多人只不过是简单地表露了对专制、残酷和混乱的不满。
孩子们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消失。母亲们年迈体弱,手无寸铁,不知该去哪里寻找,只好来到总统府前苦苦追问,要求军政府对此做出解释。没有人理会她们的诉求,母亲们唯一能做的便是手挽着手围绕广场行走,在警察的注视下一圈又一圈地行走。她们被警告,被恐吓,甚至有几位母亲被投入河中杀害,然而她们并没有畏缩。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母亲们不停地追问,母亲们不断地行走。
19.
1983年,阿根廷军政府倒台。1986年,这个国家再次举行了民主选举。在“五月广场母亲”和无数阿根廷人的共同努力下,到了21世纪初,曾经参与专政的军队成员终于开始陆续接受审判。母亲们要求严惩当年的刽子手,以此告慰那些被杀害和被“失踪”者的灵魂。三十多年过去了,母亲们绝不宽恕,母亲们还在行走。
只是不知“失踪”者可有几人生还?我看着这些貌不惊人的母亲们,她们挽着手袋,穿着老派的裙子和皮鞋,看起来就像外出散步的邻家老太太,谁能想到她们拥有如此惊人的勇气?谁知道她们的心里到底有多苦?她们举着失踪儿女的照片——被放得巨大的照片,你几乎能从那巨大中感受到母亲的悲愤与痛苦,虽然她们仍在祈祷着奇迹的出现——让失踪的重现,让死去的活着。很多照片旁边都有同样一句浸满泪水的话:你在哪里?
20.
儿女们也许回不来了,然而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素未谋面的孙儿们也回不来了。在“肮脏战争”期间被绑架的几千名年轻女性中,有一百多人被确知已经怀孕。大多数孕妇在孩子出生后才被杀死,孩子生命的开始便是她们自己人生的终结。有些在集中营里出生的婴儿们被送去了孤儿院和收养机构,然而据说大多数婴儿都被警察和军官收养,有些人正是这些婴儿的杀父或杀母仇人。想想就令人不寒而栗啊——抢走敌人的孩子,让他们来模仿和崇拜自己,对于刽子手们来说,没有比这更彻底的胜利了。
21.
我小的时候读了一点点中国历史,看到源源不绝的天灾人祸、内外战乱,便觉得中国人简直是世界上最苦难的民族。长大以后才发现,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世界上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痛苦的记忆。尤其是来到拉丁美洲之后,耳闻目睹的苦难是如此之多,正在受苦的人们就活生生地站在你面前,你无法“理智”地用冰冷的数据去判断哪个国家的苦难更为深重,因为于每一个个体而言,每一桩悲剧都意味着整个宇宙的崩塌。
漫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我似乎感受到了脚下的历史之痛。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广场都铭刻着残酷的记忆和无法兑现的承诺。贝隆夫人演讲的阳台还在,学生们从中“消失”的咖啡店还在,建筑风格优雅的刑讯中心也还在。或许这样更好吧,只有直面历史之痛,伤口才会愈合得更快。
(未完待续)
文章转载自网络
请尊重知识产权
侵权可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