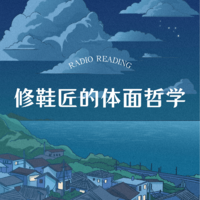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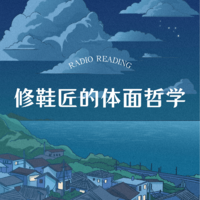
街边不起眼的修鞋摊,老鞋匠郑伯用布满裂口的手,修补着形形色色的鞋子,也修补着人们生活中微小的窘迫与尊严。在他眼中,一双干净完整的鞋,关乎一个人的“体面”。
在城市最繁华的商圈边缘,有一条被摩天大楼阴影覆盖的僻静小街。街角常年盘踞着一个极其简陋的修鞋摊——一张磨得油亮的矮脚木凳,一个装着各色皮料、线轴、鞋钉、胶水和工具的木箱,一把撑开的、边缘破损的旧伞,便是全部家当。摊主郑伯,年逾七旬,佝偻着背,像一棵被岁月风干了的老树根,深深地扎根在这方寸之地。他的双手粗糙得如同老树皮,布满黑褐色的裂纹和老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污渍。然而,就是这样一双手,却有着令人惊叹的灵巧,穿针引线、粘胶打磨、敲敲打打,动作娴熟而沉稳,带着一种沉浸其中的专注。
郑伯的生意,全靠老主顾和偶然路过的“急需”。在这个买新鞋比修旧鞋更便捷更划算的年代,修鞋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道不合时宜却令人心生敬意的风景。他收费低廉得可怜,补个鞋跟五块,换根拉链十块,有时遇到实在拮据的老人或学生,他摆摆手,一句“算了算了,顺手的事”,便不再计较。
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午后。一个穿着考究西装、拎着公文包的年轻白领,步履匆匆地经过鞋摊,突然“哎哟”一声,尴尬地停住了脚步。他抬起右脚,只见锃亮的黑色皮鞋后跟,一小块鞋跟胶皮不翼而飞,露出了里面难看的木质层,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发出“哒、哒”的怪异声响,与他一身的精英气质格格不入。他脸上满是懊恼和窘迫,环顾四周,似乎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郑伯抬起昏花的老眼,瞥见了年轻人的窘态。他放下手中正在粘胶的旧布鞋,用沙哑但清晰的声音招呼道:“小伙子,鞋跟掉了吧?拿过来,很快就好。”他的语气平静自然,没有一丝看笑话的意思,仿佛这只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
年轻人犹豫了一下,或许是实在无法忍受那“哒哒”的声响和路人偶尔投来的目光,最终还是尴尬地脱下那只“瘸腿”的皮鞋,穿着袜子踩在冰冷的地面上,局促地站在一旁。郑伯接过鞋,浑浊的眼睛凑近那缺失的鞋跟处仔细看了看。他从木箱里翻找出一块颜色、纹理都极其接近的黑色橡胶皮料,用铅笔在皮料上比划着轮廓,再用一把锋利的小刀,手腕沉稳地切割、修整。动作不快,却精准得如同外科手术。接着,他清理掉鞋跟上残留的旧胶,涂上特制的强力胶水,小心翼翼地将新切好的皮料对准位置,用力按压贴合。最后,用小锤子沿着边缘轻轻敲打加固。
整个过程不过十来分钟。郑伯把修好的鞋递还给年轻人:“好了,试试。胶还没完全干透,走路别太使劲跺脚就行。”
年轻人穿上鞋,走了几步,鞋跟稳稳当当,那恼人的“哒哒”声消失了,步伐重新恢复了自信。他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连声道谢,掏出钱包:“老师傅,多少钱?”
“五块。”郑伯伸出粗糙的手指比划了一下。
“五块?”年轻人显然有些惊讶于这低廉的价格,他掏出十块钱塞给郑伯,“不用找了,谢谢您,帮大忙了!”
郑伯却执意从油腻的围裙口袋里摸出五块皱巴巴的零钱,塞回年轻人手里:“说好五块就五块。举手之劳。”他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持。年轻人看着手里那五块钱,又看看老人沟壑纵横的脸和那双布满裂口、粘着胶水的手,最终没再推辞,郑重地道了谢,脚步轻快地汇入了人流。
“郑伯,您收那么少,图个啥?”旁边卖烤红薯的老王忍不住打趣,“这年头,五块钱够买啥?”
郑伯慢悠悠地拿起刚才放下的旧布鞋,继续粘着开胶的鞋帮,头也不抬地说:“老王啊,你卖红薯,暖的是人家的胃。我修鞋,修的是人家的路。”他顿了顿,用粗粝的手指抹平鞋帮上的胶水,“你看那小伙子,穿得那么体面,鞋跟坏了,走路一瘸一拐,多难看?心里也憋屈。花几块钱修好,他走得稳当了,心里也舒坦了。这钱,挣得心安。”
老王嘿嘿一笑,不再说话。郑伯的话很朴素,却像他手中磨得锃亮的鞋钉,直直地钉进了人心。
我常去郑伯那里给老父亲修他那双穿了几十年都舍不得扔的老式皮鞋。每次去,都能看到形形色色的鞋子摆在他脚边:有年轻姑娘断了跟的高跟鞋,有孩子踢破了头的小运动鞋,有老人开胶的棉布鞋,也有磨穿了底的旧皮鞋……每一双鞋,都承载着主人的一段路程,一段故事。郑伯对待它们,都如同对待一件需要精心修复的艺术品。他不仅修补破损,还会顺手把鞋面擦干净,给干裂的皮鞋涂上一点廉价的鞋油,让鞋子尽可能恢复几分“体面”。
有一次,一位衣着朴素、神色疲惫的清洁工阿姨,拿着一双鞋帮几乎完全撕裂的旧运动鞋来修。鞋很破旧,散发着汗味。郑伯没有丝毫不耐烦,仔细检查了裂口,摇摇头:“这口子太大了,布面都糟了,缝是缝不牢了。我给你想办法粘上,再打几个补丁加固,能穿,但肯定不好看。”阿姨局促地搓着手:“能穿就行,能穿就行!干活穿,不讲究好看,就是……便宜点行吗师傅?”
“行,”郑伯爽快地应下,“粘粘补补,三块钱吧。”他找出几块厚实的帆布头,剪成合适的形状,里外都仔细粘好、缝上加固线。虽然鞋子上多了几块难看的“补丁”,但确实结实了许多。阿姨感激地付了钱,穿上鞋,用力踩了踩,脸上露出安心的笑容。郑伯看着她的背影,对旁边的我说:“干他们这活儿,整天走路,费鞋。鞋要是破了,走路硌脚不说,心里也不得劲。穿双囫囵鞋,干活也踏实点。”
夕阳的余晖给郑伯佝偻的身影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边。他依旧埋着头,专注地对付着一只脱了线的皮鞋。那双布满裂口的手,在皮料、针线和金属工具间穿梭,动作依旧沉稳而充满力量。在他的摊位上,没有光鲜亮丽的商品,只有修补的痕迹和油污的浸润。然而,正是这双修补了无数双鞋的手,也在不经意间,修补着城市褶皱里那些微小却真实的窘迫与尊严。
他或许不懂什么高深的哲学,但他用一生的坚守诠释着一个最朴素的道理:一双干净、完整、能稳稳走路的鞋,是一个人行走于世最基本的“体面”。这份“体面”,无关贫富,关乎尊严。而郑伯,就是这喧嚣都市边缘,一位沉默的“体面”守护者,用他布满老茧的手和一颗温厚的心,让无数双疲惫或仓促的脚步,得以继续从容地丈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