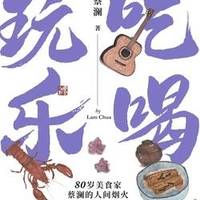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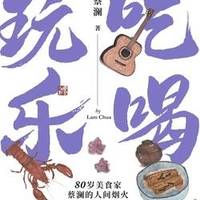
生活散文 之 吃喝玩乐:蔡澜的人间烟火07
第三章 奇人异士录
有些老友,忽然间想起,特别思念过往相处的一段时光。
小刀
01
认识尚·皮尔时,我还很年轻,在欧洲流浪。由马赛到里昂,曾到郊外的一个小邻村,和一户农民指手画脚地租了间房,就住下了一阵子。
每个小地方都有它的组织,一家大小集会的是教堂,唯有男人在一起聊天的,当然是那一间唯一的小酒吧了。落脚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往那里钻。
打从上了法国码头开始,我已经学会喝他们的酒,最平民化的是李基尔。它一定要混水来喝,颜色深褐,像白兰地,但加了水分之后就变成乳白。与其说像白兰地,不如形容为“滴露”消毒水更传神。而且,喝起来味道也的确像消毒水。用药草浸酒精的李基尔,又甜又苦,很呛喉,但是喝惯了会上瘾,口一渴便想起它。
02
酒吧中的几个大汉对我投以好奇的眼光。欧洲乡下人很单纯,但也不会随便和陌生人打交道。我那天不想先开口,就一直站在柜台后默默地喝酒。
肚子有点饿,叫了些火腿。先上桌的是面包,一长条。我向酒保要刀叉。酒保耸耸肩,摊开双手,表示没有。
没有?那其他人怎么进食?我往四周一看,法国土佬都是用自己带来的小刀把面包切开。
“当”的一声,一柄刀子飞来,插在我面前的柜台上。刀锋连木柄,加起来有手掌般长,能折叠,打开刀锋后,柄端有个小铁螺,向左边一扭,铁环顶着刀肉,不会折回来割伤手。
这柄刀还在微微地震动。它不像一般的利刃,没有杀伤力,不带侵略性或威胁性,只是一把和平的工具。
03
“拿去!”在柜台另一侧的老头儿说。他身体健壮,但略为肥胖。
我道谢后举起小刀,把面包摆好,就当锯木头一样地切下去。
周围一片哄笑。
老头儿摇摇头,把面包和刀子接过去,大拇指压在面包上,另外四根手指握着木柄,刀锋向内拉,一块块整齐地切开。
“这样。”老头儿示范。
我点点头,依样画葫芦,即刻成功,众人大乐。
接着,老头儿把一个玻璃罐子推过来,里面浸着很多的小四方块,如中国腐乳一样的羊脂芝士。此物奇臭,要渍于水中才不会发散味道,否则熏死人也。
拿起刀子当牙签,往芝士一插,我毫不客气地吃了一块。
04
老头儿拍拍我的肩膀,说:“那么臭的东西你也敢试!不错!”
我指着挂在墙上的火腿,“敢吃。”又指着香肠,“敢吃。”再指洋葱、大蒜,“敢吃。”最后指着那柄小刀,“不敢吃。”
众人大笑,围过来请我喝李基尔。老头儿伸出他的手:“我叫尚·皮尔。”
我大力握着,皮肤很粗糙,但我感觉到一阵阵的温暖。
从此,我一直随着尚·皮尔到处走。
他的儿女已长大,他不用自己劳动,闲来无事,老喝红酒。坐在树下,由袋中又拿出另一瓶,没有开酒器,他拔出小刀,向瓶盖左一插右一插,再轻轻地前后摇松,“啵”的一声,就把木塞挑了出来。
05
我们喝完了酒就躺下来睡午觉,厚厚的一层黄金落叶,是张很柔软的床。醒来遥望着小湖,老半天,动也不动。我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生活,倒也不觉得闷,反正他要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两个人有时候连一句话也不说。
掏出蓝色的硬烟盒,抽了一支又粗又肥的烟,他说:“拿去。”
我接过来,看烟没有滤嘴,烟叶是黑色的,可见一定很烈,是法国普通人爱抽的“吉妲牌”。吉妲,吉卜赛人的意思,盒上画着一个拿着扇子的跳舞女郎。
吸了一口,喉咙好像给几十只手搔了痒,即刻大力咳嗽起来,满脸涨得发紫。尚·皮尔又大笑。
我瞪了他一眼,继续睡觉。
听到“唰唰”的声音,我偷看了一下,只见老头儿用小刀削树枝、挑洞。不一会儿,他雕出一管烟筒,递给我,说:“拿去。”
06
树上有很多成熟的核桃,我想尝尝。摇树干,哪摇得动?气起来,干脆脱了鞋子扔去,几次都打不中,打中了只掉一两颗。
尚·皮尔摇摇头,他伸手把落叶拨开,原来遍地都是核桃,像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
我把两颗核桃抓在手中,用力地压,有时核桃爆得开,有时挤压半天都无效。试了几次,已经手软。尚·皮尔一直冷眼地看。我不认输,掏出手帕,包了几颗在里面,抓紧手帕的四个角,往树干大力摔去,核桃裂开,肉完整,我贪心地吃得满嘴。尚·皮尔对这个开核桃的方法颇为欣赏,自己试了几次,痴痴地笑。
捡了一个大粒的,尚·皮尔拿小刀细心地雕琢。完成之后交给我。
07
那个核桃让他刻出了一个侧面的男人面孔,壳上的皱痕,看上去是一头长长卷卷的假发。正在想这个人像谁的时候……
“路易十三,路易十三!”尚·皮尔顽皮地笑。
我捧腹大笑。
临走的前一天,我乘巴士到里昂镇上,在大酒铺买了一瓶X. O白兰地。
“拿去。”我学尚·皮尔的口头禅,把酒交给了他。
当晚,他在家里请我吃饭。
火炉中的松木发出香味。
08
尚·皮尔的太太和他一样肥胖,双颊红得像苹果,从大铁锅中舀出浓厚的牛肉汤来,命令我多吃一碗。
老头儿拿刀切面包蘸着汤入口。
“这把刀,不离你。”我说。
“是的。”尚·皮尔张开双掌,“它是我的第十一根手指。”
“刀很小,不会伤人吗?”我问。
尚·皮尔望着小刀,沉入回忆:“广阔的原野,一大片芥菜花,像黄色的海。几个孩子在花田中,为一个满脸雀斑的少女决斗。对方拔出这把小刀,我把它抢了过来。”
说完他摊开左手,有一道很深的疤痕。我禁不住为他心痛。
09
“后来呢?”
“后来?后来这个少女感动了,长大了嫁人。你看这个大肥婆,就是她!”尚·皮尔指着他太太大声地笑。
他老婆走过来拧他的肚皮,但也很开心地笑。
隔天,尚·皮尔坚持要送我到火车站。
车开动了,我探出身子来向他招手,他跟跑了几步,把一样东西塞在我手中,是那把小刀!
看着他肥胖的影子渐小,好似他失去了什么东西。是的,他已把他身体的一部分,送给了我。
老人与猫
10
岛耕二先生在日本影坛占着一席很重要的位置,大映公司的许多巨片都是由他导演,买到香港来上映的有《金色夜叉》和《相逢音乐町》等,相信老一辈的影迷会记得。
他原是位演员,样子英俊、身材魁梧,当年六英尺高的日本人不多。
我和岛耕二先生认识,是因为请他编导一部我监制的戏,谈剧本时常到他家里去。
从车站下车,徒步十五分钟方能抵达,在农田中的一间小屋,有个大花园。
一走进家里,我看到一群花猫。
年轻的我,并不爱动物,被那些猫包围着,有点恐怖的感觉。
岛耕二先生抱起一只,轻轻抚摸:“都是流浪猫,我不喜欢那些富贵的波斯猫。”
11
“怎么一养就养那么多?”我问。
“一只只来,一只只去。”他说,“我并没有养,只是拿东西给它们吃。我是主人,它们是客人。‘养’字,太伟大,是它们来陪我罢了。”
我们一面谈工作,一面喝酒。岛耕二先生喝的是最便宜的威士忌Suntory Red,两瓶一共有1.5升的那种,才卖500日元。他说宁愿把钱省下来买猫粮。喝呀喝呀,很快就把那一大瓶东西干得精光。
又吃了很多岛耕二先生做的下酒小菜。肚子一饱昏昏欲睡,就躺在榻榻米上。常有腾云驾雾的美梦出现,醒来发觉是那群猫用尾巴在我脸上轻轻地扫。
12
也许我浪费纸张的习惯,是从岛耕二先生那里学来的。当年面纸还是奢侈品,只有女人化妆时才肯花钱去买,但是岛耕二先生家里总是这里一盒那里一盒的,随时抽几张来用。他最喜欢为猫擦眼睛,一见到它们眼角不清洁就向我说:“猫爱干净,身上的毛用舌头去舔,有时也用爪洗脸,但是眼缝擦不到,只有由我代劳了。”
后来,到岛耕二先生家里,成为每周的娱乐。之前我会带着女朋友到百货公司买一大堆菜料,两人捧着上门,用同一种鱼或肉举行料理比赛,岛耕二先生做日本菜,我做中国菜。最后,由女朋友评判,我较有胜出的机会,女朋友是我的嘛。
我们一起合作了三部电影,最后两部是在星马出外景。遇到制作上的困难,岛耕二先生的袖中总有用不完的妙计,抽出来一件件地发挥,为我这个经验不足的监制解决问题。
13
半夜,岛耕二先生躲在旅馆房中分镜头,推敲至天明。当年他已有六十多岁。辛苦了老人家,但是我并不懂得去痛惜,不知道健壮的他,身体已渐差。
岛耕二先生从前的太太是大明星、大美人轰夕起子,后来的情妇也是年轻貌美的,但到了晚年,却和一位面貌平凡、开裁缝店的中年妇人结了婚。
羽翼丰满的我,已不能局限于日本,飞到世界各地去监制制作费更大的电影。不和岛耕二先生见面已久。
逝世的消息传来。
我不能放弃一班工作人员去奔丧,第一个反应并没想到他悲伤的妻子,反而是:那群猫怎么办?
14
回到香港,见办公室桌面有一封他太太的信。
……他一直告诉我,来陪他的猫之中,您最有个性,是他最爱的一只。(啊,原来我在岛耕二先生眼里是一只猫!)
他说过有一次在槟城拍戏时,三更半夜您和几个工作人员跳进海中游水,身体沾着漂浮着的磷质,像会发光的鱼。他看了好想和你们一起游,但是他印象中的日本海水,连夏天也是冰凉的。身体不好,不敢和你们去。想不到您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拉他下海,浸了才知道水是温暖的。那一次,是他晚年中最愉快的一个经历。
逝世之前,NHK(日本广播协会)派了一队工作人员来为他拍了一部纪录片,题名为《老人与猫》,在此同时寄上。
我知道您一定会问主人死后,那群猫由谁来养?因为我是不喜欢猫的。
请您放心。
15
拜您所赐,最后那三部电影的片酬,令我们有足够的钱把房子重建。改为一座两层楼的公寓,有8个房间出租给别人。
在我们家附近有所女子音乐学院,房客都是爱音乐的少女。有时她们的家用还没寄来,就到厨房找东西吃,和那群猫一样。
吃完饭,大家拿了乐器在客厅中合奏。古典的居多,但也有爵士,甚至有披头士的流行曲。
岛先生死了,大家伤心之余,把猫分开拿回自己房间收留,活得很好……
读完信,我禁不住滴下了眼泪。那盒录影带我至今未动,知道看了一定哭得崩溃。
今天搬家,又搬出录影带来。
硬起心把它放进机器里。荧光幕上出现了老人,抱着猫,为它清眼角。我眼睛又湿,谁来替我擦干?
人间市标
16
人,像建筑物一样,都能成为市标。可惜的是,老建筑有时还会受到保护;而人,在他们活着时不去看看,就没机会了。
在中环永吉街的摊子中,领有牌照的,除了柠檬王那一家之外,就是一档卖毛笔的。八十二岁的李天祥先生,一辈子都在那里摆档,卖的毛笔便宜得令人发笑。档口拉了横布,写着:“为天下事读书写字,二十元七支。”
今天下大雨,以为他没做生意,看到他还是西装笔挺地站着。李先生曾经说过:“我只有两套西装,但是也要穿来尊重客人。”
文具店的毛笔都要卖到几十块钱一支,李先生的也是从内地进货,但不暴利,他笑着说:“在中环摆档摆了几十年,不发达的也只有我一个吧?”
如果把钱存起来,也算是笔小储蓄,但是他二十多年来从未间断,每年回家乡岭东,总是把钱捐给一所小学。领过他奖学金的学生都上过大学,现在担任起要职来了。
17
“子女呢?”我问。
“他们的书没念成。”李先生说,“不过很懂事,也不埋怨我把钱都捐光。”
“太太呢?”
“十年前过世了。”他没带悲伤,“我自己住在一个四百平方英尺的小房子里,漏水也不去修,能省几百块,学校就多几百块。”
每个收到李先生奖学金的同学,大概以为他是什么华侨富商,我真想抓他们来永吉街看看这个档口。
李先生每年都说有预感,再也做不下去,但每次到永吉街,还看得到他。偶尔,他会拿出一张嘉应商会的照片,说:“曾宪梓和我都是客家人,但是我是唯一没有办公室的董事。”
我笑了:“为你,我尊敬客家人。”
一技之长
18
书画文具店,知名的有上环的“文联庄”和油麻地的“石斋”。老板黄博铮先生,本身是一个书法家,与同好共创“甲子书法社”,一周一次在店里雅集,也教学生。
做这一行的,本身不爱好艺术不行,黄先生说:“市场很狭窄,没什么人肯干。”
我就是喜欢光顾这种“没什么人肯干”的铺子。“石斋”中各种文具齐全,单单宣纸就有上百种选择,我最爱用的是“仿古宣”。
字画收藏一久,白色或米黄色的纸,便会变成浅褐色或淡绿色。后者的颜色最美,看起来非常舒服,那种绿绿得可爱,像新摘的龙井。闻起来还有种香味,真个名副其实的古色古香。当今写字,不可能有这种效果,只有用“仿古宣”了。色彩一样,但没有香味,也只好接受。
19
店里也替客人接刻印的单。不收费用,直接让顾客和名篆刻家接触。我的大师兄孔平孙先生也帮人家刻,小师兄禤绍灿本来也在“石斋”挂作品,但近年来积极教拳,篆刻方面少去碰。古人说,做才子有二十种条件,琴棋书画后还有个“拳”字。绍灿师哥是真正的才子,我只是二十分之一才子。
这个年代,还有什么人对书画有兴趣呢?老板黄先生说:“主要客路是一些中产阶级,公务员和老师居多。他们收入稳定,空余时间控制得住,就会学字画了。但是近年来铁饭碗也打破了,客人又减少。”
“我们这一辈,也被父亲骂不学无术,”我说,“我相信青出于蓝,总有人肯学。”
“是的,”黄先生说,“有一技之长,至少老了可以摆摆摊写挥春,不必去当看更。”
二窟
20
小时候读电影书籍,看到一则名导演马荣·李莱经常来香港的事。
为什么来香港?拍戏吗?旅游吗?
答案完全不是。他来香港制造玩具。
很多电影人除了电影,一生不会干别的,他们以为电影已是一切,做其他事全部是旁门左道。生意更与艺术搭不上关系。
殊不知电影是一种燃烧生命的行业,那么多人在干,失败者居多。出众的,少之又少。一直维持在顶峰是个梦,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实现,就算卓别林、库布里克等聪明绝顶的大师,至晚年,也呈现疲倦状。
21
生涯之中,总是有起有落。电影人,大多数以为自己是天才,只有往上爬,一部比一部卖座,没有倒下来的日子。电影行业那么吸引人,是有它的道理的。
就算一直倒霉下去,有一天忽然拍部莫名其妙的戏,即刻翻身。所以大家都死守下去。
一部电影的卖座,全靠天时地利人和,有时即便拍得好,但说仆街就仆街。
电影人不信邪:“我从前也拍过卖座戏,这一部不行,下一出证明给观众看。”
从前是用别人的钱拍的,现在为了证实自己的才华,把老本也投资下去。这一次,又完蛋了,储蓄完全花光。
22
一切靠自己。到了晚年,潦倒的不少。昔日风光,很难回头。享受惯了,余生怎么过?
所以有钱的时候应该做点小生意,最好是自己的爱好,像童心未泯的李莱,有什么比做玩具更好?只要不花完自己的投资,年轻时就得做。
而人生最大的投资,莫过于培养本行之外的兴趣,专心研究,成为副业。所谓狡兔三窟,电影人的聪明,何止狡兔?至少也要二窟呀!
田记花店
23
对白兰花的迷恋有增无减,在九龙城街市买完菜,就走过衙前塱道口,到七十一角落铺的隔壁田记花店买几朵,才上班去。
可惜此花有季节,每年开两次,夏天和深秋,过了那段时期,只有想念了。
今天习惯性地走过花档,竟然被我发现了:寒冷的岁暮,怎会有白兰花?
“泰国空运来的。”黄太说。
啊,怎么我想不到?那边热带,白兰变了种,一年四季都开。
那么微小的东西,装在透明塑料袋中,一共五朵,背后还用一片剪成锄形的香蕉叶衬着,卖四块钱。
“一箩箩用冰保鲜,不然很快坏掉。”黄太解释,“我知道你爱白兰,特地进货。”
真感谢她的好意,黄太在这儿开档,也有三十多年。已经六十多岁的她,前几年先生过世,儿子手不方便,在家。和儿媳妇两个人守档口。婆媳之间的关系,特别良好。
24 杀青段
“从哪儿买的?”我问。
“花墟呀。”她说,“每天五点钟就去采购。我住在马鞍山,三点多就起。”
“哇,”我问,“那么几点收档?”
“晚上八九点,”她说,“我睡得少。”
看见一盆盆的年花和橘子连花钵,搬运起来也不容易。
“是花墟的人运来的?”我问。
“不。”她指着停在档前的面包货车。走前一看,车里载满花。
“谁驾车?”我问。
“我自己呀!”黄太笑说。
档边常摆五六张空椅,是黄太从垃圾堆中捡回来的,任由七八十岁老先生、老太太坐着休息。
黄太说:“和他们聊天,我觉得很年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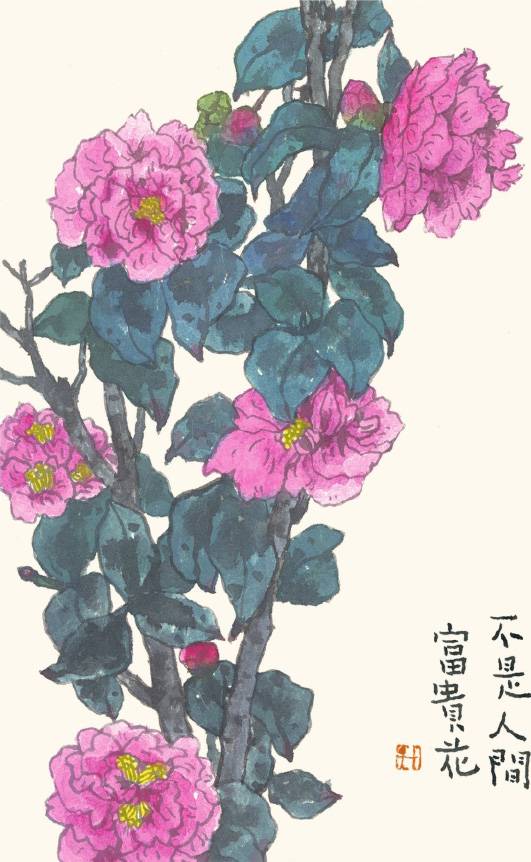
相关链接:
01-03 第一章 壹 294593 贰 892289 叁 387172
04-05 第二章 壹 527581 贰 636788
06 第三章 壹 490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