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 一截土墙 / 02 一村懒人
03 留下这个村庄 / 04 只剩下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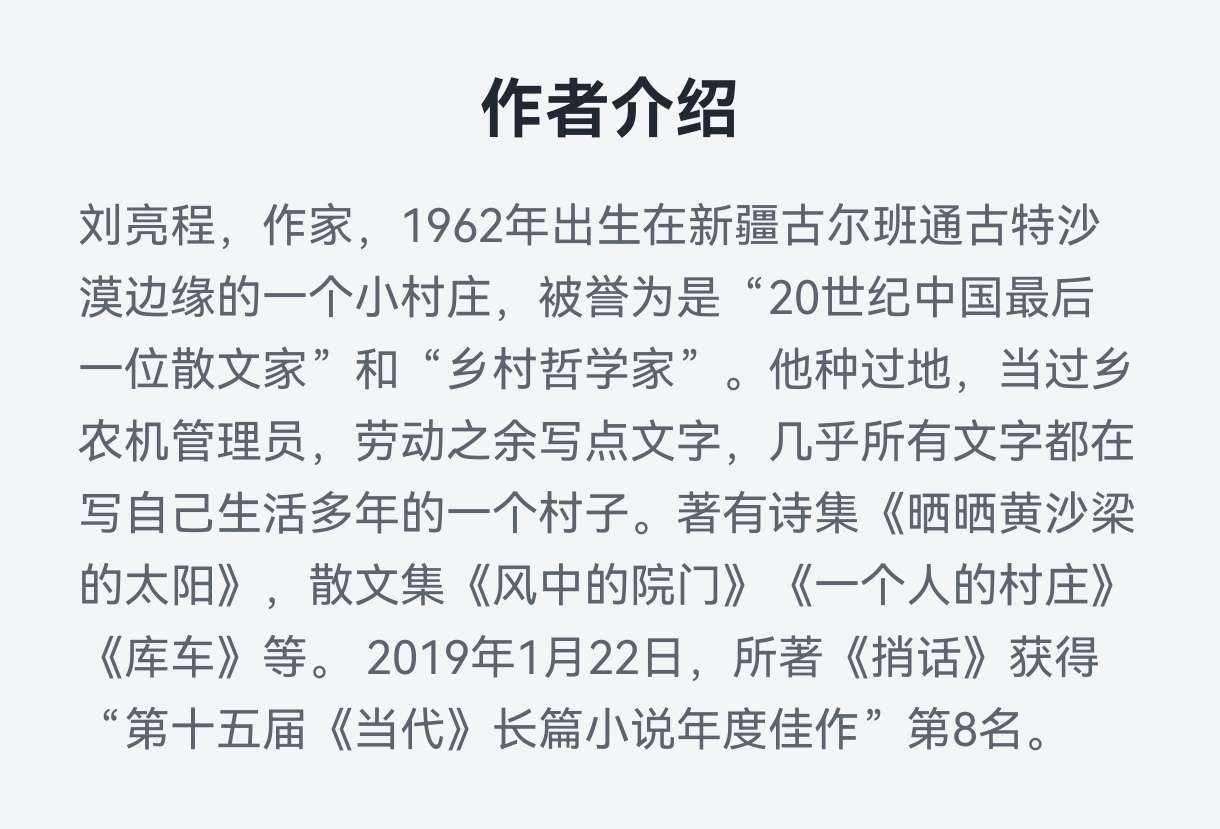
1、我走的时候还年轻,二十来岁。不知我说过的话在以后多少年里有没有人偶尔提起。我做过的事会不会一年一年地影响着村里的人。那时我曾认为什么是最重要迫切的,并为此付出了多少青春时日。现在看来,我留在这个村庄里影响最深远的一件事,是打了这堵歪扭的土院墙。
我能想到在我走后的二十年里,这堵土墙每天晌午都把它的影子,从远处一点一点收回来,又在下午一寸寸地覆盖向另一个方向。它好像做着这样一件事:上午把黑暗全收回到墙根里,下午又将它伸到大地的极远处。
2、一堵土墙的影子能伸多远谁也说不清楚,半下午的时候,它的影子里顶多能坐三四个人,外加一条狗,七八只鸡。到了午后,半个村庄都在阴影中。再过一会儿,影子便没了尽头。整个大地都在一堵土墙的阴影里,也在和土墙同高的一个人或一头牛的阴影里。
我们从早晨开始打那截墙。那一年四弟十一岁,三弟十三岁,我十五岁。没等我们再长大些那段篱笆墙便不行了。根部的枝条朽了,到处是豁口和洞。几根木桩也不稳,一刮风前俯后仰,呜呜叫。
3、那天早晨篱笆朝里倾斜,昨天下午还好端端,可能夜里风刮的。我们没听见风刮响屋檐和树叶。可能一小股贼风,刮斜篱笆便跑了。父亲打量了一阵,过去蹬了一脚,整段篱笆齐齐倒了。靠近篱笆的几行菜也压倒了。我们以为父亲跟风生气,都不吭声地走过去,想把篱笆扶起来,再栽几个桩,加固加固。父亲说,算了,打段土墙吧。
母亲喊着吃早饭啦。太阳从我们家柴垛后面,露出小半块脸。父亲从邱老二家扛来一个梯子,我从韩四家扛来一个梯子。打头堵墙得两个梯子,一头立一个,两边各并四根直椽子,拿绳绑住,中间槽子里填土,夯实,再往上移椽子,墙便一截一截升高。
4、我们家的梯子用一根独木做的,打墙用不着。木头在一米多高处分成两叉,叉上横绑了几根木棍踏脚,趴在墙上像个头朝下的人,朝上叉着两条腿,看着不太稳当,却也没人掉下来过。梯子稍短了些,搭斜了够不着,只能贴墙近些,这样人爬上去总担心朝后跌过去。梯子离房顶差一截子,上房时还容易,下的时候就困难,一只脚伸下来,探几下挨不着梯子。挨着了,颤颤悠悠不稳实。只有我们家人敢用这个梯子上房。它看上去确实不像个梯子。一根木头顶着地,两个细叉挨墙,咋看都不稳当。
5、一天中午正吃午饭,韩三和婆姨吵开了架,我们端碗出来看,沿听清为啥。架吵到火爆处,只听韩三大叫一声“不过了”,砰砰啪啪砸了几个碗,顺手一提锅耳,半锅饭倒进灶坑里,激起一股烟灰气。韩三提着锅奔到路上,抡圆了一甩,锅落到我们家房顶上,“腾”的一声响。我父亲不愿意了,跑出院子。
“韩三,你不过了我们还要过,房顶砸坏了可让你赔。”
6、下午,太阳快落时,我们在院子里乘凉,韩三进来了,向父亲道了个歉,说要把房顶上的锅取回去做饭。婆姨站在路上,探着头望,不好意思进来。父亲说,你自己上去拿吧。我这房顶三年没漏雨,你一锅砸的要是漏开了雨,到时候可要你帮着上房泥。韩三端详着梯子不敢上,回头叫来了儿子韩四娃,四娃跟我弟弟一样大,爬了两下,赶紧跳下来。
“没事,没事。”我们一个劲喊着,他们还是不敢上,望望我们,又望望梯子,好像认为我们有意要害他们。
7、后来四娃扛来自家的梯子,上房把锅拿下来。第二年秋天那块房顶果然漏雨了。第三年夏天上了次房泥,我们兄弟四个上的,父亲也参加了。那时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没什么是我不能干的。
原以为父亲会带着我们打那堵墙。他栽好梯子,椽子并排绑起来,后退了几步,斜眼瞄了几下,过来在一边架子上跺了两脚,往槽子里扔了几锨土,然后扛着锨下地去了。
父亲把这件活扔给我们兄弟仨了。
8、我提夯,三弟四弟上土。一堵新墙就在那个上午缓慢费力地向上升起。我们第一次打墙,但经常看大人们打墙,所以不用父亲教就知道怎样往上移椽子,怎样把椽头用绳绑住,再用一个木棍把绳绞紧别牢实。我们劲太小,砸两下夯就得抱着夯把喘三口气。我们担心自己劲小,夯不结实,所以每一处都多夯几次,结果这堵墙打得过于结实,以致多少年后其他院墙早倒塌了,这堵墙还好端端站着,墙体被一场一场的风刮磨得光光溜溜,像岩石一样。只是墙中间那个窟窿,比以前大多了,能钻过一条狗。
9、这个窟窿是我和三弟挖的,当时只有锨头大,半墙深。为找一把小斧头我们在刚打好的墙上挖了一个洞。墙打到一米多高,再填一层土就可以封顶时,那把小斧头不见了。
“会不会打到墙里去了。”我望着三弟。
“刚才不是你拿着吗,快想想放到哪了。”三弟瞪着四弟。四弟坐在土堆上,已经累得没劲说话。眼睛望着墙,愣望了一阵,站起来,举个木棍踮起脚尖在墙中间画了一个斧头形状。我和三弟你一锨我一锨,挖到墙中间时,看见那把小斧头平躺在墙体里,像是睡着了似的。
10、斧头掏出后留下的那个窟窿,我们用湿土塞住,用手按瓷。可是土一干边缘便裂开很宽的缝隙,没过多久便脱落下来。我们再没去管它,又过了许久,也许是一两年,或者三五年,那个窟窿竟通了,变成一个洞。三弟说是猫挖通的,有一次他看见黑猫趴在这个窟窿上挖土。我说不是,肯定是风刮通的。我第一次扒在这个洞口朝外望时,一股西风猛窜进来,水桶那么粗的一股风,夹带着土。其他的风正张狂地翻过院墙,顷刻间满院子是风,树疯狂地摇动,筐在地上滚,一件蓝衣服飘起来,袖子伸开,像了半截身子的人飞在天上。我贴着墙,挨着那个洞站着。
11、风吹过它时发出“喔喔”的声音,像一个人鼓圆了嘴朝远处喊。夜里刮风时这个声音很吓人。像在喊人的魂,听着听着人便走进一场遥远的大风里。
后来我用一墩骆驼刺把它塞住,根朝里,刺朝外,还在上面糊了两锨泥,刮风时那种声音就没有了。我们搬家那天看见院墙上蹲着坐着好些人,才突然觉得这个院子再不是我们的了,那些院墙再也阻挡不住什么,人都爬到墙头上了。我们在的时候从没有哪个外人敢爬上院墙。从它上面翻进翻出的,只有风。在它头上落脚,身上栖息的只有鸟和蜻蜓。现在那些蜻蜓依旧趴在墙上晒太阳,一动不动。它们不知道打这堵墙的人回来了。
12、如果没有这堵墙,没有二十年前那一天的劳动,这个地方可能会长几棵树、一些杂草,也可能光秃秃,啥也没有。如果我乘黑把这堵墙移走,明天蜻蜓会不会飞来,一动不动,趴在空气上。
如果我收回二十年前那一天(那许多年)的劳动,从这个村庄里抽掉我亲手给予它的那部分——韩三家盖厨房时我帮忙垒的两层土块抹的一片墙泥,冯七家上屋梁时我从下面抬举的一把力气,我砍倒或栽植的树,踏平或踩成坑凹的那段路,我收割的那片麦地,乘夜从远处引来的一渠水,我说过的话,拴在门边柱子上的狗,我吸进和呼出的气,割草喂饱的羊和牛——黄沙梁会不会变成另个样子。
13、或许已经有人,从黄沙梁抽走了他们给予它的那部分。有的房子倒了,有的路不再通向一个地方,田野重新荒芜,树消失或死掉。有的墙上出现豁口和洞,说明有人将他们垒筑的那部分抽走了。其他人的劳动残立在风雨中。更多的人,没有来得及从黄沙梁收回他们的劳动。或许他们忘记了,或许黄沙梁忘记了他们。
过去千百年后,大地上许多东西都会无人认领。
14、在外面时我老担心这个村庄会变得面目全非。我在迅速变化的世界里四处谋生。每当一片旧屋拆毁,一群新楼拔地而起,我都会担心地想到黄沙梁。它是否也在变成这样呢。他们把我熟悉的那条渠填掉,把我认识的那堵墙推倒,拆掉那些土房子。
如果这样,黄沙梁便永远消失了。它彻底埋在一个人心里。这个人将在不久的年月离去,携带一个村庄的全部记忆。从今往后,一千年一万年,谁都不会再找到它。
15、活着的人,可能一直在害怕那些离去的人们再转头回来,认出他们手中这把锨、脚下这条路,认出这间房子,这片天空这块地。他们改变世界的全部意义,就是让曾经在这个世界生存过的那些人,再找回不到这里。
黄沙梁是人们不想要的一个地方,村里人早对它失望了,几十年来没盖一间新房子,没砌半堵新墙。人们早就想扔掉它到别处去生活。这个村庄因此幸运而完整地保存着以前的样子。没有一点人为变故,只有岁月风雨对它的消磨——几乎所有的墙,都泥皮脱落。我离开时它们已斑驳地开始脱落,如今终于脱落光,露出土块的干打垒的青褐墙体。没有谁往这些墙壁上再抹过一把泥。
16、这是一村庄懒人。他们不在乎这个地方了。
那条不知修于何年从没淌过水的大渠,也从来没碍过谁的事,所以留存下来。只是谁家做泥活用土时,到渠沿上拉一车,留下一个坑。好在这些年很少有人家动过泥土。人已懒得收拾,所有地方都被眼看惯、脚走顺、手摸熟。连那段坑洼路,也被人走顺惯。路上还是二十年前我离开时的那几个坑和坎。每次牛车的一个轱辘轧过那个坎时,车身猛地朝一边倾一下,辗过那个坑时,又猛地朝另一边歪一下。我那时曾想过把这段路整平,很简单的事,随手几锨,把坎挖掉,土垫到一边的坑里,路便平展展了。
17、可是每次走过去我便懒得动了。大概村里人跟我一样,早习惯了这么一倾一歪,没这两下生活也就太平顺了。这段路的性格就是这样的,它用坑坎逗人玩。牛有时也逗人玩,经过坑坎路段时,故意猛走几步,让车倾歪得更厉害些。坐在车上打盹的人被摇醒。并排坐着的两个人会肩撞肩头碰头。没绑牢实的草会掉下一捆。有时会把车弄翻,人摔出好远,玩笑开过头了,人恼火了,从地上爬起来,骂几声路,打两鞭牛,一身一脸的土。路上顿时响起一阵笑语哞叫。前前后后的车会停住,人走过来,笑话着赶车人,帮着把翻了的车扶起来,东西装好。
18、如果路上再没有车,空荡荡的。一个人在远路上翻了车,东西很沉,其他人从另外的路上走了。这人只有坐在路边等,一直等到天黑,还没有人,只好自己动手,把车卸了,用劲翻过空车,一件一件往上装东西,搬不上去的,忍痛扔掉。这时天更黑了,人没劲地赶着车,心里坎坎坷坷的,人、牛、路都顿觉无趣。
草长在墙根,长在院子里、门边上,长在屋顶和墙缝……这些东西不妨碍他们了。他们挨近一棵草生活,许多年前却不是这样的。
19、那时家家户户有一个大院子,用土墙或篱笆围着。门前是菜地,屋后是树和圈棚,也都高高低低围拢着。谁家院子里长了草,会被笑话的。现在,几乎所有院子都不存在。院墙早已破损,门前的菜地荒凉着,只剩下房子孤零零立在那里。因为没有了围墙,以前作为院子的这块与相邻的路和荒野便没有区别。草涌进来,荒野和家园连成一片,人再不用锨铲它们。草成了家人中的一个,人也是草丛中的一棵。雨水多的年成村子淹没在荒草里,艾蒿盖地,芦苇没房。人出没草中,离远了便分不清草在动还是人在动。干旱年成村子光秃秃的,堆着些没泥皮的土房子。模样古怪的人和牲畜走走停停。
20、更多年成半旱不旱,草木和人,死不了也活不旺势。人都靠路边走,耷拉着头,意思不大地过去一日又一日。草大多聚到背阴处,费劲地长几片叶,开几朵花儿,最后勉强结几粒籽。
草的生长不会惊噪人。除非刮风。草籽落地时顶多吵醒一只昆虫最后的秋梦。或者碰伤一只蚂蚁的细长后腿。或许落不到地上。一些草籽落到羊身上,一些落在鸟的羽毛上,落在人的鞋坑和衣帽上,被带到很远,有水的地方。
21、在春天,羊摇摇屁股,鸟扇扇翅,人抖抖衣服,都会有草籽落地。你无意中便将一颗草籽从秋带到春。无意的一个动作,又将它播洒在所经之地。
有的草籽在你身上的隐蔽处,一藏多年。其间干旱和其他原因,这种草在大地上灭绝,枝被牛羊吃掉,火烧掉。根被人挖掉,虫毁掉。种子腐烂掉。春天和雨水重新降临时,大地上已没有发芽的种子。春天空空来临。你走过不再泛绿的潮湿大地,你觉得身上痒痒,禁不住抖抖身子——无论你是一条狗、一只羊、一匹马、一只鸡、一个人、一只老鼠,你都成为大地春天唯一的救星。
22、有时草籽在羊身上的厚厚绒毛中发芽,春天的一场雨后,羊身上会迅速泛青发绿,藏在羊毛中的各种草籽,凭着羊毛中的水分、温度和养分,很快伸出一枝一枝的绿芽子。这时羊变得急躁,无由地奔跑、叫、打滚、往树上墙上蹭。草根扎不透羊皮,便使劲沿着毛根四处延伸,把羊弄得痒痒的。伸不了多久便没了水分。太阳晒干羊毛时,所有的草便死了。如果连下几场雨,从野外归来的羊群,便像一片移动的绿草地。
23、人的生死却会惊动草。满院子草木返青的时候,这个家里的人死亡或出生,都会招来更多人。那时许多草会被踩死,被油腻滚烫的洗锅水浇死,被热炉灰蒙死。草不会拔腿跑开,只能把生命退回到根部,把孕育已久的花期再推迟一季。
那是一个人落地的回声,比一粒草籽坠落更重大和无奈。一个村庄里只有有数的一些人,无法跟遍地数不清的草木相比——一种草或许能数清自己。一株草的死亡或许引起遍地草木的哀悼和哭泣。我们听不到。人淹没在人的欢乐和悲苦中。无论生和死。一个人的落地都会惊动其他人。
24、一个人死了,其他人得帮衬着哭两声,烧几页纸、送条黑障子。一个人出生了,其他人也要陪伴着笑几下,送点红绸子、花衣服。
生死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事。在村里,这种看似礼节性的往来实则是一种谝工。我死的时候你帮忙挖坑了,你死了我的子孙会去帮你抬棺木。大家都要死是不是。或者你出生时我去贺喜了,我去世时你就要来奔丧。这笔账你忘了别人会为你记住。
25、我没想这样早地回到黄沙梁。应该再晚一些,再晚一些。黄沙梁埋着太多的往事。我不想过早地触动它。一旦我挨近那些房子和地,一旦我的脚踩上那条土路,我一生的回想将从此开始。我会越来越深地陷入以往的年月里,再没有机会扭头看一眼我未来的日子。
我来老沙湾只是为了离它稍近一些,能隐约听见它的一点声音,闻到它的一丝气息。我给自己留下这个村庄,今生今世,我都不会轻易地走进它,打扰它。
26、我会克制地不让自己去踩那条路、推那扇门、开那页窗……在我的感觉中它们安静下来,树停住生长,土路上还是我离开时的那几行脚印、牲畜和人,也是那时的样子,走或叫,都无声无息。那扇门永远为我一个人虚掩着,木窗半合,树叶铺满院子,风不再吹刮它们。
我曾在一个秋天的傍晚,站在黄沙梁东边的荒野上,让吹过它的秋风一遍遍吹刮我的身体。我本来可以绕过河湾走进村子,却没这样做。我在荒野上找我熟悉的一棵老榆树。连根都没有了。根挖走后留下的树坑也让风刮平了。我只好站在它站立过的那地方,像一截枯木一样,迎风张望着那个已经光秃秃的村子。
27、我太熟悉这里的风了。多少年前它这样吹来时,我还是个孩子。多少年后我依旧像一个孩子,怀着初次的,莫名的惊奇、惆怅和欢喜,任由它一遍遍地吹拂。它吹那些秃墙一样吹我长大硬朗的身体。刮乱草垛一样刮我的头发。抖动树叶般抖我浑身的衣服。我感到它要穿透我了。我敞开心,松开每一节骨缝,让穿过村庄的一场风,同样呼啸看穿过我。那一刻,我就像与它静静相守的另一个村庄,它看不见我。我把它的一草一木,一事一物,把所有它知道不知道的全拿走了,收藏了,它不知觉。它快变成一片一无所有的废墟和影子了,它不理识。
28、还有一次,我几乎走到这个村庄跟前了。我搭乘认识不久的一个朋友的汽车,到沙梁下的下闸板口村随他看亲戚。一次偶然相遇中,这位朋友听说我是沙湾县人,就问我知不知道下闸板口村,他的老表舅在这个村子里,也是甘肃人。三十年前逃荒进新疆后没了音信,前不久刚联系上。他想去看看。
我说我太熟悉那个地方了,正好我也想去一趟,可以随他同去。
29、我没告诉这个朋友我是黄沙梁人。一开始他便误认为我在沙湾县城长大,我已不太像一个农民。当车穿过那些荒野和田地,渐渐地接近黄沙梁时,早年的生活情景像泉水一般涌上心头。有几次,我险些就要忍不住说出来了,又觉得不应该把这么大的隐秘告诉一个才认识不久的人。
故乡是一个人的羞涩处,也是一个人最大的隐秘。我把故乡隐藏在身后,单枪匹马去闯荡生活。我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走动、居住和生活,那不是我的,我不会留下脚印。
30、我是在黄沙梁长大的树木,不管我的杈伸到哪里,枝条蔓过篱笆和墙,在别处开了花结了果,我的根还在黄沙梁。他们整不死我,也无法改变我。他们可以修理我的枝条,砍折我的桠杈,但无法整治我的根。他们的刀斧伸不到黄沙梁。
我和你相处再久,交情再深,只要你没去过我的故乡,在内心深处我们便是陌路人。
汽车在不停的颠簸中驶过冒着热气的早春田野,到达下闸板口村已是半下午。这是离黄沙梁最近的一个村子,相距三四里路。我担心这个村里的人会认出我。
31、他们每个人我看着都熟悉,像那条大路那片旧房子一样熟悉。虽然叫不上名字。那时我几乎天天穿过这个村子到十里外的上闸板口村上学,村里的狗都认下我们,不拦路追咬了。
我没跟那个朋友进他老舅家。我在马路上下了车。已经没人认得我。我从村中间穿过时,碰上好几个熟人,他们看一眼我,原低头走路或干活。蹿出一条白狗,险些咬住我的腿。我一蹲身,它后退了几步。再扑咬时被一个老人叫住。
“好着呢嘛,老人家。”我说。
32、我认识这个老人。我那时经常从他家门口过。这是一大户人家,院子很大,里面时常有许多人。每次路过院门我都朝里望一眼。有时他们也朝外看一眼。
老人家没有理我的问候。他望了一眼我,低头摸着白狗的脖子。
“黄沙梁还有哪些人?”我又问。
“不知道。”他没抬头,像对着狗耳朵在说。
“王占还在不在?”
“在呢,”他仍没抬头。“去年冬天见他穿个皮袄从门口过去。不过也老掉了。”
我又问了黄沙梁的一些事情,他都不知道。
“那个村子经常没人,”他说,“尤其农忙时一连几个月听不到一点人声。也不知道在忙啥。”
33、我走出村子,站在村后的沙梁上,久久久久地看着近在眼底的黄沙梁村。它像一堆破旧东西扔在荒野里。正是黄昏,四野里零星的人和牲畜,缓缓地朝村庄移动。到收工回家的时候了,烟尘稀淡地散在村庄上空。人说话的声音、狗叫声、开门的声音、铁锨锄头碰击的声音……听上去远远的,像远在多少年前。
我莫名地流着泪。什么时候,这个村庄的喧闹中,能再加进我的一两句声音,加在那声牛哞的后面,那个敲门声前面,或者那个母亲叫唤孩子的声音中间……
我突然那么渴望听见自己的声音,哪怕极微小的一声。
我知道它早已经不在那里。
34、我想听见风从很远处刮来的声音,听见树叶和草屑撞到墙上的声音,听见那根拴牛的榆木桩直戳戳划破天空的声音。
什么都没有。
只有空气,空空地跑过去。像黑暗中没有偷到东西的一个贼。
西边韩三家院子只剩下几堵破墙,东边李家的房子倒塌在乱草里,风从荒野到荒野,穿过我们家空荡荡的院子。再没有那扇一开一合的院门,像个笨人掰着手指一下一下地数着风。再没有圈棚上的高高草垛,让每一场风都撕走一些,再撕走一些,把呜呜的撕草声留在夜里。
35、风刮开院门时一种声音,父亲夜里起来去顶住院门时又是另一种声音——风被挡住了。风在院门外喊,像我们家的一个人回来晚了,进不了门。我们在它的喊声里醒来,听见院门又一次被刮开,听见风呼呼地鼓满院子,顶门的歪木棍“扑腾”倒在地上,然后一声不吭。它是歪的,滚不动。
我一直清楚地记得父亲在深夜走过院子的情景,记得风吹刮他衣服的声音。他或许弓着腰,一手按着头上的帽子,一手捂着衣襟,去关风刮开的院门。刮风的夜晚我们都不敢出去,或者装睡不愿出去。躺在炕上,我们听见父亲在院子里走动,听见他的脚步被风刮起来,像树叶一样一片接一片飘远。
36、那样的夜晚我总有一种隐隐的担心。门大敞着。我总是害怕父亲会顶着风走出院门,走过马路,穿过路那边韩三家的院子,一直走进西边的荒野里,再不回来。
许多年前,我的先父就是在这样一个深夜,独自从炕上坐起来,穿好衣裳出去,再没有回来。那时我太小了,竟没听见他开门关门的声音,没听见他走过窗口的脚步和轻微的一两声咳嗽。或许我听见了,肯定听见了,只是我还不能从我的记忆里认出它们。
37、那时候,一刮风我便能听见远远近近的各种声音。地下密密麻麻的树根将大地连接在一起,树根之间又有更密麻的草根网在一起,连树叶也都相连着。刮风时一片叶子一动,很快碰动另一片,另一片又碰动一片,一会儿工夫,百里千里外的树叶像骨牌一样全哗啦啦动起来。那时我耳朵贴在黄沙梁任何一棵树根上,就能听见百里外的另一棵树下的动静。那时我随便守住一件东西,就有可能知道全部。
38、可是现在不行了,什么都没有了。大树被砍光,树根朽在地里。草成片枯死。土地龟裂成一块一块的。能够让我感知大地声息的那些事物消失了,只剩下风,它已经没有内容。
虽然也栽了些树,一排一排地立在渠边地头,但那些树的根连在一起不知要多少年时间。它们一个不认识一个。那些从别处移来的树,首先不认识这块地,树根一埋进土里便迷路了。不像以前那些树,根扎得又深又远,自己在土层中找到水和养分。现在的树都要人引水去浇,不然就渴死了。
《刘亮程散文精选集》01-15(共20篇)
709467、676961、713771、788695、916307、626523、427541、602983、 833917、243887、762547、681469、809073、874281、本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