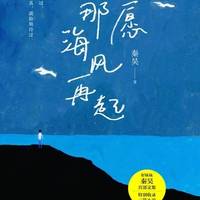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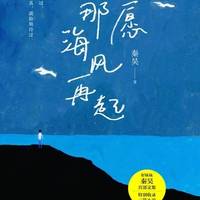
人物散文 之 但愿那海风再起17
编者:本篇是台湾民歌集合,选了一些歌曲,如读文过程中有时间可点击BGM聆听,也可读完后再欣赏
第三部分
那年我们路过小小的山巅
01
“台湾民歌”这个主题其实我不应该写,因为涉及的人和歌的体量都很庞大,如果要把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都说一说,那这本书都不够写。况且也已经有人写得太好,整理得太清晰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来看看。我只是此刻想到一首歌,可以代表我的感受,就是施孝荣的《拜访春天》。台湾民歌流行时期对我来说就像华语乐坛的春天,我不是那个时期出生的,没有经历过那个萌动蓬勃的年代,只是无数次从那些美好的歌曲中,不断地回去拜访那个春天。
这里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台湾民歌”中的民歌二字并不等同于我们平时说的“民歌”,而是更接近“民谣”,只是“台湾民歌”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改来改去没啥必要,就沿用了下来。
02
但似乎说成民谣也有点不符合当下对民谣的定义了,台湾民歌时期是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涉及的音乐风格其实是多种多样的,虽然确实有很多现在听来是民谣风格的作品,譬如叶佳修的作品,但也有比较古典风格的创作者和歌手,譬如李泰祥、齐豫、许景淳,也有很上口很流行的抒情歌曲,譬如梁弘志、蔡琴、郑怡的歌曲,也有比较注重原住民文化的胡德夫,也有偏流行摇滚的丘丘合唱团,还有致力于推广“台湾闽南语”传统民谣的陈达,甚至还包括在后期对民歌进行批判和颠覆的罗大佑……太多太多了,不同观念,不同风格,不同特色,汇聚一堂。
所以台湾民歌其实并不代表一个风格,就好像巴黎画派也并不是一种风格,后印象派也不是一种风格一样,这种界定方式其实是采取时间+地区维度的,我的理解是,从某个具体事件之后的某段时间内,在一个特定区域里的一些人各自或合作完成了某个共同目标或某种集体诉求,然后在更新更进步的潮流或架构到来时被拆解,融入更新的架构中或干脆消退,成为一个记忆符号。
03
我用这个逻辑整理一下,台湾民歌运动大概就是:从1976年李双泽在淡江大学砸可乐瓶开始,一些台湾地区的年轻创作人和歌手,各自或协同出了大量音乐作品,完成了李双泽号召的“唱自己的歌”这个共同目标,给华语乐坛贡献了新鲜的血液和巨大的推动力以及人才储备,这些力量随后逐渐形成或融入了以大唱片公司为主导的华语流行音乐行业架构,到80年代中期,台湾民歌的概念就已经被稀释到无法成为一个单独派别了。至此,华语乐坛的盛夏到来了。
我觉得从1980年台湾地区第一家唱片公司——“滚石唱片”成立,实际上就已经在拆解“台湾民歌”这个概念了,把民歌中的各种面貌都融入了自己的流行音乐工业化体系。这就是当代社会大家都明白的道理:资本总是有办法收编一切当下时兴的元素和新兴的力量(连反消费主义都可以被收编用来构建成一种新的消费概念)。
04
台湾民歌对如今的年轻人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知不知道都无所谓,知道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不知道也不妨碍继续享受如今的华语音乐,因为它的血液早已渗透到华语音乐的细枝末节。
但台湾民歌这个概念对我来说却很重要,它相当于我听音乐的一种初恋情结,相当于我与音乐初遇一刹那所看到的美丽。
完全无法想象自己不曾有过那样的相遇:
不曾在儿时的黑胶唱片中听到那样的意象: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外婆的澎湖湾》,词曲:叶佳修);
05
不曾在音乐课中听包美圣用最清丽的歌声描述童年乐事:池塘里水满了雨也停了,田边的稀泥里到处是泥鳅(《捉泥鳅》,词曲:侯德健);
不曾听到银霞用少女细软的声音唱出一株植物带来的落寞: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兰花草》,作词:胡适,作曲:陈贤德、张弼);
不曾听到蔡琴唱出这样的柔情: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恰似你的温柔》,词曲:梁弘志);
不曾听过齐豫披着长发唱出这样的荒凉: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橄榄树》,作词:三毛,作曲:李泰祥);
06
不曾听过郑怡用那冲破云霄的声音唱出民间歌手陈达的故事:抱一支老月琴,三两声不成调,老歌手琴音犹在,独不见恒春的传奇(《月琴》,作词:赖西安,作曲:苏来);
不曾听过徐晓菁和杨芳仪用最和谐的二重唱表达关于秋的感怀:听我把春水叫寒,看我把绿叶催黄,谁道秋下一心愁,烟波林野意幽幽(《秋蝉》,词曲:李子恒);
不曾听过李建复用威严的声音唱出民族的阵痛: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地擦亮眼(《龙的传人》,词曲:侯德健);
不曾听过杨弦和罗大佑各自用不同的旋律谱写思乡的时代悲歌: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那酒一样的长江水,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乡愁四韵》,作词:余光中);
07
不曾在王梦麟的歌声中一瞥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欢锣喜鼓咚得隆咚锵,钹铙穿云霄,范谢将军站两旁,叱咤想当年。战天神护乡民,魂魄在人间,悲欢聚散总无常,知足心境宽(《庙会》,作词:赖西安,作曲:陈辉雄);
不曾听过陈明韶把乡愁揉碎了融入远行脚步中的浮云游子意:浮云一样的游子,行囊装满了乡愁,虽然努力往前走,乡愁一样入梦中(《浮云游子》,词曲:苏来);
不曾听过金智娟用沙哑亢奋的声音呐喊:就在今夜我要离去,就在今夜一样想你(《就在今夜》,词曲:邱晨);
不曾听过黄大城巍峨的声音中广阔的天地:茫茫沧海中,有我一扁舟,碧海蓝天为伴。我随轻舟航,航向海天会,海鸥轻风为伍(《渔唱》,词曲:靳铁章);
08 杀青段
不,我完全无法想象自己没有听到过这些歌,没有被他们的声音震撼、感动、温暖过。如果没有这些作品,我可能也无法写下自己的那些作品,无法“唱自己的歌”,无法把自己的所思所想传到别人的耳中、心中。
如果音乐有四季,不知道现在烈火烹油的华语音乐市场是处在哪个季节了。如果人生也有四季,那我的人生肯定已经不是春天了。但所幸春天的气息早存在于我的每一个肺泡里,使得我一张嘴就能回到春天那小小的山巅,在那些歌里去拜访美好的年代。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
有雨细细浓浓的山巅
你飞散发成春天
我们就走进意象深深的诗篇
——《拜访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