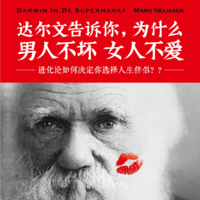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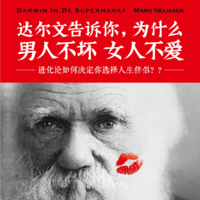
为什么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1.
2008年,我在日本京都一场关于人类行为和进化社会的会议上,听一个心理学家发言。他在实验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通常所称的“反社会(常规)”的一些特征可能会产生非同寻常的效果。“这个,”他说,“跟所谓的人类性格的‘黑暗三性格’有关,比如自恋、神经质、不择手段。”最后一个则跟狡猾和无知并行。在心理学领域早已得出结论,这些特征经常集中出现在一个人身上,被视为三合一的“黑暗三性格”。人们不应当为这些个性感到骄傲。个性如此的人经常被他人回避,几乎没有朋友。“可以料想的是,”发言者说,“这些个性在很久以前也是无益的。谁的脑门被扣上了这黑暗的三合一印章,就只能听天由命,很少有机会获得集体的支持。”
2.
这时,讲话人的研究突然指向了另一个方向。他说:“然而那些自恋、神经质和不择手段的年轻小伙子通常有很多女朋友,性经历也比‘乖’男人丰富。相比稳定的恋爱关系,他们的恋爱持续时间都较短。不过,女孩们好像都很喜欢这种反社会常规的坏男孩。”讲话人有些幸灾乐祸地说。他观察得出的结论与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完全相反——一个反社会常规的人反而性经验更丰富,根据达尔文的理论,这是不正确的。这个结论让我皱起了眉头。这为什么跟我们通常对人类进化论的认识背道而驰呢?这就体现出传统心理学和进化生物学之间的一个有趣的冲突。于是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敲这篇文章。这还引起我邻座的小小不满,他想偷瞄我在写什么,可惜不会荷兰语。没想到开会竟然也能这么有意思!
3.
短暂的恋爱关系是个有趣的现象,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能带来一定的利益。倘若男人们使用这条繁殖策略,就能比那些乖乖谈恋爱、只跟其伴侣传宗接代的男人更快地繁衍出后代。他们根本就不用尽父亲的义务,甚至都不用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假设有这样一个采花大盗,四处大方地播散自己的精子,每个月都有一个女人为他怀孕,那么五年后,他就会有六十个子女。他完全没意识到自己拥有那么一大笔财富,不用付孩子们的学费,不用教孩子什么,不用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甚至连自己的孩子叫什么都不知道……然而孩子们却承载着他的基因。这就是进化的利益!乖爸爸听话地留在妈妈身边,同样的时间里最多只能让妈妈怀孕三次。看,还是有区别的吧。
4.
当然,现实中肯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就算采花大盗们再主动,也只能在梦里实现上述例子中那么多次成功的繁殖。况且,谈到进化,就要想到史前,想到十万年前人类的行为被自然选择、锻造的阶段,那时孩子成活的几率可小多了。
人类由于脑袋大所以早早地来到世上,其实还是太早了,所以需要更多的照顾和保护才得以生存。这时,有个乖爸爸在就好了,他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就是在一段长期的两性关系中,和妈妈一起把孩子带大。事实表明,我们祖先中的单亲妈妈把自己的孩子带大成人的可能性要小很多。所以,上文提及的那些超级主动却毫不严肃的家伙们的后代中的大多数,都无法成活。而好爸爸们的孩子则能活下来,至少,他们长大成人、传宗接代的机会要大得多。
5.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种男性的繁殖策略,每种都有各自的进化成功之处。这就解释了那些坏男孩的行为,但还没能解释女孩为他们倾倒的原因。当下,如果有女孩看上那些“黑暗三性格”男孩,就说明她们的曾曾曾祖母也应如此。这样看来,其中还是应该有一些进化优势的。人们通常料想的是,女人更倾心于严肃的、忠诚的、能长期尽到父亲职责的男人。这些男人至少能保证孩子能更好地活下去。说得没错,可是……
假设我们的曾曾曾祖母对那些采花大盗视而不见,从没有被他们迷住,那么这些先生也就无法将他们放纵的基因传承下去,如今我们也就不可能认识到他们的行为了。这样看来,曾经有许多曾祖母,就跟当下很多女士一样,倾心于那些花花公子。虽然这跟我们的进化直觉相抵触,不过还是可以解释的。
6.
女士们为那些花花公子倾倒,那么她们子女的基因也就倾向于短期恋爱关系和那些“黑暗三性格”男孩。这样一来,她们就可能有很多孙子孙女!拥有很多孙子孙女也是一种进化的成功。也许那些女士们生下的孩子成活机会较小,可一旦成活下来,儿子们就能跟他们的父亲一样,为她们生出很多孙子孙女。坏爸爸生出坏儿子,同样,女儿们也能把那些“坏”基因传给后代。
看看,我的故事快讲完了,结论是,那个拿着话筒讲话的心理学家的研究,不仅不跟达尔文理论背道而驰,反而成了一种印证。我合上笔记本的时候声音太响,引来了与会者们不满的目光。当大会主席问“有什么问题吗”时,我站起来,用大家都听得懂的语言向那个演讲者指出,他低估了进化生物学。说完之后,我还是不好意思地脸红了。下个演讲者的讨论已经开始了。都坐好,别说话了。
疼痛是进化论在胡扯吗?
7.
偷听别人说话可不是什么光荣的事,不过我还是无意地不光荣了一回。一个学生小组就进化论和创世论展开了辩论。具体论点如下:一个神,也就是创世论中创造生命的那个神,并没有尽职尽责,因为很多事物的结构都不够完好,比如人们会患癌症,引发战争,吃饭的时候会噎着……一个无所不能、心中有爱的创造者创造出包括人类在内的世间万物,总该追求完美,而不是半路撒手吧。所以肯定没有所谓的神存在,也没有创世,只有进化。
8.
“好吧,”其中一个学生开始陈述自己的观点,“那是不是因进化产生的一切都是完美的呢?就真的都那么好吗?就拿疼痛来说吧,有些人好多年甚至一生都在忍受疼痛。其中的作用又在哪儿呢?如果没用,这种身体机制又为什么得到进化了呢?这么说,是不是也该把进化论丢掉呢?”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在讨论疼痛的好处,不过并没有放在一个进化的学术背景中。疼痛有好处吗?如果有,它又为什么毁了有些人的生活呢?
9.
我本来想对那些争论的学生们说,我觉得,要理解疼痛是一种生物的适应性变化并不难。第一个支撑论点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出。我们,我是指所有脊椎动物的大脑和骨髓,都有非常复杂的结构来记录疼痛。第二,有一点很清楚,如果我们完全感觉不到疼痛,也就活不长了。那些患有罕见的先天疾病、感受不到疼痛的人,必须非常小心,不能伤了自己。他们通常很早就去世了。疼痛能传送身体有危险的信号,提示我们,阻碍身体正常运作甚至会带来生命危险的问题出现了。脚踝扭伤了,很疼,是要叫我们让那条腿好好休息,直到伤痛痊愈。这可是个极富价值的适应性变化,意味着感受疼痛的基因被进化选中,在万物中大规模地扩散开来。这可比人类的出现早多了,在几亿年前就发生了。
10.
当然,疼痛也是有代价的。它会消耗能量,减少进化推崇的其他活动,比如寻找食物、自我防卫、与伴侣筑巢等。如果大脑觉得疼痛持续的时间够长了,就会通过分泌安多酚来减少或消除疼痛。这种类似吗啡的止疼剂是我们的身体自行产生的,不过剂量通常不够,所以疼痛持续的时间比预警需要的时间要长很多。举个极端些的例子吧。有种病持续发作,带来很多疼痛,这又有什么好处呢?就此有两点可说。
第一,这种病本身并没有什么进化优势。要是我们的祖先得了癌症,可能很快就死了。病把人的身体掏空了,人没有足够的能量来采集食物、自我防卫等等。最后癌症就会索要致命的“过路费”。我们的科学和医学知识使如今得了癌症的人能够活下去,至少比以前活得久多了,而代价就是疼痛。我们通过人工方法让这个警告信号持续作响的同时,也控制住了病魔。
11.
第二,我们这么在意疼痛是因为疼痛的感觉很不舒服。疼痛一点都不好玩,不过这正符合其功效。要是好玩的话,我们都会想要,从而去寻找病痛。而如果疼痛没什么感觉,我们也不会在意和留心。所以,疼痛必须是不舒服的。对我们来说,那种不适感本可以成为一种提醒。不过进化关心的不是这个!自然选择挑中了疼痛的预警功能,却没有在意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并未对此做出改变。而且疼痛大多出现在生命终结前夕,尽管那场生与死的斗争有时会持续很长时间。不管听起来有多么冷酷残忍,那时我们早已被自然选择淘汰,因为繁殖的可能已经不存在了。无利的疼痛并没有被自然选择排除,因为自然选择不能对其产生控制,所以疼痛可能一直存在。
12.
正如那位学生所言,这一切都表明,无利的疼痛是一种不良的适应性变化,所以进化过程才被拿来讨论。此外,生产时的疼痛也是多余的。有人曾说过,动物的无痛生产会导致母爱的缺失,不过这从来都未被证实过。分娩疼痛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生物适应性变化,即繁殖的副产品。在进化的过程中,人类的大脑越来越大,头颅也随之变大,分娩时产生的疼痛亦愈演愈烈。
然而,出生的通道骨盆却不会按照人类头颅的比例扩大,因为扩张的骨盆会给女人的行动带来巨大障碍。由此,人类的孩子早早地来到世上(意味着需要更多长辈的照顾),分娩也就变得比早前困难了。人类大脑的生长有利有弊,疼痛即为弊,不过这并没有成为进化的阻碍。
13.
以上分析很好地印证了以下事实:进化中的适应性变化不可能总达到最佳状态,或者说,从来都达不到最佳状态。一种结构、一个系统或者一种行为被自然选择相中,是因为较其他而言,它们更有利。如果器官中的一个变化让这个器官相比从前能够更好地运作,那么这个变化就会被自然选择相中,改善后的器官会取代老器官,一代代传下去。说得更准确些,是进步的基础基因能够得以扩散。不过这样想来,就会一直有一种变化存在,使器官能够更好地运作。倘若带来终极改善的基因突变碰巧没有出现,那么这次终极改善也就自然出局。这不仅适用于器官,对于身体机制,比如行为,也如此。
14.
通常我们的眼睛被视为一个完美的器官,只可能是某个智慧的创造者创造出来的。没错,感觉上我们的眼睛是完美的,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既看不到红外线,也看不到紫外线;晚上也看不到颜色,虽然那些颜色是存在的;还有如一毫米的十分之一那样的细节我们也不能用肉眼察觉……所以我们要借助夜视镜、显微镜、望远镜这些工具。除此以外,我们的眼睛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不过这倒成了眼科医生赚钱的好机会!如今又有多少人不戴眼镜呢?
15.
所以说,我们的眼睛不是个完美的器官,不过对我们,还有我们的祖先来说,这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够用了。眼睛在进化中得到了改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百分之百的完美。
同理,疼痛机制也在进化中保存了下来,不过,距离完美还很远。
如果我不想在学生中留下无礼的名声,就不能去掺和这场偷听来的争论。相比之下,我会在课堂上装作偶然提出这个话题,然后告诉他们:不管人们感到多么痛苦,疼痛并不违背进化论,反而是进化论的一种印证。哎!
魔镜魔镜告诉我:
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16.
会开得热火朝天,讨论也如火如荼,大伙儿的情绪可谓高涨。这正是我喜欢的——不是喜欢开会,而是这种火热。观察我的同类的行为真是一件幸福的事。他们的脸色、挥舞的手臂、说话的声调、敲桌子的拳头、有趣的交流方式,当然,在那些言语背后还隐藏着许多别的东西。我沉默地看着,享受着。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年轻的同事,他刚才提出了一个不错的方案,不过很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有些人觉得棒极了,而有些人则大呼“可笑”和“没有经验”,要立刻推倒,进行下一个议题。不过大会主席想先听完所有人的看法,再让大伙儿投票。
17.
我看见坐在旁边的那个同事把一张大会出勤表藏在一堆纸下面,在出席人的名字后面悄悄地画上加号和减号,分别表示支持和反对他的提议。显然,等到加号达到一定数量时,他就会向主席提出投票的要求。两个反对提议的老家伙(亲爱的同事们,不好意思)稳稳地坐在我们对面,而他们旁边的那个人却很沉默,还没有表明一丝一毫的态度。
我那可怜的邻座正犹豫着在他的名字后面画个加号还是减号,想等那个沉默者开口,可他就是缄口不言。“画个减号吧。”我在他耳边小声说。邻座见自己的小把戏被揭穿,吓坏了。“你怎么知道的?”他小声问。“你看看他的胳膊、脑袋,还有他喝咖啡和抬眉毛的样子就知道了。”
18.
同事非常气愤地看着我。要不是我们有年龄差距,他肯定会撇嘴骂我,在接下去的会议中把我当成空气。“他又没说什么!”他朝我小声说。“孩子,那是镜像行为,就画个减号吧,他反对你的提议。”主席不高兴地看着我们这个方向,发现“有些同事在下面开小会”。所以,我只好等到会间休息时再向他一一道明。
镜像行为是诸多行为化石中的一种,很久以前就存在了,可几乎没人意识到它的存在,不过,这对行为生物学来说,却是一种非常值得研究的有趣现象。一方面,人类想要表现出相互间的差异,比较强势或者自以为比较强势的人,会通过发送强势信号将态度清楚地表现出来。谁害怕什么东西,同样也会发出信号;谁觉得别人不如自己,就会被一个带有同情的俯视的眼神出卖。
19.
而另一方面,当人与人之间没有区别或者不想被区分开时,也会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多为模仿彼此的态度或姿势。人们互相模仿,把对方的行为从“镜子里”投射出来,这在生物学里叫“镜像行为”,还有人称之为“回音行为”;也有人叫它“全等行为”,不过这听起来更像一种病的名字。
如果人与人之间互相喜爱,可能是爱上对方,也可能只是普通的互相赞同,是可以通过他们的镜像行为看出来的。他们不使用语言,而是通过模仿,想表达的是:“看,为了清楚表明我们处于同一高度,我很想爬进你的皮肤里,可那还挺难的,那我就模仿模仿你吧。我尽可能地效仿你,这样我们多多少少就成了一个人。”
20.
好吧,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不过这就是这种行为的基础。在餐厅里,你能通过最大化的镜像行为看出,哪些情侣互相恩爱,而哪些人的脚在桌子下面打架,因为后者的姿势和动作的差别会很大。
“你怎么知道那个人反对我的提议?”同事跟个间谍似的,一边小声问我,一边搅着咖啡,以此掩饰他想听我讲述那颠覆性的理论。“因为他双手交叉、架着胳膊的姿势,跟那两个反对你的提议的老家伙一模一样。那两个人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你的方案还不如垃圾,而那个没说话的人则通过相同的姿态,发送出跟他们处于同一战线的信号。”看来我的话还不够有说服力,他喝了一口咖啡,又说:“这么说,你只是根据他的胳膊判断出来的?那谢谢你的……”
21.
“不是的,”我说,“很明显,他脑袋的姿势和摆动时的样子也在模仿反对你的人。还有他的眉毛,每次反对你的人一抬眉,他也会这么做。这些都是很微小的动作,属于微观运动,几乎不被察觉,但也会发生在镜像行为中,只是你几乎看不到罢了。你注意到了吗,他每次喝咖啡的时候,拿起杯子的样子几乎跟那两个人完全一致。我们把这个叫作‘镜像行为式喝咖啡’,好玩吧。”那位同事可笑不出来,不过也不难理解,横在那份方案前的强大阻力让他不知所措。他说:“你说的都很有意思,不过,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呢?能帮得上我吗?又能运用到实际中去吗?还是只想在会间休息的时候制造紧张气氛?”
22.
我很同情他,并没有说出下面的话:“你还年轻,还有很多提交方案的机会。”我试图给他一些希望,尽管连我自己也不怎么相信。
“镜像行为也能反过来使用,通过人为模仿来影响对方。虽然机会很小,你还是可以通过对自身姿势和动作的控制,去效仿那个不说话的人。要是能坚持几分钟,就有机会让其下意识地对你产生同情,从而支持你。有些人会使用这种方法来取悦别人,比如售货员。心理咨询师也会用镜像行为来获取病人的信任。要是那个不说话的人时而注意到你,你就可能通过人工镜像行为来改变他的想法。不过这机会真的很小,一张厚实的支票可能更管用。”
23.
我的话并没有使他高兴起来。看来,他不想再跟一个只会取笑他战役失败的老同事聊下去,于是,他放下咖啡杯,走回会议室。这时,主席也伸手指了指那间屠宰场,一群刽子手便跟了进去。
“鉴于话题的敏感和气氛的紧张,我提议不记名投票。”主席说,“大家都同意吗?好的,发选票吧。”秘书把选票发了出去,一会儿又收回去仔细统计起来。“主席投了反对票。”我凑近那可怜的邻座说。“这你又是怎么看出来的?是他的眼睛吗?”邻座小声问。“不是的,这次我偷看了。”
幸福和流感,
一个关于社交圈的话题
24.
“这事儿我可得跟你说说!”一位公司经理打来电话。他在报纸上看到一个跟人类幸福有关的研究报道后,有如经历了一次山体滑坡。不过他打这个电话我还是挺开心的,借此我又有机会好好观察我们的社交行为了。虽然人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社交性,不过,我们好像对此了解得很少。这个经理让我做了回人类社交的见证人。他的故事是这样的。
他读到的一项美国的研究表明,我们的行为,尤其是幸福,会受到朋友的社交圈的强烈影响。在一个人类社交关系似乎要被Facebook、Netlog和LinkedIn等社交网络主宰或即将被主宰的时代,这可是个热门话题。不过,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真实生活和有血有肉的朋友。不光是我们的朋友具有影响力,朋友的朋友也一样,虽然我们连他们的面都没见过。
25.
还有,我们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也可能具有同样的影响力,社交圈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还真就这么大。当然,决定幸福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有一点是可以想象的——和我们接触最多的朋友的生活幸福度,多少是会传染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是否幸福,能掌控我们的幸福度。生活在一群幸福的人之间,你也会变得幸福起来,就算从来没见过面的人,也可能对你产生影响,这一点让电话里的那个商人很是惊讶,他说:“我担心自己是个机器人。”不过,他最感兴趣的话题还是“这种理论能不能用到公司里去”,并且希望就此得到一些解释,而我乐意为此效劳!
26.
假设您朋友的朋友得了流感,您的朋友可能会被传染,过一阵您自己可能也会生病。以此类推,这串流感还能扯得更远点,因为您朋友的朋友也是被别人传染的,流感病毒由此在人们的社交圈中扩散开来。我们可以简单地想象一下,一个离社交圈较远的人,相比直接接触的人,被传染的机会也较小。您想想看,如果您最好的哥们儿给您发短信说他不来看您了,因为他爱人的好朋友的女朋友的同事得了流感,怕把您给传染了,那您一定会说,他是在为自己不想来找借口。
27.
传染性咳嗽是可控的,然而幸福又该如何控制呢?它又怎么会具有传染性呢?
我让电话里的那位听众去看我2008年写的《大脑机器》,里面就有解释,比那项美国研究发表得可早多了。在那本书里,我把幸福称作许多欢乐体验的串联。欢乐是一种重要的感情,它给予能量,促成合作。倘若你生命的某个阶段充满欢乐,你就会说自己是幸福的。这下子,感情具备了双重价值,一方面具有纯粹的生物效用,恐惧能够帮助我们抵御危险,自豪促使我们做出更多积极的社交举动,提高我们的社交声望……
28.
而另一方面,感情也需要交流,从而使别人对其有所了解,甚至接纳。观察他人的感情信号对我们的大脑,尤其是镜像神经元,有着不同寻常的强烈影响,同一种感情就这样被唤醒了。当然,其强度相比直接发射感情信号要弱些,不过还是会产生一种转移。可能仅发生在两个人之间,也可能产生于一群人之中,感情通过转移扩散至整个群体。我曾称此为“心理学上的血液循环”,感情如血液流遍全身一般流遍集体。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一点非常重要。人类进化中的一个关键特征为社交行为的发展,这一点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们是社交性超强的生物,拥有巨大而复杂的社交性,有点像白蚁,不过可比白蚁强多了。倘若没有这种社交性,文化的发展就会滞后。
29.
在发现新地域需要殖民时,人类就无法发明出抵御严寒的技术(这里我说的是几万年前的事),无法传播知识等等。这一切只有通过紧密合作才会成为可能,而这种紧密合作也就几乎成了“人类”的同义词。只有当群体中的所有成员了解对方的情绪状态,并尽可能地使自己处于同一水平时,合作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此处,心理学上的血液循环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正如恐惧能警告人们危险的到来,欢乐也以同样的方式让每个人从中获取能量。所以说,幸福早在几万年前就传染得很厉害了。我很感谢经理在电话里提及的那些研究人员,是他们优秀的研究使《头脑机器》里的观点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30.
“这个能用到我公司里去吗?”经理还在问这个问题,“比如,把感情的传染性用到我同事身上,从而使产量得到提升。”进化论中关于人类行为的观点能获得商业界的关注,让我感到荣幸。在说了一声“当然可以,但是……”后,我跟那位经理约了个时间,准备亲自去他公司看看聊聊。我们的确可以把进化论中关于人类社交行为的知识运用到一个合作群体中,不过得小心使用。挂上电话,我们让彼此都幸福起来。看来,幸福通过电话也能传染,这点流感就做不到了。
(未完待续)
文章转载自网络
请尊重知识产权
侵权可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