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作者说:
我想通过文字,捕捉那种独特的氛围——石板路上的霜、马头墙下的苔痕、竹竿上油亮的腊肉,还有孩子们舔冰柱子的欢声笑语。这些细节,构成了徽州冬天的肌理,也承载了我对这片土地的眷恋。
老人们抱着铜手炉坐在门槛上,妇人们蒸着米饺,货郎的铃声在巷子里回荡,乌篷船在暮色中靠岸……这些场景,仿佛一幅缓缓展开的水墨画,带着岁月的痕迹和人间烟火的气息。我想表达的,不仅是冬天的景致,更是那种温吞的、带着暖意的生活态度。
那一声声“叮——咚”,不仅是时间的脚步,也是人们对家的期盼。这样的冬天,连寒意都是温吞的,因为它包裹着人间的温情与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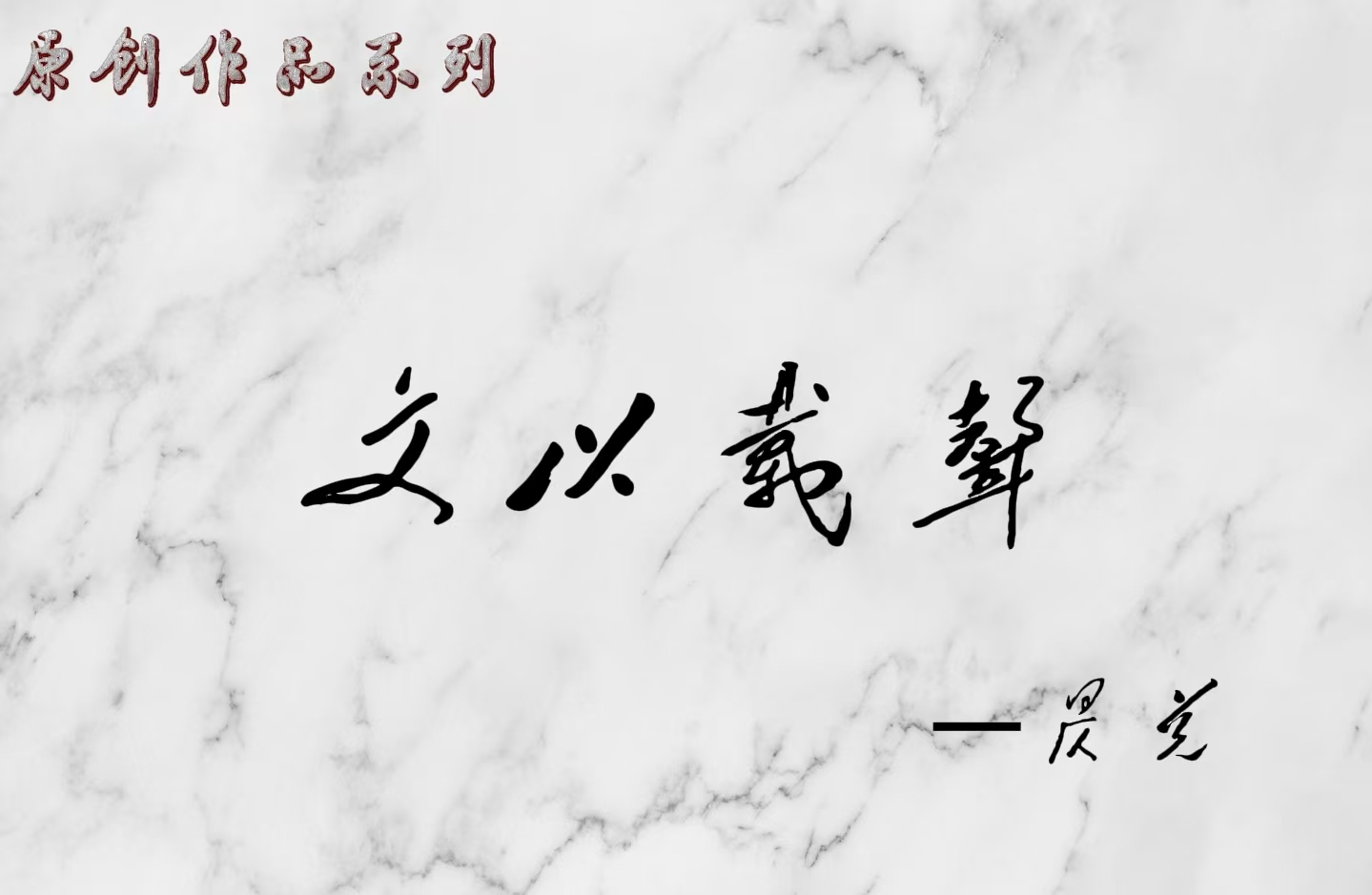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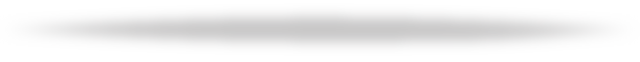
《冬落徽州》
作者:昃 兑
皖南的冬是藏在白墙黑瓦里的。天色总灰蒙蒙的,像宣纸浸了陈年的茶水,檐角便在这昏黄里勾出几道倔强的墨线。石板路让霜浸得发亮,早起挑水的汉子踩过去,扁担吱呀呀的响,惊醒了蜷在柴堆边的狸花猫。
这儿的冷是绵软的,不似北方的刀子风。寒气顺着马头墙的缝隙往下淌,倒叫墙根下的苔痕养得更润了。老人们爱抱着铜手炉坐在门槛上,看晾在竹竿上的腊肉渐渐凝出油亮的光。妇人们把包好的米饺放进蒸笼时,总不忘往围兜里揣两块,哄那些追着饺香来的娃娃。

若是落了雪,倒显出徽州骨子里的清贵。雪粒子细细碎碎地扑在八仙桌似的天井里,不消半个时辰,就把青砖地铺成宣纸。祠堂门环上垂着冰溜子,倒比端午挂的艾草还齐整。最妙是后山竹林,雪压得竹梢弯成月牙,风一过,簌簌地抖落满地碎玉,倒像谁家新妇在筛糯米粉。
晴日里常有暖阳,懒洋洋地趴在美人靠上。废弃的旧学堂里倒是久违的热闹!孩子们挤在廊下,挨挨挤挤舔冰柱子。卖小玩意儿的货郎偏不叫卖,骑着漆皮斑驳的三轮自行车走西家串东家,叮叮当当的脆响能顺着九曲巷飘二里地。这时候炊烟升得格外慢,仿佛要在粉墙上多描几笔水墨。

待到暮色染透古渡口,乌篷船便驮着半舱暮色靠岸。船头煮鱼的泥炉咕嘟嘟冒热气,混着渔人哼的小调,把整条江水都煨暖了。对岸酒旗在风里招摇,酒香缠着雪意,倒酿出三分春意。
这样的冬天,连寒意都是温吞的。就像檐角融雪滴在石臼里,叮——咚,一声声数着归期。

